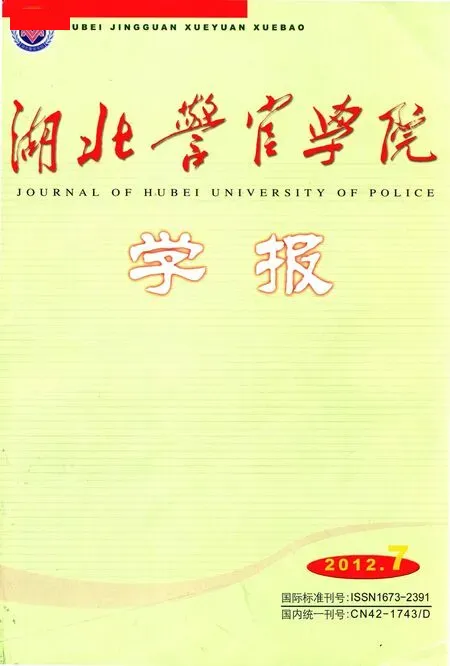傳統(tǒng)與超越:構建案例引證制度
管仁亮,潘仲華,付紅梅
(1.西南政法大學,重慶400031;2.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上海200135)
傳統(tǒng)與超越:構建案例引證制度
管仁亮1,潘仲華2,付紅梅2
(1.西南政法大學,重慶400031;2.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上海200135)
相同或者相似情況同樣對待是人類樸素平等觀念的體現(xiàn)。但司法實踐中“同案不同判”呈愈演愈烈的趨勢,許霆案和何鵬案就是典型例證。相似的案件情節(jié),法官的判決卻差之千里。這凸顯出法官裁量缺乏一個合理的統(tǒng)一標準。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導制度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探索一種新的案例制度,賦予其法律效力,才能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行為,走出目前的困境。
案例引證制度;同案不同判;案例指導制度
一、問題的提出:總結反思的視角
要實現(xiàn)司法公正,樹立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必須建立完善的制度來統(tǒng)一法律適用標準,指導下級法院審判工作,并豐富相關法學理論研究。上世紀8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制度研究開始朝規(guī)范化的方向發(fā)展。相關的案例編纂活動推動了最高人民法院對地方人民法院的指導工作,有五百多個案例相繼被公布。作為司法改革的重要舉措,案例指導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中被明確提出來。這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提出構建和完善案例指導制度,以期解決目前的“同案不同判”問題[1]。但是,該制度一經(jīng)提出,就飽受爭議和質疑。盡管最高人民法院高調建立案例指導制度,但其實施仍然陷入了以下困境:
一是案例指導制度實際上涉及司法權與立法權的界定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將案例指導制度定位于彌補法律漏洞,這就涉及指導性案例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問題。如果承認其具有拘束力,就有違于全國人大及常委會的立法權獨占制;如果不承認,則案例指導制度將僅作為法官判案的參考,不會產(chǎn)生較好的效果,最終會流于形式。二是案例指導制度的制定程序缺少有效制約。確定指導性案例與制定司法解釋不同,其沒有征求全國人大及常委會意見的過程,也沒有相關的備案制度。一旦確立相關的拘束力,司法權極易被濫用。三是指導性案例的推行缺乏相應的實施細則,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具體實踐中,關于法官是否有權提出指導性案例、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如何適用指導性案例、法官不適用指導性案例的理由及相關處罰、指導性案例的期間和溯及力等都沒有相關規(guī)定。[2]四是案例指導制度缺乏必要的監(jiān)督機制。案例指導制度對是否涉及權力監(jiān)管部門、監(jiān)管部門是重新設立還是法院內部設立、監(jiān)督的權限多大、是否要建立專門的違規(guī)處罰體系等均無相關規(guī)定。五是指導性案例的適用對法官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戰(zhàn)。就目前而言,我國法官的素質參差不齊,要想在浩瀚如云的判例中找出依據(jù)或適用多個指導性案例,有不小的難度。上述分析也暗合相關學者觀點,案例指導制度試行的地方性經(jīng)驗在效力載體、適用技術、邊界標準、選擇機制等方面呈現(xiàn)出上下不統(tǒng)一、平行差異大等問題。這是事關制度成敗的重大問題,不能“緩議”,在制度出臺之前應當仔細思量。[3]
截至目前,案例指導制度的制度性缺陷難以被克服。然而,其在我國當前的司法情境中仍有存在基礎和現(xiàn)實意義:一是我國幅員遼闊,地區(qū)差異特別是經(jīng)濟上的差異會影響司法審判的實際效果。因此,要做到“同案同判”,必須建立相關制度,以完成不同地域的司法銜接。二是大眾傳媒的發(fā)展易使“同案不同判”成為社會問題。三是為了適應在科學發(fā)展觀的指引下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以及遵循司法為民、司法便民的理念,司法系統(tǒng)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制度,通過司法能動的方式去解決諸多社會問題。四是“案多人少”是當今司法審判的現(xiàn)實狀況。我們急迫需要以一種司法判例的形式為解決類似案件提供統(tǒng)一的法律標準,緩解“爆炸式”的訴訟壓力。五是在司法實踐中已經(jīng)存在相關案例引證的需求。諸多大標的案件已經(jīng)移交到了下級法院。面對新類型的疑難案件,下級法院需要印證相關“先例”。因此,要真正解決“同案不同判”,約束法官的自由裁量行為,我們必須探索一種新的制度,賦予其法律效力,以擺脫目前的困境。
二、發(fā)掘與剖析:價值分析的視角
基于案例指導制度的缺陷及現(xiàn)實中的需要,筆者認為可以改良現(xiàn)行案例指導制度為案例引證制度。所謂案例引證制度,是指以裁判文書為載體,將其中的裁判要旨、法律邏輯、裁判規(guī)則具體明確化,通過總體的制度構建和運行機制的梳理,在相關案件上征求全國人大及常委會的意見,經(jīng)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討論決定后,以公報的形式進行發(fā)布,法官在審理同類訴訟時,須以案例的裁判規(guī)則為依據(jù),并在裁決理由中加以闡述的制度。案例引證制度源于古代的判例制度和兩大法系在判例法上的實踐,同時借鑒了構建案例指導制度時的經(jīng)驗。其基于固有的性能和功用,具備了諸多法律價值,具體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彌補法律漏洞。法律的穩(wěn)定性必然導致一定的滯后性,一旦法律無法為法院審理案件提供明確依據(jù),案例引證制度就應當適時出現(xiàn)以彌補其不足。大陸法系的傳統(tǒng)就是通過立法來制定完整的程序,不要求法官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地制定法律(法官造法)。但是事實證明,法律無法面面俱到。法律規(guī)則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根本無法形成盡善盡美、包羅萬象的法律體系。[4]法律規(guī)則是一種語言。隨著社會的多樣化發(fā)展,這種以法律為載體的語言凸現(xiàn)出種種不足。案例引證制度可在相關規(guī)范不確定時統(tǒng)一裁判的適用標準,并發(fā)掘成文法在立法時的社會價值標準。同時,法官在審判中引證先例,既保持了法律的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也適應了社會生活的發(fā)展變化,即暗含了“同案同判”的訴求。案例引證制度能巧妙地解釋法律,不是“立法”,卻有效彌補了司法解釋的大量出現(xiàn)對成文法的沖擊,同時又對成文法起到了良好的補充作用。隨著國家立法體系的完備,司法解釋將最終淡出我們的視野,取而代之的將是以案例引證的方式輔助成文法的實施。
二是約束法官自由裁量權。傳統(tǒng)的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約束主要是通過合議庭實現(xiàn)的,但由于具體的司法裁判的尺度不一,在相同事實的案件中,不同的法院或者相同法院的不同法官可能會作出不同的判決。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間太大,實際上已經(jīng)嚴重影響到法律權威和司法公信力。以現(xiàn)行《刑法》為例,不論是在定罪還是在量刑方面,許多規(guī)定都比較抽象、籠統(tǒng),彈性幅度大。除了法律規(guī)定,法官的個人因素也間接地對裁判的效果產(chǎn)生影響。因此,現(xiàn)在的量刑尺度基本上游走于尋求法官裁量權的靈活性與裁判尺度的統(tǒng)一性(限制法官自由裁量)之間。案例引證制度在諸多案件的經(jīng)驗、統(tǒng)計、分析、合法與合理的論證的基礎上,脫離了具體案件情形,制定了普遍性規(guī)定,在量刑問題上使法官形成普遍性的經(jīng)驗,從而達到量刑公正和量刑均衡。當然,案例引證制度中的法官解釋權并不是毫無限制的。這種主觀能動性是在判案過程中,結合引證的案例在判決理由中加以明確的,而不是將司法解釋權完全地交給法官。
三是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案例引證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樹立司法權威。通過發(fā)揮引證案例的作用,有效解決了審判實踐中各法院或法院的各合議庭適用法律時的“同案不同判”問題,保證了審判工作的質量和效率,使司法審判達到公正性和統(tǒng)一性的要求。[5]案例引證制度能在一定的范圍內規(guī)范司法權的行使,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從而鞏固了司法作為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的地位。[6]其要求在相同或者大體相同的案件中實現(xiàn)相同的判決。一旦社會對法律規(guī)則或者裁判規(guī)則產(chǎn)生預期,人們將自覺地遵守法律。案例引證制度能將尊重“先例”的理念傳承下去,將典型案例中的法官智慧和理性體現(xiàn)在之后的裁判規(guī)則中,以便法官處理大量的同類訴訟。要想使裁判獲得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的信服,法官必須詳盡說明裁判理由,以解決司法實踐中當事人很難獲知具體的事實認定和判決理由的問題,提高判決的信服力。
三、解構與梳理:制度建構的視角
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對構建相關制度的探索體現(xiàn)在案例指導制度和判例制度中,如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2004—2008)》的案例指導制度、河南省鄭州市中原區(qū)人民法院的先例判決制度、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判例指導制度、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指導制度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示范性案例評審規(guī)則等。他們的理念與案例引證制度是一致的,都是為同類訴訟提供具體的裁判規(guī)則。但是如何構建案例引證制度的案例選擇主體、案例選擇標準、案例選擇程序和案例發(fā)布方式,是當下亟須解決的問題。下文將從五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是案例引證創(chuàng)制主體。這里的創(chuàng)制主體包括案例的上報主體和決定主體。案例引證制度無法打破現(xiàn)有的司法體制,但是可以在現(xiàn)行司法制度框架內,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導,并負責具體引證案例的選擇、制定、公布、匯編、備案和監(jiān)督。案例的上報主體應當是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而決定主體應當是最高人民法院。部分學者堅持有限主體創(chuàng)制論,認為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可以創(chuàng)制法律。[7]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基層人民法院的案例如何約束上級法院。我們必須明確:基層人民法院可以成為判決創(chuàng)制的主體,即將法官的智慧和判案經(jīng)驗寫進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是案例引證的創(chuàng)制主體,即由最高人民法院壟斷引證案例的創(chuàng)制決定權。當然,高級人民法院也有自己的職責,那就是對基層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上報的案例進行初步的篩選,將提煉的裁判規(guī)則和法律要旨上報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修改并公告。
二是案例引證具體標準。具體的裁判標準可以根據(jù)案件類型予以劃分:第一類是法律規(guī)定相對原則性或者不明確的案件,如許霆案中對ATM機是否屬于金融機構的認定。第二類是新類型案件,如知識產(chǎn)權案件和勞動爭議案件。這類案件的裁判依據(jù)和裁判結果往往極具爭議性,很多時候會影響社會價值導向,甚至影響未來的立法活動。第三類是易發(fā)、多發(fā)性案件。此類訴訟即同類訴訟,法官的司法經(jīng)驗相對成熟。我們可以從此類案件中提煉出一般的法律要義,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行約束。第四類是有重大影響的案件。這類案件的法律適用往往比較困難。由于社會輿情、媒體參與、行政權力等多方面的影響,判決的作出會對整個司法領域產(chǎn)生大的“震蕩”,如劉涌案、佘祥林案、聶樹彬案、杜培武案、邱興華案、許霆案、何鵬案、藥家鑫案、孫偉銘案等。第五類是疑難復雜案件。這類案件在定性上存在爭議,往往是法律未明確規(guī)定或者尚未立法的情形,亟需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案例引證制度為其提供法律依據(jù)。[8]第六類是政策導向性案件。可通過案例的發(fā)布對當前的政策進行宣傳,以實現(xiàn)法治觀念的更新和法治進程的推進。如美國的米蘭達案,就體現(xiàn)了法官對政策的考量。[9]
三是案例選編程序。應在中級及中級以上人民法院設置專門的案例選編委員會,具體組成人員包括法院政策研究室成員、法院審判委員會成員、地方大學法學院教授及學者等。對于地方人民法院在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典型、疑難案例,先由法院的政策研究室進行初步篩選,其間要進行充分討論,接受法學院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并予以備案。要增強案例的說理性,注意案例選編理由及評析的展開。典型案例的具體內容包括案件事實、控辯雙方的觀點、判決理由、判決結果以及提煉的判決要旨。遴選后的案件經(jīng)案例選編委員會上報高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再將中級人民法院遴選的案件和本院受理的上訴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報送,由最高人民法院對案件進行挑選并確定。
四是案例引證發(fā)布方式。案例引證制度要吸取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制度的不足,確保經(jīng)遴選引證的案例一經(jīng)向社會公開,當事人及代理律師能方便查詢,并成為法庭抗辯的理由。在公開的渠道上,首先要選擇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報。特別是對判決的正當性、合法性爭議較大以及在案件事實認定和證據(jù)采信上存在較大分歧的案例,要及時為法官提供法律適用的裁判規(guī)則和思路以及相關認定事實和審查證據(jù)的典型經(jīng)驗。其次要注重多渠道、多媒體的傳播方式。《人民法院報》、《法制日報》等平面媒體具有周期短、發(fā)行量大的優(yōu)勢,可供案例引證制度選擇。同時,為了方便法官和當事人尋找適用的案例,應建立數(shù)據(jù)庫和案例檢索系統(tǒng),便于分類和查詢。最后應重視半官方平臺。引證的案例可通過一些出版機構編輯出版,豐富案例引證制度的傳播途徑。
五是案例引證的采用程序及相關的檢察監(jiān)督。案例引證制度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在審理同類訴訟時,以案例的裁判規(guī)則為依據(jù),并在裁決理由中加以闡述;不適用引證案例的應說明理由,理由不當則直接導致案件的重審或改判。人民檢察院應對引證的案例實施檢察監(jiān)督,即可提出抗訴。盡管引證的案例已經(jīng)脫離了審判環(huán)節(jié),但是仍然與具體司法實踐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引證案例無法保證正確性和合憲性,理論上就存在被撤銷和被提起抗訴的可能性。因此,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的發(fā)生,最高人民法院及下級人民法院在選取案例的過程中要征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地方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意見,邀請其參與討論,發(fā)表意見。
余論
案例引證制度需要其他制度配合才能實現(xiàn)應有的效果。在整個司法體制框架內,各個制度之間都存在廣泛的聯(lián)系。因此,我們必須處理好案例引證制度和法官遴選與監(jiān)督制度、文書公開制度以及司法解釋制度之間的關系:既要劃分各自的適用范圍,也要注重制度之間的互相銜接與支持。
[1]黃曉云.案例指導制度的歷史沿革[J].中國審判新聞月刊,2011(59).
[2]陳燦平.案例指導制度中操作性難點問題探討[J].法學雜志,2006(3).
[3]楊力.中國案例指導運作研究[J].法律科學,2008(6).
[4]劉作翔,徐景.案例指導制度的理論基礎[J].法學研究,2006(2).
[5]龔稼立.關于先例判決和判例指導的思考[J].河南社會科學,2004(2).
[6]陳衛(wèi)東,李訓虎.先例判決·判例制度·司法改革[J].法律適用,2003(1).
[7]馮軍.論刑法判例的創(chuàng)制和適用[A].武樹臣.判例制度研究(下)[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8]陳燦平.司法改革及相關熱點探索[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
[9]張艷.案例指導制度的價值探究及理性定位[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
D926
A
1673―2391(2012)07―0093―03
2012—03—31
管仁亮,男,山東日照人,西南政法大學;潘仲華,男,上海人,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付紅梅,女,江西新余人,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
【責任編校:王 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