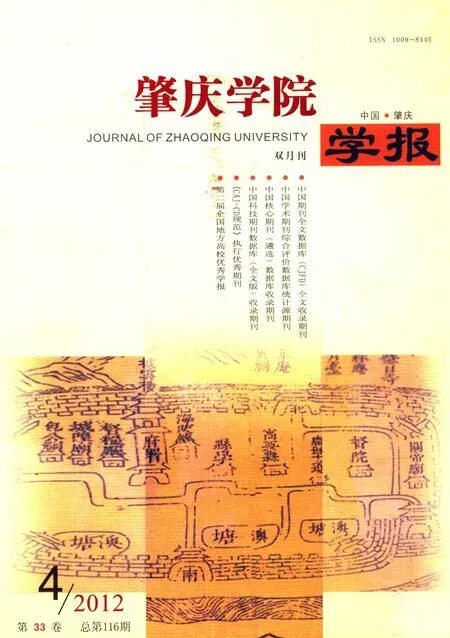魯迅的書籍裝幀與“民族性”體現
張圣兵
(江蘇廣播電視大學 傳媒藝術系,江蘇 南京 210036)
魯迅的書籍裝幀與“民族性”體現
張圣兵
(江蘇廣播電視大學 傳媒藝術系,江蘇 南京 210036)
魯迅是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國現代書籍的裝幀設計方面也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不僅對中國傳統(tǒng)的書籍裝幀藝術深有研究,還大力引進了西方好的書籍裝幀形式。在引進西方優(yōu)秀文化藝術的同時,他注意到了一個關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問題——“民族性”,魯迅的書籍裝幀設計正是他勇于引進西方文化而又能夠保持傳統(tǒng)文化中“民族性”的體現。
魯迅;書籍裝幀;“民族性”
如果從我國秦漢時期的簡冊書籍就開始算起的話,中國書籍裝幀的歷史已相當久遠。隨著造紙術、印刷術等出版技術的發(fā)明,中國書籍裝幀的形式得到了不斷的豐富和變化,先后出現了卷軸裝、散頁裝、旋風裝、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不同的裝幀藝術形式。但是,現代書籍的裝幀形式是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廣而逐步發(fā)展起來的,其中魯迅的貢獻功不可沒。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一員,魯迅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國現代書籍的裝幀設計方面也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不僅對中國傳統(tǒng)的書籍裝幀藝術深有研究,而且大力引進、介紹了西方好的書籍裝幀形式。在進行現代書籍裝幀設計的嘗試與革新中,魯迅不僅身體力行,從書籍的封面、版式、插圖、紙張、印刷等各個環(huán)節(jié)親自參與書籍的裝幀設計,他還扶植了一批年輕的書籍裝幀設計家。如陶元慶、孫福熙、司徒喬、錢君等人就是在魯迅的直接鼓勵和支持下,創(chuàng)作出許多優(yōu)秀的書籍裝幀藝術作品的。魯迅在引進西方優(yōu)秀文化藝術的同時,注意到了一個關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問題——“民族性”。魯迅提出的“民族性”不僅在當時的文學、繪畫等藝術形式中得到了體現,書籍裝幀這一魯迅經常接觸的藝術領域自然也是他吸收外來文化與繼承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實驗場地。
魯迅在很早以前就已關注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藝術并意識到“民族性”問題。早在1912年受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僉事時,魯迅就開始大量搜集并研究中國古籍中的插圖和各種石刻碑拓,如《漢畫像》、《六朝造像目錄》和其他許多金石拓本。魯迅當時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主要職責就是保存祖國的歷代文化遺產以及為發(fā)展社會教育服務,這為他接觸祖國的優(yōu)秀文化遺產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同時,這一穩(wěn)定的工作及優(yōu)厚的待遇也為魯迅收集與研究碑拓藝術提供了經濟上的來源。在1915年至1918年這幾年時間里,魯迅搜集、購買了大量的碑帖拓片和古籍插圖并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為了研究中國的歷史與文字,更好地繼承和發(fā)揚中國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魯迅不僅臨摹漢魏六朝的碑帖文字,甚至把墓志上的紋飾也臨摹下來。他曾對許壽裳說過:“漢畫像的圖案,美妙無倫,為日本藝術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鱗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贊許,說日本的圖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淵源固于我國的漢畫呢。”[1]在魯迅的日記里,也經常能夠看到“錄碑”、“整理拓片”的記載,并將不同的拓片作對照。錢君在《憶念魯迅先生》一文中回憶1927年11月的一天,他和陶元慶一起拜訪魯迅時說:“我們跟他上樓,大家隨便談了一些閑話,因為元慶常為魯迅先生設計封面,不知不覺談到這個話題上,并提出民族化的問題來,魯迅一聽,認為很有意思,便想到他所收藏的畫像石拓片,于是取出來大家探討,提醒我們是否可以從這些東西中吸取養(yǎng)料……這些精美的畫像石拓片,對我啟發(fā)很大,后來我在許多封面中運用了這些畫像的構圖和技法,如《民十三之故宮》和《東方雜志》等書刊裝幀。”[2]由此可見,魯迅多年來傾力搜集大量的畫像碑拓,并不僅僅是為了愛好而收藏,而是要通過研究這些傳統(tǒng)文化遺產并從中探尋出中華民族的“魂”,即文化藝術中的民族精神,也就是魯迅后來經常提到的“民族性”。魯迅建議錢君和陶元慶在書籍的裝幀設計上要多運用一些民族形式,認為如果把青銅器、畫像石等優(yōu)秀的圖案紋樣運用到封面設計中去,會有強烈的民族風格出現。由此可見,一方面,魯迅積極推動我國的書籍裝幀通過學習國外優(yōu)秀作品而不斷創(chuàng)新,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希望能夠創(chuàng)作出具有我國自己獨特面貌特征、不同于別國風格的書籍裝幀藝術作品。
魯迅在1927年12月所寫的《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一文中說:“陶元慶君繪畫的展覽,我在北京所見的是第一回。記得那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虛,則就是:民族性……陶元慶君的繪畫,是沒有這兩重桎梏的。就因為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我想,必須用存在于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yè)的中國人的心里的尺來量,這才懂得他的藝術。 ”[3]549-550此外,魯迅在致美術青年的信中也曾多次提到過“地方色彩”或“中國特色”的問題。如“地方色彩,也能增畫的美和力,自己生長其地,看慣了,或者不覺得什么,但在別地方人,看起來是覺得非常開拓眼界,增進知識的”[4]431-432。 “這幅木刻, 我看是好的,很可見中國特色。我想,現在的世界,環(huán)境不同,藝術上也必須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4]4-5。“有些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4]80-81。 事實上,無論是“地方色彩”,還是“中國特色”,在魯迅看來,就是要在藝術作品中保持“民族性”。這種“民族性”都是中國藝術所具有的不同于別國藝術的特點,或者說是中國美術所具有的民族性的特點。魯迅筆下的“中國向來的靈魂”或 “地方色彩”正是這種“中國特色”的“民族性”的體現。這種“中國向來的靈魂”或“地方色彩”的文化,充分地體現在魯迅所設計的書籍中,成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書籍裝幀設計的典范。
魯迅于1922年設計、出版的《吶喊》一書,封面既簡潔、樸雅,又能體現豐富的文化內涵。該書可以說是從傳統(tǒng)的書籍裝幀形式向現代書籍裝幀藝術過渡的代表之作,也是魯迅所主張的 “民族性”、“中國向來的靈魂”在書籍裝幀上的充分體現。魯迅在設計《吶喊》一書的封面時以深紅色作底色,沉重有力而又鮮艷醒目,它既象征著受害者的鮮血,又昭示著斗爭和光明。在一個黑色的長方塊上像是用利刃深深地鐫刻上去一樣地寫著兩個很有力度的隸書字體——“吶喊”,字體舒展,猶如兩個被關在鐵屋子里的人正張大嘴巴竭盡全力高聲“吶喊”。而在“吶喊”二字四周的黑方塊上又“鏤刻”上一圈方形的框線,猶如一座牢籠囚禁著“吶喊者”。黑色的方塊襯托著“牢籠”和牢籠里的“吶喊者”,象征著舊社會的黑暗在無情地困擾著人民大眾。魯迅在《吶喊》的《自序》中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意思是掙扎著死去比昏睡著死去痛苦得多。但正如金心異(錢玄同)所言:“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3]419-420這“吶喊”就是要喚醒那些正在黑暗的“鐵屋子”里昏睡的人們,起來反抗,起來戰(zhàn)斗,共同毀壞那囚禁人們的“鐵屋子”,推翻那吃人的黑暗的舊社會。

魯迅《吶喊》一書的封面設計既包含著現代意識,又富有民族特色,還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含義。大面積“中國紅”和隸書字體等這些帶有“中國特色”的設計元素地成功運用,既簡潔醒目,又穩(wěn)重樸雅。與其說作者在設計書籍封面,不如說作者就在吶喊、在召喚,在傳達他自己內心的焦慮與憂患意識,也寄予了他的希望。這些正是魯迅的改革思想在書籍裝幀上的體現。

《桃色的云》是魯迅最早采用古典圖案來裝飾書籍封面的作品。它是魯迅翻譯盲詩人愛羅先珂的童話集,1923年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該書在白色封面上,用紅、黑2色套印,書的上半部分是由漢畫人物、禽獸及流云組成的紅色帶狀紋飾,這種紅色紋飾不像《吶喊》封面中的紅色那樣沉重,帶狀紋飾像朝霞,又像流云,給人一種飄渺、流動之感。設計者正是利用這種飄渺、流動的紋飾圖案,既點明了“桃色的云”這個主題,也告訴了讀者:這是一本具有豐富想象力的童話故事書。書的封面下邊利用黑色宋體鉛字排上書名和作者名,簡潔明了,正好與封面的上部紋案形成上下呼應之勢。白底、黑字、紅色圖案,封面總體上給人一種簡約、素凈的風格印象,又透露出一種濃郁的東方古韻。魯迅把之前搜集、研習的漢代畫像拓片開創(chuàng)性地運用在書籍的封面設計上,這是他在翻譯作品的裝幀設計上追求民族化風格的成功嘗試,為書籍裝幀設計借鑒民族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下了成功的先例。這也是魯迅所提倡的對待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要做到 “古為今用”的思想體現。魯迅親自設計或題名的書刊中,很多都體現了這一思想。

除此之外,魯迅還采用過中國傳統(tǒng)的線裝書的形式來印西洋畫冊,以此來表現東方傳統(tǒng)文化。雖然他采用這種方法來設計的書刊在數量上并不多,但卻很有特色。例如,《會稽郡故書雜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梅斐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等都采用此法。這些書雖是舊式線裝,卻又不顯其舊,特別是對題箋的設計,意匠新穎,古雅清新,很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民族裝幀藝術的情趣。另外,1934年魯迅編的畫冊《木刻紀程(一)》,“赭石色地,淺赭石色的橫長方色塊放在書的中間略偏上方,魯迅所書五個黑色活潑、有力的行書名字,一條黑色的手繪線把這四個字上下隔開,‘壹’字放這四個字的右邊;西式翻身,傳統(tǒng)的裝訂形式”[5]。該書的裝幀設計看起來比較簡單,但內里卻繼承著明清時代線裝書設計的那種簡約、雅致的風格。封面整體給人的感覺是古雅而富有韻味,很有 “東方的美”,不失為書籍裝幀設計中的優(yōu)秀作品。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背景下,當時很多國人都提出了向西方文明學習的要求,“西學東漸”之風日漸興盛,大有沖擊和動搖中國幾千年傳統(tǒng)文化之勢。在此背景下,魯迅面對當時一片西化的呼聲,清醒地指出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不要忘了借鑒優(yōu)秀的民族藝術。一方面,他提出了“拿來主義”,鼓勵辨證地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另一方面,他也再三強調了要在文學、藝術中繼承和發(fā)揚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保持和彰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魯迅的書籍裝幀設計正是他勇于引進西方文化而又能夠保持傳統(tǒng)文化中“民族性”的體現。魯迅這種開放而又自立的文藝思想,不僅在當時起到很大的指導作用,而且直至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間文化交流中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1] 邱陵.書籍裝幀藝術簡史[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25-26.
[2] 楊永德,楊寧.魯迅最后十二年與美術[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25-26.
[3] 魯迅.魯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 魯迅.魯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5] 楊永德.魯迅裝幀系年[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78-79.
Book Cover Designing by Lu Xun and his Embodies Of“Nationality”
ZHANG Shengbing
(Jiangsu Radio And TV University,Jiangsu,Nanjing,210036,China)
Lu Xun was not only a great writer,thinker and revolutionist,but had also made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modern book binding design.He had not only done deep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book binding art of China,but also vigorously introduced good book binding forms from Western World.Lu Xun paid attention to a matter of fundamental national culture—“nationality”while introducing Western excellent culture and fine arts.It is embodied to Lu Xun bravely introduce western culture,at the same time be able to keep this“nationality”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Lu Xun’s book binding design.
Lu Xun;cover designing;nationality
J524.5
A
1009-8445(2012)04-0045-03
(責任編輯:盧妙清)
2012-01-11
張圣兵(1969-),男,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傳媒藝術系教師,高級工藝美術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