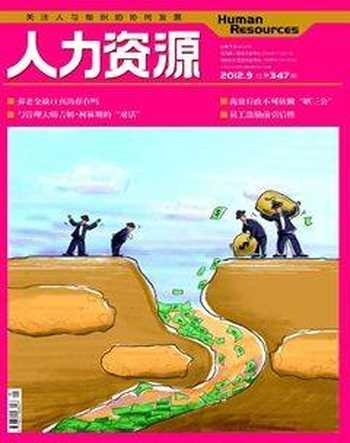“習”:山高不礙云飛(外兩篇)
老范行軍
很小的時候,大家都被灌輸: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怎樣做才叫“好好學習”?
看一眼這張“圖”——上邊是兩根“羽毛”,無疑代表了鳥的翅膀;下面是輪“太陽”,想必就是光天化日了。那么,先民創意此字到底想要表明什么意思呢?不難分析:甲骨文中的這個字,表示了鳥在晴朗的日子里練習飛翔。
這個會意“鳥在晴朗的日子里練習飛翔”的字,就是“習”。
《說文解字》里釋義“習”是:數飛也。“數”為多,可見“習”乃多次練習奮飛之技。
繁體字之“習”,上面依然保留著“羽毛”的姿態,也即飛的“會意”,簡化字干凈利索地“剪”掉了鳥兒練習飛翔的翅膀。
分析“習”之初義,反觀職場之上的經驗、創意、理念、技術、方法……,不可一揮而就,只有不斷地“練習飛翔”,方可“習”得。
“習”的過程最忌諱的是:一瓶不滿,半瓶晃蕩;不求甚解,遇事麻爪。
任何好的東西都不是天上掉餡餅,而是不斷地“習”得,而好的習慣也就是在習得的基礎上,潛移默化,形成了“程序化”,瓜熟蒂落了一般。習慣成了自然,做事便游刃有余,從容淡定。
“習”得了溝通技巧,“竹密何妨水過”。
“習”得了銷售技能,“山高不礙云飛”。
總之,“習”得了什么,都是自己的。
俗話說,技不壓身。
“看”:不畏浮云遮望眼
“看”是個會意字,“手”與“目”組成:a+目=看。
“看”里面有“目”,當然,不是一“目”十行,那樣,過于草率與匆忙;更不是“目”中無人,那樣,等于把他人看扁,到頭來卻被大家看扁;此“目”乃是“眼”觀六路,把周圍的那點事,看得明白。
看明白是非——看不明白,說明沒有判斷力,隨人舉手,人云亦云,有路就走,不辨方向,到頭來還是走不通。
看明白真假——看不明白,說明缺乏識別力,近墨而不知恥,遠善卻不覺愧;需實時蜻蜓點水,該虛時猛虎下山……真個糊涂蛋一枚,孵化不出孔雀。
看明白忠奸——看不明白,說明沒有觀察力,良莠混淆,云泥不分。如果與友隔閡,尚可挽救;以敵為友,上了賊船想下來,晚矣。
看明白遠近——看不明白,就不知道誰親誰疏,好似把一碗水端平了,其實,那碗水誰喝了也不會感到解渴。
看明白香臭——看不明白,就無法了解哪里放著香瓜,哪里埋著地雷。
職場之上,必須看得明白,不明不白的結果,就是不紅不黑,成為一個邊緣人,“姥姥不疼舅舅不愛”。
“看”里面有“目”,此“目”乃是“不畏浮云遮望眼”之“目力”,所以要看得遠,才好。
如何才能看得遠?
“看”字本身就“結構”了直觀的啟示——要望遠,必須放下“手”里的雞毛蒜皮,抬“手”搭在“目”之上,擋住刺眼的陽光,方可眺望。所以,這“手”上的負擔,其實是心中的沉疴,只有像清人王永彬在《圍爐夜話》中說的“可放手者,便須放手”,才能靜下心來,登高遠望,看破浮云。
關于“看”,還有個段子,有點意思,抄錄于此:看上級不順眼,是自己的能力不夠;看老板不順眼,是自己的夢想不夠;看同事不順眼,是自己的胸襟不夠;看朋友不順眼,是自己的眼力不夠;看自己不順眼,是自己的修煉不夠;看別人不順眼,是自己的修養不夠。
“看”里有“手”,此“手”乃撥“開”門扉之“手”——前面說過“開”字遠古時的形態,即用手打開門閂。所以,“看”這職場的人來人往,熙熙融融,就得“看”得“開”。
看不開,喝水都塞牙縫,屋漏偏逢連夜雨,春風不度玉門關。
看開了,枯木逢春,柳暗花明,逢兇化吉。
“功”:你是在建一座教堂嗎
傻瓜才不想建功立業!
可是,仔細想來,“建功立業”的機遇又像羚羊的尾巴,很難伸手就能抓到。
如果我們是營銷人員,可能千辛萬苦之后,簽訂了一個千萬、過億的大單;
如果我們是研發人員,可能廢寢忘食之后,研發了一項市場前景廣闊的產品;
如果我們是采購人員,可能踏破鐵鞋無覓處,終得到物美價廉的材料,使得產品成本大幅下降,讓利消費者的同時,也讓競爭者退避三舍……
可是,我們偏偏是行政助理、人事主管、出納、統計員、前臺接待……是的,我們忙忙碌碌,卻與一鳴驚人不在一條線上,更難碰撞到轟轟烈烈的壯舉——建立功業,似乎遙不可期。之所以說“似乎”,因為,英雄并非都誕生在風口浪尖之上,功勛也不是都產生于扭轉乾坤之時。大海沒有沙灘,還會浩瀚澎湃嗎?那么,平靜的沙灘不就是承載海洋的胸懷嗎?
一粒沙,就是一片沙漠。
一片葉,就是一棵大樹。
只要我們將自己的“一畝三分田”耕耘得郁郁蔥蔥,同樣是在建立不可磨滅的業績。
真的嗎?
真的。
看看這個“功”字。
功=工+力,寓意明了:“工”作中竭盡全“力”,就是“功”勞。也就是說,不在于從事的工作多么微不足道、異常瑣碎,只要認真、細致、準確、快速地完成,就是將簡單的事情,做到了不簡單。
對,就是不簡單。
盡管,在他人眼里,算不上“優秀人才”。
那,又何妨?
稻盛和夫在《活法3》中說:“我認為,構筑組織好比修筑城池。修筑完美的城池首先必須建造堅固的石墻。然而,石墻并非僅由巨石——優秀人才所構成。巨石與巨石之間必須填埋小石塊。每個險要之處,若沒有巨石與巨石之間填埋的小石塊,那石墻必須脆弱不堪,一觸即潰。”
可見,時刻肩負著 “小石塊”的責任,實質上正是在建功立業。沒有“小石塊”,就沒有堅固、持久的石墻,也就沒有了企業的基業長青。
山腳下,一些石匠在鑿石頭。有人過去問他們:“你們在做什么哪?”
一個石匠回答:“還能做什么,掙錢養家唄。”
第二個石匠不無自豪地說:“我嘛,很簡單啦,在做世界上最好的石匠活。”
第三個石匠看了一下遠方,輕輕地說:“我在建一座教堂!”
現在,冥想一下:第三個石匠鑿下的石頭,會放在教堂的什么地方?
如果石頭成為一塊臺階,讓眾人踩在上面,會影響到石匠的工作質量嗎?
如果石頭深埋于地基下,從此不見日月,會影響到石匠的工作熱情嗎?
答案是否定的。
當然了,許多時候,我們還是想要做功臣,不甘當“小石塊”,想成為“巨石”——“工”作中所要付出的就是巨大的努“力”了。功臣之“臣”,由“巨”和兩個短“〡”構成:上面的“〡”,要頂天立地;下面的“〡”,為腳踏實地——宏大的愿景深耕于默默的前行,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