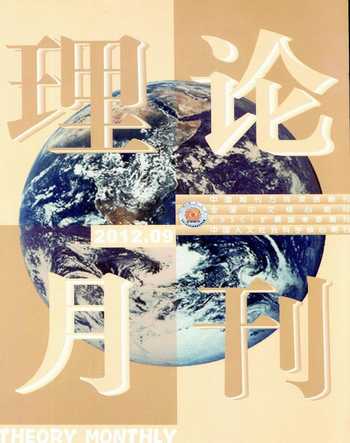論美國版權法定賠償的適用
張春艷
摘要:在美國版權法定賠償的裁決中,一些非商業用戶被施以巨額法定賠償,而另一些侵犯音樂專輯著作權的大公司卻被裁定較少的法定賠償。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陪審團考慮法定賠償的社會警示作用;后者主要是因為音樂專輯作為編輯作品,其所有組成部分被當作一部作品來計算賠償額。法院適用法定賠償時所考慮的Williams案檢驗標準、Gore案檢驗標準和Phillp Morris案檢驗標準實則是懲罰性賠償檢驗標準。UMG案檢驗標準作為法定賠償檢驗標準,明顯減少了懲罰性因素。
關鍵詞:版權;作品;法定賠償;檢驗標準
中圖分類號:D93.34(7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9-0185-04
一、問題的提出
2010年美國對兩起版權法定賠償案件的裁決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和爭議。一個沒有任何營利的非商業用戶被施以巨額法定賠償,而另一個侵犯音樂專輯著作權的大公司卻被裁定較少的法定賠償。
2005年初,美國六大唱片公司(Capitol Records、SonyBMG、Arista Records LLC、Interscope Records、UMGRecordings以及Warner Bros.Records)起訴一非商業用戶Jammie Thomas從計算機發布24首音樂到Kazaa網站的分享資料夾的行為侵犯其版權,要求適用法定賠償。2007年10月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聯邦陪審團判定JammieThomas侵權行為成立,以每首歌曲法定賠償9250美金計算,她總計須賠償222000美金給原告。Thomas不服,提出一個新審判的動議。2009年6月陪審團裁定:(1)每個原告各自享有版權;(2)Whomas構成侵權;(3)Thomas屬于故意侵權。因此,陪審團裁定Thomas對涉案的24首歌曲,以每首歌曲賠償8萬美元計算,須賠償192萬美元。Thomas繼續提出抗辯,認為罰金高得離譜。主審法官戴維斯(MichaelJ.Davis)在2010年1月將法定賠償數額減低到54000美元,并稱192萬罰金是“可怕的和令人震驚的”。數天后,原告提出解決方案,只要Thomas拿出25000元的罰金并認罪就行了,但被拒絕。2010年11月,陪審團又一次裁決Thomas侵權,此次判法定賠償數額為150萬美元。
與Thomas案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Anne Bryant和Ellen Bemfeld訴媒體權利生產商和果園企業一案中(以下簡稱果園企業案),被告則承擔相對較少的法定賠償責任。
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Bryant和Bernfeld創作并發行兩張專輯,每張專輯包括10首歌曲。2007年4月,Bryant和Bernfeld以媒體權利生產商和果園企業未經其許可,在網上音樂商店銷售其享有版權的數字音樂作品并提供下載業務為由起訴到紐約州南區法院,并要求法定賠償,法院最后裁定媒體權利生產商構成故意侵權,每張專輯賠償1000美元共計2000美元;而果園企業由于主觀上不知道其實施的是侵權行為,被判每張專輯賠償200美元,共計400美元。而且Bryant和Bernfeld提出要求被告支付律師費的請求也被法院否決。2010年4月,美國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支持地區法院的判決:版權人只能就音樂唱片專輯整體獲得法定賠償,而不能就專輯中的每首歌分別獲得法定賠償。
通過比較,不難發現,同一年適用法定賠償的兩起案件,裁決的結果卻有天壤之別。一起案件的故意侵權法定賠償裁決是“可怕的和令人震驚的”,而另一起案件的故意侵權法定賠償裁決只有區區2000美元。這種巨大的反差不禁使人質疑:巨額法定賠償的法律依據何在?非商業用戶為何成為施以巨額法定賠償的對象?法定賠償的檢驗標準和計算標準是什么?本文將圍繞著這些問題。對美國版權法定賠償的適用展開論述。
二、美國版權法定賠償立法
美國的版權法定賠償救濟源于1710年英國的《安妮法》。1790年,美國頒布的版權法中首次出現了法定賠償條款,其后,版權法雖然經多次修訂,但法定賠償的條款始終被保留了下來。美國現行版權法是1976年版權法,不過,隨著新技術的出現,該法也多次進行修訂。
美國版權法第504條(c)款對法定賠償作了明確規定:“(1)除本款第(2)項另有規定外,版權所有人在最終判決作出前之任何時間,可以就訴訟所涉及的所有侵權行為選擇法定賠償,以代替以實際損失及侵權人所得進行的賠償。就任何一部作品而言。無論侵權人系個人單獨承擔侵權責任還是兩名或者兩名以上的侵權人連帶承擔侵權責任,法定賠償金為不低于750美元或者不超過30000美元,以法院視正當而定。就本款規定而言,編輯作品或者演繹作品的所有內容構成一部作品。(2)版權所有人承擔舉證責任證明侵權行為系故意實施并且經法院認定的,法院可酌情決定將法定損害賠償金增加到不超過15美元的數額:侵權人承擔舉證責任證明該侵權不知也無理由相信其行為侵犯了版權并且經法院認定的,法院可酌情決定將法定賠償金減少至不少于200美元的數額。無論如何,侵權人認為并且有合理根據相信其對版權作品的使用依第107條系合理使用的,法院應免除法定賠償……。”
根據美國版權法第504條(c)款的規定,可以看出,第一,美國版權法按照侵權者的主觀因素分別規定三種不同的法定損害賠償幅度;第二。編輯作品的所有內容構成一部作品。
在Thomas案中,Jammie Thomas從計算機發布音樂的行為被裁定為故意侵權,依據美國版權法第504條(c)款(2)項的規定,陪審團可以在750美元到15萬美元的幅度內做出法定賠償裁定。顯然。2010年11月陪審團做出的150萬美元的法定賠償裁決是按每首歌6250美元計算,的確控制在版權法規定的法定賠償幅度內。并沒有違反版權法的規定。而在Bryant和Bernfeld訴媒體權利生產商和果園企業一案中,媒體權利生產商因故意侵權被裁定2000美元的法定賠償,是因為法院將音樂專輯視為編輯作品。按照版權法的規定,一部編輯作品的所有部分構成一部作品,那么一張包含10首歌的專輯僅視為一部作品,故而,媒體權利生產商只需就兩部作品。而非二十部作品進行法定賠償。因此,如果僅僅考慮美國版權法的規定,這兩起案件的裁決都符合法律的規定。但是,讓人深思的是,同樣是故意侵權,陪審團為何對并沒有從侵權中獲利且只給權利人造成極少損失的非商業用戶裁決每部侵權作品6250美元的法定賠償?反之,法院對一個從侵權中獲利的大公司只做出每部侵權作品1000美元的法定賠償。這樣的反差無法通過版權法法定賠償的規定予以解釋,只能在法定賠償適用中尋找答案。
三、對非商業用戶適用巨額法定賠償的社會原因分析
Thomas是非商業用戶,并沒有從其侵權行為中直接獲利。她給原告造成的損失也很少。Thomas非法發布的歌曲,在iTunes音樂超市和其他的零售商在線賣僅0.99美元至1.29美元之間。在iTunes音樂超市每首歌如果賣0.99美元,唱片公司僅能得到0.70美元。也就是說,Thomas非法發布歌曲,給被告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僅有十幾美元。區區十幾美元的直接損失卻要承擔天文數字的法定賠償,這個結果不僅讓Thomas難以接受,就連主審案件的法官也認為這是一個“可怕的和令人震驚的”裁決。其實,在美國,對非商業用戶裁決巨額法定賠償,并非個案。2009年12月,陪審團曾裁定美國波士頓大學學生Joel Tenenbaum因非法下載和分享30首享有版權的歌曲構成故意侵犯原告的版權,裁決Tenenbaum每首歌須支付22500的法定賠償金,總計675000美元。
Thomas案和Tenenbaum案在當事人方面有一個共同點,即被告方都屬于沒有從侵權中獲利且給原告造成極少損失的非商業用戶,而原告都是美國的大唱片公司。按常理。一個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公司沒有必要為區區幾十美元而大動干戈。但事實是,近些年,數以千計的非商業用戶陸續成為這些大公司的打擊目標。這實際上,與美國唱片業協會的維權策略有關。
Thomas和Tenenbaum都是因為使用p2p軟件下載音樂而被原告起訴。針對p2p網絡軟件對唱片業造成的巨大沖擊,美國的唱片業協會采取了三大策略:首先是以間接侵權為由,起訴P2P文件分享公司和網絡服務提供者;其次唱片業發起了一個廣告宣傳運動,指出正是在線用戶的不良行為才是實質譴責的對象。最后,當這些措施都未能奏效時,他們采取了非常有爭議的策略,開始起訴非商業用戶。
不可否認,非商業用戶給唱片公司造成的直接損失要遠遠小于間接損失,非商業用戶通過P2P網絡進行文件分享會使唱片公司失去大量潛在的消費者。對于這些非商業用戶侵權者,唱片公司一般采取庭外解決,真正像Thomas和Tenenbaum那樣經過陪審團審理的畢竟是少數。不過,陪審團認為Thomas和Tenenbaum的行為帶有普遍性,如果不加以嚴厲制裁,就會給唱片業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裁決巨額的賠償金。可以說,陪審團為唱片公司打擊非商業用戶的侵權行為“推波助瀾”。在歷史上,版權保護的是公共利益,但是現在,法庭中占主流的觀點把作者或者版權持有者的利益放在社會利益之上。因此,為了充分保護版權作者或者持有者的利益。這些非商業用戶開始為數百萬計的版權損失“埋單”。但是,對非商業用戶裁決天文數字的法定賠償還是讓許多人質疑這些裁決的合理性,這些裁決是否違反了美國憲法的正當程序條款?
四、美國版權法定賠償適用的檢驗標準
當Thomas被裁決222000美元的法定賠償時,Thomas不服,提出一個新審判的動議,其理由是法定賠償的數額太過分,提出依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BMW訴Gore案(以下簡稱“Gore案”)中確立的懲罰性賠償適用檢驗標準,陪審團的裁決違反了美國聯邦憲法的正當程序條款。Thomas提到的懲罰性賠償適用檢驗標準并非法定賠償適用檢驗標準,但是由于兩者都具有威懾被告侵權的目的,有相似之處。所以經常被援引用作檢驗法定賠償適用的合理性。
(一)懲罰性賠償適用檢驗標準
1.Williams案檢驗標準。1915年,Williams姐妹起訴鐵路公司超出法律規定的票價向她們每人多收了66美分,按照阿肯色州法律的規定,兩姐妹請求陪審團裁決鐵路公司按每人$50到$300之間進行賠償。最后兩姐妹各得到75美元的賠償,這個數額是兩姐妹實際損失的114倍。鐵路公司爭辯說裁決結果太過分,損害了它的正當程序權利,提出上訴。聯邦最高法院駁回了鐵路公司的上訴,支持阿肯色州法院的裁決,并指出,不應該僅僅通過比較鐵路公司超收較少的票價和兩姐妹獲得較多的賠償額來檢驗裁決的合法性。相反,應該考慮下列因索進行檢驗:公共利益;無數實施危害行為的可能性;保證統一遵守已規定票價的需要。
Williams案檢驗標準比較關注對公共利益的維護,強調賠償的社會示范作用,通過懲罰被告,為他人確立一個反面“典型”。使他人能夠從中吸取教訓而不再從事類似的侵權行為,以達到制裁侵權行為,維護公共秩序的目的,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2.Gore案檢驗標準。199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ore案中確立了懲罰性賠償適用檢驗標準,認為假如懲罰性賠償與實際損失相比被裁定極其過分。那么這一裁定將違反司法正義,構成違憲。在Gore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裁定500倍于實際損失的懲罰性賠償是極其過分的,并確立了懲罰性賠償的三部分檢驗標準。這個標準包括的要素有:(1)被告行為的可譴責性;(2)受害者遭受的實際損失與懲罰性賠償額之間的差距;(3)特定案件救濟和與之相類似的案件的救濟之間的差別。
可以看出,Gore案檢驗標準首先強調被告行為的可譴責性。一般而言,被告行為的可譴責性越高,再次侵權的可能性越大或者給原告造成的損失越多。為了達到威懾和阻止侵權的目的,相應地,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就越高。其次,Gore案檢驗標準認為懲罰性賠償額與實際損失之間應存在一定的比例差距。在Gore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懲罰性賠償額是實際損失的500倍是極其過分的,違反了正當程序條款。但是,這并不意味著500倍就是一個固定的標尺,認為懲罰性賠償額如果等于或者超出實際損失的500倍,就肯定屬于極其過分,低于500倍的懲罰性賠償就不過分。在個案中,還須考慮其他兩個因素,進行綜合考量。聯邦最高法院曾在太平洋互助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訴一案中指出了陪審團的裁決“非常接近”合憲性和非合憲性的臨界點。認為懲罰性賠償的數額如果遠遠超出補償性賠償額的四倍就有可能違反正當程序條款。再次,Gore案檢驗標準遵循相似的案件相似處理原則,認為具體的個案與相似的案件應該給予相似的救濟,不應該差別太大。
3.Philip Morris案檢驗標準。Jesse Williams是一個有著嚴重煙癮的煙民,由于長期吸Philip Morris公司制造的香煙導致得肺癌而死,他的遺孀Mayola Williams將該公司起訴至法院。陪審團認為Philip Morris公司存在過失和欺騙行為,裁定該公司向原告支付821,000美元的損害賠償額和795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額。Philip Morris公司不服,認為陪審團以被告給非當事人的受害者造成損害作為計算部分懲罰性賠償額的依據違反了美國憲法正當程序條款。對于此案,聯邦最高法院明確指出,陪審團不能基于被告給非當事人造成的傷害而懲罰被告,否則,將屬于“非經正當程序而從被告方拿走‘財產”。但是同時也指出,那種可能給多數人造成危害的行為與可能給少數人造成危害的行為相比,前者更應該受到譴責,因此陪審團在確定可譴責程度時可以適當考慮這些因素。
Philip Morris案檢驗標準與前兩種檢驗標準相比。具有明顯的差別。前兩種檢驗標準主要明確可以基于哪些因素決定是否懲罰被告以及懲罰到何種程度?Williams案檢驗標準認為,從警示他人實施侵權行為、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的角度考慮,應該懲罰被告。Gore案檢驗標準則認為被告行為的可譴責性是懲罰被告的前提基礎和重要影響因素。但是,Philip Morris案檢驗標準關注的不是如何懲罰被告。而是明晰法律關系和明確被告的責任,不盲目懲罰被告,強調對被告的懲罰應僅限于所涉案件的當事人之間。
綜合三種不同的檢驗標準,可以看出,Williams案檢驗標準強調懲罰性賠償的社會示范作用,Gore案檢驗標準突出懲罰性賠償制裁侵權者違法行為的功能,Philip Morris案檢驗標準則認為,懲罰性賠償應該罰當其所,在發揮其威懾功能的同時,應將懲罰控制在涉案的范圍內,不能將懲罰延伸至侵權者對非當事人實施的違法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種檢驗標準都是在懲罰性賠償案件中確立的,并沒有涉及法定賠償案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些檢驗標準不能適用于法定賠償案件。Nancy Gortner法官在審理Tenenbaum案時,即運用了Gore案檢驗標準,認為“聯邦最高法院在懲罰性賠償判例法中闡述的正當程序原則與Tenenbaum案件有關聯。”將Gore案的三個檢驗標準運用到這個案件中是適當的,于是將原法定賠償數額削減了90%,Tenenbaum只需賠償6.75萬美元。在Zomba企業有限公司訴全景唱片公司一案中,法院在判決的附帶意見中也明確指出,這些判例可以適用于法定賠償案件。當然,也有法院認為,被告依據Gore案檢驗標準對法定賠償額提出異議是“弄錯了位置”。因此,在美國,懲罰性賠償檢驗標準可否用于法定賠償案件仍有爭議。
(二)法定賠償適用檢驗標準(UMG案檢驗標準)
2000年,MP3.Com購買了幾家唱片公司的數以千計的流行歌曲CD,將其轉錄成Mp3格式并復制在起電腦主機上允許MP3.Com的用戶通過聯機系統播放未經授權的錄音資料。盡管系統用戶已經擁有CD。法庭依然裁定MP3公司屬于確實知道其違反了版權法,構成故意侵犯UMG唱片公司的錄音著作的版權。在該案中,法院忽略了Gore案檢驗標準,創設了自己的法定賠償檢驗標準。該標準包括:(1)將被告侵權的規模和范圍與潛在危害結合起來;(2)被告在申訴和審判期間可以減輕處罰的行為;(3)被告的規模和金融資產狀況;(4)在決定按每張CD為計算單位評估損害賠償之前,考慮對未出庭當事人的威懾。
UMG案檢驗標準通過綜合考量被告的情況,檢驗法定賠償額是否過分,既考慮到了對被告潛在侵權和未出庭當事人的威懾,也考慮到了被告減輕處罰的情節。不僅如此,UMG案檢驗標準還考慮到了被告的經濟承受能力。與上述三種懲罰性賠償檢驗標準相比,UMG案檢驗標準明顯減弱了懲罰性色彩,在追求法定賠償威懾功能的同時,也特別關注被告可以減輕處罰的行為。在UMG案檢驗標準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將一張CD視為一部作品作為法定賠償的計算標準。這種計算標準對被告極其有利。可以大幅降低法定賠償的數額。
五、美國版權法定賠償的計算標準
依據美國版權法第504條(c)款(1)項的規定,計算法定賠償額時以每部作品作為計算標準,同時特別規定,一部編輯作品的所有部分構成一部作品。每部作品的計算標準是美國版權法定賠償的一大特色,在司法實踐中,比較容易操作。不過,為了避免采用這種計算標準導致法定賠償額過高,對被告不公,于是版權法規定,由多個獨立作品集合而成的編輯作品只被視作一部作品。在果園企業案中,音樂唱片專輯被當作編輯作品,構成一部作品,因此,版權人只能獲得一個法定賠償,被告的賠償責任得以大幅減少。正因為如此,編輯作品的計算標準容易成為法定賠償中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問題,法院對此問題也持不同意見。
以音樂專輯為例,有的法院直接判決認定音樂專輯是編輯作品。這意味著,按照美國版權法的規定,音樂專輯作為編輯作品只能獲得一個法定賠償。有的法院則認為,如果侵權作品由原告以專輯的形式發行,那么法定賠償就應該以每張專輯為計算標準。與前一種觀點相比,后者增加了一個“以專輯的形式發行”的限定性條件。也就是說,按照后一種觀點,并非所有的專輯都能被當作一部作品看待。如果專輯里的歌曲最初并不是以專輯的形式發行,而是每首歌曲單獨發行,那么該專輯就不能當作一部作品計算法定賠償,而應該以專輯中的每首歌曲作為計算標準。因此,按照后一種觀點,歌曲的最初發行方式決定著法定賠償的計算標準。
不僅作品的最初發行方式決定著編輯作品法定賠償的計算標準,編輯作品的構成部分的性質也會決定著法定賠償的計算標準。第一巡回法院曾在Gamma Audio案中指出,如果一部作品是一部由多部分構成的整體作品的一部分且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而且是可行的”,那么為了計算法定賠償,可將其看作一部獨立的作品。也就是說,只要編輯作品的構成部分具有獨立的經濟價值,而且是作品,這些構成部分就可以分別獲得法定賠償。有的法院則不贊同這種“獨立經濟價值”決定論,認為“獨立經濟價值”決定論完全是對國會“為了計算法定賠償,編輯作品的所有構成部分都被視為一部作品”規定的嘲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還有其他三個巡回法院也采納“獨立經濟價值”決定論,但是至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法院將該理論運用到音樂專輯的案件中。也就是說,即使有些法院對部分編輯作品采取“獨立經濟價值”決定論,將具有獨立經濟價值的構成部分作為獨立的作品來分別計算法定賠償額,但是這部分編輯作品并不包括音樂專輯,音樂專輯的所有構成部分一直被當作一部作品計算法定賠償額。
責任編輯王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