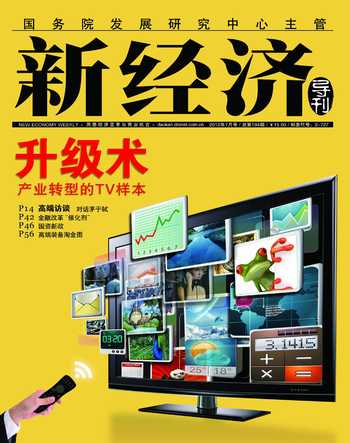期待新的改革共識
吳敬璉
為什么“十二五”規劃提出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原因可能有二:一個原因是不少人以為中國改革從來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方案的設計,一直停留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水平上,而不了解中國改革在上個世紀已經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現在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另外一個原因是本世紀初出現了另一種“頂層設計”,需要來比較哪一種“頂層設計”更加符合中國實際,更加正確和更加有可能成功。
明確未來改革方向
在我看來,說我們直到現在還在“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誤解。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做法,“走一步看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從決策層到經濟學家和社會大眾,都認識到改革總是摸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就提出了一個“頂層設計”的問題。不過當時不叫“頂層設計”,而叫做“目標模式”。
20世紀末建立起來的中國市場經濟初步框架,還存在很大缺陷。這一方面表現為它還保留著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若干重要因素,其中集中表現為,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國有經濟對市場的控制。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須的法治沒有建立起來。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不斷受到來自支持舊體制和舊路線人們的質疑和反對。隨著腐敗猖獗和貧富分化加劇,一些支持舊路線和舊體制的人們提出的“藥方”或者叫做另一種“頂層設計”,就是動用國家機器來制止腐敗和貧富分化;同時運用政府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靠海量投資來營造炫人耳目的政績。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強,尋租的制度基礎就越大,腐敗也就更加嚴重;而腐敗越是嚴重,在某種錯誤的輿論導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強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控制力。
后一種“頂層設計”的初始形態叫“北京共識”,后來則被稱為“中國模式”。其主要內容是依靠強政府、大國企,用海量投資來支持高速增長。這種政府主導的發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從西方各國政府短期政策中得到鼓舞。其“優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業績的支持。實踐中還出現了一些“樣板工程”,例如被“中國模式”的支持者所盛稱的“高鐵奇跡”,還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強力動員和大量注入資源實現的超高速發展等等。
于是就出現了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還是國家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的“頂層設計”之間的選擇問題。在我看來,“十二五”重新提出“頂層設計”的問題,其實質是明確未來改革的正確方向。
爭取形成新的共識
近幾年事態的發展表明,出現了總結不同“頂層設計”之爭,形成新的“改革共識”的可能性。
首先,近些年來,通過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分析和討論,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其次,近來,那些采取“強政府、大國企”模式發展經濟的部門和地方這種模式所造成的種種嚴重后果正在顯露出來。因此,近來朝野上下推進全面改革的呼聲開始提高,甚至出現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識”的可能。
這一新的改革共識不是脫離過去的基礎重起爐灶,而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比如說上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小平“南方講話”以后形成的新的改革高潮存在著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1992年以后就不再像過去那樣,把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并提。事實上,中國改革進程中落后的方面,包括政府職能明確界定和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調整,都涉及到政治改革。正如小平在1986年講過多次的,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改革也落實不了。
“十二五”規劃要求“更加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所說的“改革”,是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改革”,因此,我們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也應當不是某個單項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而是全面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目前,各界人士正在對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進行熱烈的討論。對于經濟改革總體規劃的討論,大體上涉及三個領域:一個是私用品領域,即“競爭性領域”,包括市場開放、國有經濟布局調整、農地改革、金融改革等項目;一個是公共領域,包括財稅改革、民間組織發展等;還有一個是市場監管,包括從實質性審批到合規性監管、反壟斷執法等。
對于政治改革的討論,也大體上涉及三個領域:一個是法治,一個是民主,一個是憲政。至于三者具體包括哪些內容,它們應當有重點地進行,還是協同推進,這些問題,都還有待深入地討論。
和基層創新相結合
社會經濟體制作為一個巨型的系統,為了保證各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和互動,必須要有從上到下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但是,進行頂層設計一定要傾聽民眾訴求,與從下到上的創新相結合,從地方政府主動探索獲得啟發和經驗。
現在已經出現了一些地方的改革試驗。比如上海從前幾年起就要求國有資本退出幾十個競爭性行業,而且每年都要檢查落實情況。增值稅擴圍試點,也是上海市最先提出的,這項對發展我國的服務業很有意義的改革,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國家財稅部門的積極響應,有望加快增值稅最終向消費型轉型的步伐。
還有廣東省的一些體制創新也很值得注意。一個是從2010年開始,時任廣州市委書記的朱小丹(現任廣東省省長)提出應該用“非禁即入”取代“準入”制度。現在他們已經獲準進行寬松商務登記制度的試點。再比如深圳試水創新的民間組織無主管設立,現在已經在廣東全省實施,實施效果很好,包括國家民政部的一些官員們也認為這樣的做法是有益無害的。再有就是村民自治的選舉制度。這本來是我國現有法律明文規定的制度,但是事實上絕大部分地方都沒有很好地執行,現在廣東烏坎樹立了一個好的范例,也有可能減少今后推廣的阻力。
許多基層的制度創新,往往都能為整體改革提供重要的方向提示和實施經驗,甚至本身就具有全局意義。我們應當熱情支持,使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更好地結合起來,協力推進改革。這樣,中國就必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難,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重顯輝煌。
(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歡迎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