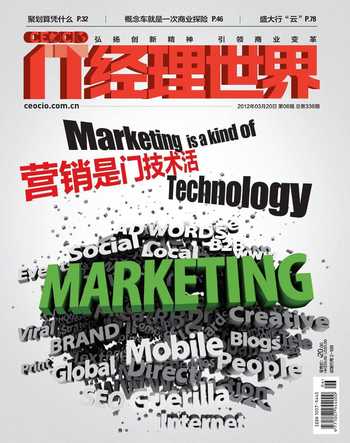我們造就空間,空間也造就我們

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最早發現空間的變化:法國人類學家馬克·奧吉在談論所謂“非場所”(non-place),著名的網絡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在談論“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前者類似于在現代化社會中像機場、旅館這樣的流動性空間;再進一步,進入到虛擬空間中,這個時候你會發現越來越不能用原來空間那個定義了。因為原來的“空間”首先具有一定歷史繼承性,歷史會給某個空間賦予特定的意義,但進入到信息空間當中,它的歷史負載越來越少,導致這個空間的質量——也就是重量——越來越輕。
奧吉說的“非場所”有重大缺失:既不和活動于其中的人們建立關系,更和人們的身份無關。這都是對應著傳統的“場所”來說的,這種場所有三個特點:它處于社會關系之中;它具有歷史;它能夠賦予人們身份。然而,今天的Cyberspace(網絡空間),不僅在重新建構人們的社會關系,而且越來越成為身份認同的來源。
當人們享受Cyberspace的時候,容易把它想象成一種平行空間,就是在現實空間以外的“另類空間”(我有一本書就叫這個名字),然后這個另類空間所發生的事情,可能和現實世界的空間聯系不多。最早提出Cyberspace的是科幻小說家威廉·吉布森,他自己回憶說,當年他想到這個詞是因為他在溫哥華街上閑逛時,看到青少年在打街機,他感覺進入電腦游戲空間以后,這些人的靈魂似乎飄到另一個地方。他覺得這種空間是一個難以名狀的、無法把握的空間,所以他決定必須用新詞來概括。
傳統空間是由歷史定義的,虛擬空間不那么具有歷史性,但其實這個空間的發展也有它的歷史,雖然這個歷史是相對短暫的。如果從網絡空間本身的歷史來看,能夠很清楚地看到一個趨勢,就是它可能不是一個平行的空間,而是演變成同目前現實生活高度交叉的空間,換句話講就是越來越多的你以為只在現實空間才能做的事,現在都可以在這個空間里來做,甚至包括做愛。實際上甚至存在一個虛擬空間“反噬”現實空間的場景,這個場景在將來不僅不會削弱,還會進一步加深,從而我們的生活,或者叫生存當中需要加上一個信息空間的維度。
虛擬空間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本身植根于人類社會的技術發展和社會發展,是兩者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此前,我們已征服了所有的物理空間。一開始人類在陸地上,后來去征服海洋,西方的霸權史就是一部征服海洋的歷史。為什么西歐最后會成為全世界的統治者?因為它有“地理大發現”,它有所有的航海家,他們發現了地球的形狀,他們通過“地理大發現”把自己的殖民霸權伸到全世界。最后當整個地球被這么一種探索改寫了以后,人類說我們還有無窮的探索欲望,然后就發展到登月、探測火星。當所有的物理空間都被探索殆盡的時候,我們就發明了虛擬空間。我們要熱烈地去探索這個空間,所以虛擬空間本身的出現是建立在歷史之上的。
我們的城市在虛擬空間出現之前也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城市本來就存在公共空間的私人化和私人空間的公共化。比如說以前孩子基本是在戶外玩的,他是一種自然生長。但是你會發現這個趨勢在走低,因為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復雜,父母們越來越恐懼他們的孩子在公共空間里的安全性。現在基本上孩子是一個孤獨的個體,回到家里,家里的物理空間是沒有辦法跟廣闊的公共空間相比的,因此你會看到孩子們更多的是沉浸在虛擬空間里的,他看電視,或打電腦。
這個進程早已經發生了。以前沒有購物中心時,大家購物可能到鄰里的夫妻店,你跟他們的關系也比較親密。現在大家都去大商場,誰也不認識誰,這樣下來城市的社會空間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虛擬空間本身并非所有這種變化的始作俑者,它可能會加重這種趨勢,但是前提是人類社會自身的發展,已經把我們自己的空間弄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
虛擬空間中的社會活動,有悲觀的看法,也有樂觀的看法。比如馬克·波斯特認為,當代的社會關系似乎缺乏一種基本層面上的交往實踐,而過去,這種實踐是民主政治的母體,分布在一系列場所:會場、市政廳、村莊教堂、咖啡館、酒館、公園、工廠食堂甚至是街頭的一個拐角。在今天的社會中,上面所說的許多場所仍然存在,但卻不再是政治討論和行動組織的中心了。媒體尤其是電視和網絡似乎將公民彼此隔絕了。但樂觀者不這樣看。在我翻譯的《比特之城》一書中,作者美國建筑學家威廉·米切爾的看法是:“由于全球化計算機網絡破壞、取代和徹底改寫了我們關于集會場所、社區和城市生活的概念,電子會場在21世紀的城市中將會發揮同樣關鍵性的作用。”
胡泳 北京大學,新媒介批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