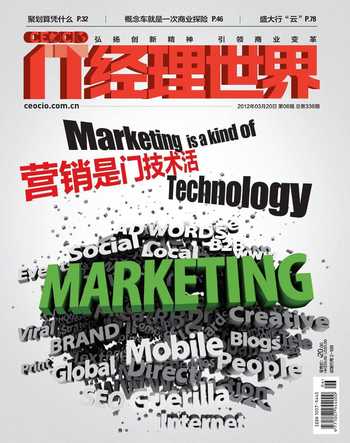汽車圈里的芯片推手



軟件設(shè)計(jì)出身的瑞薩電子大中國(guó)區(qū)汽車電子產(chǎn)品中心總監(jiān)趙明宇早在1999年時(shí)就在承接來自NEC總部(瑞薩電子的前身包含了日立、三菱和NEC半導(dǎo)體部門)的項(xiàng)目開發(fā)中接觸到了汽車電子業(yè)務(wù),曾參與汽車音響編解碼等應(yīng)用系統(tǒng)的設(shè)計(jì),但“直到5年后與汽車電子客戶面對(duì)面打交道時(shí),才真正開始理解汽車電子設(shè)計(jì)理念”。
試探和摸索的過程持續(xù)到四五年前,瑞薩開始在中國(guó)本地開發(fā)汽車電子整體解決方案,并從德國(guó)調(diào)配來車身電子方面的設(shè)計(jì)專家,協(xié)助趙明宇他們的研發(fā)活動(dòng),“第一個(gè)比較大的系統(tǒng)”是步進(jìn)電機(jī)式儀表盤。
當(dāng)時(shí),初涉汽車系統(tǒng)研發(fā)的客戶對(duì)產(chǎn)品“提不出明確的設(shè)計(jì)需求”,雙方不得不在開發(fā)過程中反復(fù)就各種細(xì)節(jié)進(jìn)行探討,不斷明確各種參數(shù)指標(biāo)。例如,如何保障儀表盤上那些由電機(jī)驅(qū)動(dòng)的指針能根據(jù)信號(hào)輸入平滑轉(zhuǎn)動(dòng)?汽車熄火后,指針怎么能自動(dòng)歸零,而不像一些微面那樣在零位處用個(gè)小塑料塊擋著?里程又如何計(jì)數(shù),發(fā)生各種意外時(shí)數(shù)據(jù)如何不丟失?
雖然儀表盤看上去不是個(gè)特別復(fù)雜的系統(tǒng),但對(duì)當(dāng)時(shí)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guó)工程師來說,工作量和復(fù)雜度不亞于今天汽車中那些更高級(jí)的系統(tǒng)。在經(jīng)歷了近兩年的艱苦攻堅(jiān)后,他們終于拿出了交鑰匙方案,目前該方案“國(guó)內(nèi)幾家車廠都在用了”。
無獨(dú)有偶,飛思卡爾和英飛凌在中國(guó)的汽車電子研發(fā)活動(dòng)基本也始于同期。飛思卡爾中國(guó)汽車電子實(shí)驗(yàn)室(Auto Labs)組建于2006年初。成立之初,公司調(diào)配了德國(guó)和英國(guó)的的專家到上海協(xié)助工作。高磊是實(shí)驗(yàn)室最初的4名中方員工之一。從2008年起,他開始負(fù)責(zé)這個(gè)實(shí)驗(yàn)室。他們研發(fā)的第一個(gè)項(xiàng)目也是儀表盤。飛思卡爾的前身是摩托羅拉半導(dǎo)體部門,摩托羅拉在上世紀(jì)20年代創(chuàng)立之初生產(chǎn)的第一個(gè)產(chǎn)品就是汽車收音機(jī),現(xiàn)在汽車芯片業(yè)務(wù)占飛思卡爾營(yíng)業(yè)額的1/3以上。
而英飛凌在中國(guó)的技術(shù)團(tuán)隊(duì)是從車身電子起步的。英飛凌的前身是西門子半導(dǎo)體部門,從 50年前“第一顆晶體管進(jìn)入汽車”開始就伴隨歐系車廠開展汽車業(yè)務(wù),目前已是全球第一大汽車半導(dǎo)體供應(yīng)商。
特殊的生態(tài)圈
值得注意的是,半導(dǎo)體公司在中國(guó)的主要研發(fā)活動(dòng)并不是芯片設(shè)計(jì),而是基于芯片的系統(tǒng)解決方案。這與中國(guó)汽車生態(tài)圈的特殊性有關(guān)。
在汽車生態(tài)圈中,處于中心的是車廠,外邊一圈是為車廠提供系統(tǒng)的博世、德爾福、大陸等一級(jí)供應(yīng)商(Tier1),再外邊一圈是半導(dǎo)體供應(yīng)商(一般是Tier2)。在國(guó)外,車廠和Tier1的技術(shù)實(shí)力足夠強(qiáng)大,他們并不需要半導(dǎo)體公司提供系統(tǒng),三者之間是專業(yè)化分工。但在中國(guó),無論車廠還是本地/跨國(guó)Tier1都還在成長(zhǎng)中,有時(shí)半導(dǎo)體公司要想賣器件就必須提供系統(tǒng)方案。
而且,一些本土車廠近幾年來愈發(fā)重視與半導(dǎo)體企業(yè)的研發(fā)合作,這其中深層次的原因是迫于技術(shù)和成本方面的博弈考慮。對(duì)于國(guó)內(nèi)車廠來說,Tier1提供的系統(tǒng)就像一個(gè)“黑匣子”,他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曾經(jīng)有一家車廠需要解決發(fā)動(dòng)機(jī)的一個(gè)問題,他們?cè)赥ier1面前甚至說不清這個(gè)究竟是自己的責(zé)任還是Tier1的問題。
同時(shí),車廠對(duì)“黑匣子”的成本構(gòu)成也一無所知,Tier1要多少,他們就得給多少。這對(duì)于每年需要把成本降低8%左右才能抵消車輛價(jià)格下降的車廠來說非常不利。現(xiàn)在,與半導(dǎo)體公司的研發(fā)合作,讓車廠找到了博弈的籌碼。一旦完成某個(gè)系統(tǒng)的研發(fā),他們就了解了其中技術(shù)和成本的構(gòu)成,在Tier1面前就有更多的話語權(quán),可以避免技術(shù)上扯皮的事,也能壓低成本。因此,目前大多數(shù)國(guó)內(nèi)車廠一方面有自己的配套廠與半導(dǎo)體公司合作開發(fā)系統(tǒng),另一方面也外購第三方系統(tǒng),在成本控制上更為靈活。
而像電動(dòng)汽車這樣的特殊類別,還要考慮政策推手的因素。中國(guó)政府對(duì)電動(dòng)汽車的補(bǔ)貼政策提出,車廠要想拿到國(guó)家補(bǔ)貼,要對(duì)電動(dòng)汽車的3個(gè)核心模塊——電機(jī)和電機(jī)驅(qū)動(dòng)系統(tǒng)、電池和電池管理系統(tǒng)以及整車控制系統(tǒng)中的至少一個(gè)擁有自主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為此,車廠需要充當(dāng)自己的Tier1開發(fā)至少一個(gè)核心系統(tǒng)。例如福田在做電池和電池管理系統(tǒng),北汽新能源在做整車控制器——為此,他們不得不尋求半導(dǎo)體公司的合作。
此外,近幾年來,半導(dǎo)體器件在汽車中的總價(jià)值已從先前幾百美元/車的平均水平快速提升。特別是在電動(dòng)汽車中,一個(gè)IGBT(絕緣柵雙極型晶體管)的價(jià)值就達(dá)到三四百歐元,IGBT與電機(jī)組成的模塊,地位相當(dāng)于發(fā)動(dòng)機(jī)——這是車廠必須掌控的核心部件,因此車廠與半導(dǎo)體企業(yè)互動(dòng)增強(qiáng),使得傳統(tǒng)商業(yè)模式發(fā)生變化。
當(dāng)然,一些咨詢公司如博斯公司預(yù)測(cè),未來10年,中外合資車廠可能會(huì)分道揚(yáng)鑣以求更好的發(fā)展,如果現(xiàn)在只做生產(chǎn)本地化,再照搬國(guó)外產(chǎn)品技術(shù),將使其自身岌岌可危。
種種因素綜合在一起,推動(dòng)了原本在第二層級(jí)的半導(dǎo)體公司在中國(guó)的系統(tǒng)研發(fā)業(yè)務(wù),而這些也在推動(dòng)中國(guó)本地汽車行業(yè)的快速演進(jìn)。
殊途同歸
最近幾年,無論本土/合資車廠,還是本土和跨國(guó)Tier1,都試圖摸索在中國(guó)研發(fā)業(yè)務(wù)的定位和訴求。一些本土車廠,例如奇瑞和比亞迪,希望掌控更多話語權(quán),因此,他們的研發(fā)活動(dòng)滲透到系統(tǒng)和半導(dǎo)體層面;一些外資車廠,例如通用,他們的全球戰(zhàn)略是在每個(gè)市場(chǎng),技術(shù)研發(fā)要本地化以更貼近當(dāng)?shù)氐男枨螅虼耍麄儗で笈c中國(guó)本土Tier1合作,這些本土Tier1就會(huì)找到相應(yīng)的半導(dǎo)體公司開展研發(fā)合作;還有一些合資車廠,他們認(rèn)為全球研發(fā)要基于一個(gè)平臺(tái),在這樣的框架下,他們與老搭檔——國(guó)際Tier1合作更為高效,這些國(guó)際Tier1也伴隨這些車廠進(jìn)入中國(guó),他們?cè)谥袊?guó)的研發(fā)也需要與半導(dǎo)體公司溝通與合作。
無論是哪種研發(fā)定位,半導(dǎo)體公司在中國(guó)的研發(fā)比重都在增加,他們的中國(guó)團(tuán)隊(duì)也更有機(jī)會(huì)快速地接觸到重大研發(fā)項(xiàng)目。
2008年,一家國(guó)際Tier1決定在上海研發(fā)發(fā)動(dòng)機(jī)控制技術(shù),需要一種“標(biāo)定工具”,就是一個(gè)可以對(duì)發(fā)動(dòng)機(jī)幾千個(gè)參數(shù)進(jìn)行微調(diào)的工具,可以將發(fā)動(dòng)機(jī)調(diào)試到最高效狀態(tài)。為了配合這家供應(yīng)商在上海的研發(fā),高磊接下了飛思卡爾總部分配來的“標(biāo)定工具”研發(fā)任務(wù)。雖然這對(duì)介入汽車電子僅兩年的高磊像“一下子跳到深水區(qū)”,但在全球資源的大力協(xié)助下,這個(gè)項(xiàng)目最終取得成功。“標(biāo)定工具”如今通過國(guó)際那家Tier1賣給了多家車廠,也成功輸出海外。
2009年,高磊的團(tuán)隊(duì)協(xié)助奇瑞研發(fā)動(dòng)力總成技術(shù)。通俗地說,動(dòng)力總成就是發(fā)動(dòng)機(jī)和變速箱等綜合技術(shù),是汽車的“心臟”。此前,歐Ⅳ標(biāo)準(zhǔn)剛剛在國(guó)內(nèi)部分城市推出,這在車企中掀起了新一輪綠色熱潮——開發(fā)更省油、排放更清潔、價(jià)格更低的發(fā)動(dòng)機(jī)控制系統(tǒng)。
高磊團(tuán)隊(duì)在這個(gè)合作項(xiàng)目中負(fù)責(zé)硬件和底層的驅(qū)動(dòng):在發(fā)動(dòng)機(jī)控制系統(tǒng)中有多達(dá)二三十種傳感器——凸輪軸、溫度、大氣壓力、油壓、爆震傳感器等,這些傳感器實(shí)時(shí)采集數(shù)據(jù)送到微控制器(32位MCU)中,經(jīng)過處理分析再對(duì)發(fā)動(dòng)機(jī)發(fā)出控制指令,讓發(fā)動(dòng)機(jī)達(dá)到最高效。這個(gè)系統(tǒng)甚至可以分析駕駛員的駕駛習(xí)慣,了解駕駛員“踩油門”的意圖是“需要加速還是保持平順”,以此來對(duì)算法微調(diào),做到更省油。設(shè)計(jì)中的一個(gè)難點(diǎn)是“爆震算法”——使汽油燃燒時(shí)減少對(duì)氣缸和活塞的損壞。高磊他們?yōu)榇俗隽舜罅磕P脱芯浚谄嫒鸷偷聡?guó)汽車工程學(xué)院碩大的發(fā)動(dòng)機(jī)臺(tái)架上,雙方對(duì)上千個(gè)參數(shù)進(jìn)行反復(fù)調(diào)試,尋找最高效的算法。并最終將爆震算法集成到了MCU中,節(jié)省了原來一般系統(tǒng)中都有的一顆專用芯片。這個(gè)項(xiàng)目持續(xù)了18個(gè)月,終于在2010年完成。目前,奇瑞正在對(duì)這個(gè)系統(tǒng)進(jìn)行苛刻的季節(jié)測(cè)試,今年年底可能會(huì)上路。

英飛凌的故事則從另一個(gè)側(cè)面折射了在中國(guó)做研發(fā)的定位問題。媒體前兩年曾報(bào)道過“重慶力帆集團(tuán)董事長(zhǎng)尹明善年過7旬開始賣技術(shù)”的消息,這其實(shí)源自力帆與英飛凌合作研發(fā)的摩托車電噴解決方案。幾年前,市場(chǎng)上的摩托車大多還是化油器的,但因應(yīng)國(guó)Ⅲ標(biāo)準(zhǔn)的排放要求,摩托車也要使用電噴系統(tǒng)。這對(duì)于占全球產(chǎn)量一半以上的中國(guó)摩托車行業(yè)來說是個(gè)關(guān)鍵性轉(zhuǎn)變。
“在此之前,力帆的工程師已經(jīng)開發(fā)了將近10年。”英飛凌中國(guó)區(qū)汽車電子事業(yè)部總監(jiān)劉魯偉說。英飛凌與力帆合作開發(fā)了近兩年,在此期間,他們根據(jù)力帆的需求設(shè)計(jì)了一款摩托車電噴專用芯片,并將以前需要三四顆芯片的電噴方案簡(jiǎn)化到兩顆。之后,英飛凌向力帆購買了這個(gè)電噴技術(shù)方案,以向其他國(guó)家推廣。力帆過去在購買技術(shù)上花了上億元,而這個(gè)技術(shù)輸出帶來的轉(zhuǎn)折曾令尹明善徹夜難眠。
現(xiàn)階段,英飛凌正與北汽福田聯(lián)合研發(fā)電動(dòng)汽車電池管理系統(tǒng)。電動(dòng)汽車的電池電壓高達(dá)336V,里面有很多“電池包”,這次雙方合作設(shè)計(jì)的方案是智能化的——根據(jù)不同電池單元的電池狀況來分別充放電,這可延長(zhǎng)電池壽命,也可改善電池效率。由于電動(dòng)汽車尚屬一個(gè)全新領(lǐng)域,大量設(shè)計(jì)工作都是全新的,雙方在此期間要做大量嚴(yán)謹(jǐn)?shù)膶?shí)驗(yàn)。
劉魯偉觀察到,國(guó)內(nèi)汽車電子起步于車身電子和娛樂系統(tǒng),但現(xiàn)在,汽車上任何電子系統(tǒng)都有中國(guó)人在開發(fā),雖然這些方案在市場(chǎng)上的占有率還參差不齊——發(fā)動(dòng)機(jī)仍由國(guó)外幾大公司控制,國(guó)內(nèi)企業(yè)份額不到10%,但在車身方面,本土企業(yè)市占率已經(jīng)很高了。
這得到瑞薩趙明宇的印證,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國(guó)內(nèi)在車身電子上的發(fā)展速度”。幾年前,他們剛介入這個(gè)領(lǐng)域時(shí),國(guó)內(nèi)車企對(duì)于BCM(車身控制模塊)和網(wǎng)關(guān)的應(yīng)用理念剛剛成型, 國(guó)產(chǎn)車搭載的也只是只有兩路CAN(汽車中的一種通信線路)的、在功能邏輯上較為簡(jiǎn)單的BCM系統(tǒng), 但如今,帶有診斷功能的多路獨(dú)立式網(wǎng)關(guān)已經(jīng)在國(guó)內(nèi)很多本土設(shè)計(jì)的車型上廣泛使用,結(jié)合網(wǎng)關(guān)應(yīng)用的BCM以及所有國(guó)際先進(jìn)車身設(shè)計(jì)理念都在中國(guó)車廠和一級(jí)供應(yīng)商中出現(xiàn)。五路CAN系統(tǒng)已進(jìn)入量產(chǎn)階段,六路CAN系統(tǒng)的設(shè)計(jì)已經(jīng)開始。這意味著汽車電子化、網(wǎng)絡(luò)化程度比以前高出很多。
待解難題
不過,雖然研發(fā)速度推進(jìn)很快,國(guó)內(nèi)汽車電子行業(yè)仍面臨很多困惑,例如如何理解汽車電子技術(shù)研發(fā)的獨(dú)特性、如何去更好地鼓勵(lì)新興技術(shù)、車企如何科學(xué)地制定技術(shù)發(fā)展規(guī)劃帶動(dòng)整個(gè)產(chǎn)業(yè)鏈的正向循環(huán)等等。
在上海的辦公室中,劉魯偉回顧這些年曾經(jīng)親身管理過的研發(fā)項(xiàng)目時(shí)說,“每個(gè)項(xiàng)目都挺不容易的,都會(huì)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不過,最令客戶和他感到困惑的是,有時(shí)侯他們歷盡千辛萬苦一起開發(fā)出的技術(shù),在市場(chǎng)上卻得不到預(yù)期的回報(bào)。就拿與力帆合作開發(fā)的摩托車電噴技術(shù)來說,2009年國(guó)內(nèi)針對(duì)摩托車的排放法規(guī)就已出臺(tái),可是因?yàn)槿珖?guó)各地執(zhí)行力度并不均衡,市場(chǎng)上仍有很多陳舊方案在用。市場(chǎng)上電噴方案的成本比化油器方案高出20%到30%——大約貴出兩三百元,很多廠家并不愿為電噴方案埋單。“技術(shù)解決了,但因?yàn)橐蚨唐诶嫱讌f(xié),導(dǎo)致市場(chǎng)解決不了,排放解決不了,新興技術(shù)也得不到鼓勵(lì)。”
趙明宇同樣也感受到一個(gè)突出問題——產(chǎn)業(yè)鏈的正向循環(huán)。來自德國(guó)的同事曾對(duì)他評(píng)論說,中國(guó)的車廠還很難清楚地說出自己今后5年的技術(shù)規(guī)劃。但以德國(guó)車廠為例,他們可以把今后10~15年內(nèi)的產(chǎn)品平臺(tái)定義得非常清晰——“當(dāng)寶馬在生產(chǎn)這一代盈利產(chǎn)品時(shí),其下一代平臺(tái)已經(jīng)規(guī)劃好了”。這樣以來,寶馬周邊的一二級(jí)供應(yīng)商就不需要“盲目地猜”,而只需依照車廠的技術(shù)規(guī)劃配合研發(fā)和生產(chǎn)即可。
以車身電子為例,如果車廠定義了下一代平臺(tái)要集成鳥瞰系統(tǒng),整個(gè)車身控制模塊的設(shè)計(jì)就要發(fā)生變化,芯片性能要全面升級(jí),還要考慮網(wǎng)絡(luò)接口。但國(guó)內(nèi)車廠的規(guī)劃很多還停留在“龐大的銷售數(shù)量上”,技術(shù)規(guī)劃不清晰也不細(xì)致,導(dǎo)致一、二級(jí)供應(yīng)商無法有效配合。
還有一個(gè)涉及面很廣的問題就是國(guó)內(nèi)企業(yè)對(duì)汽車電子研發(fā)的認(rèn)識(shí)和心態(tài)——汽車電子做出來不難,但難在把它做得成熟可靠。一個(gè)廣為流傳的故事是:國(guó)內(nèi)一家企業(yè)的技術(shù)負(fù)責(zé)人曾說,做電動(dòng)汽車并不難,現(xiàn)在市場(chǎng)上有兩個(gè)輪子的電動(dòng)自行車,再加一個(gè)輪子就是電動(dòng)三輪車,再加個(gè)輪子不就是電動(dòng)汽車了嗎?
雖然這樣“在戰(zhàn)略上藐視敵人的做法無可厚非”,但汽車行業(yè)人命關(guān)天,與消費(fèi)電子領(lǐng)域差別巨大。電動(dòng)自行車的電池電壓在60V以下,但電動(dòng)汽車電池電壓高達(dá)336V,從電壓、電流、行駛速度等方面說,兩個(gè)系統(tǒng)都不可同日而語。但不幸的是,抱持類似技術(shù)心態(tài)的企業(yè)非常多。
恰恰“耐心”是介入汽車電子商業(yè)運(yùn)作的企業(yè)必須具備的關(guān)鍵素質(zhì)。汽車電子不同于消費(fèi)電子“今年開發(fā)、今年量產(chǎn)”的快節(jié)奏,它在投入的前四五年中基本都是“零產(chǎn)出”。
新熱潮
去年是電動(dòng)汽車發(fā)展的一個(gè)低谷,幾輛電動(dòng)汽車發(fā)生了燃燒事故,所有車企都沒有什么出貨量,一些瓶頸問題還未得到解決。劉魯偉認(rèn)為,電動(dòng)汽車正處在一個(gè)“黎明前的黑暗期”,這正是一個(gè)需要耐心做研發(fā)的時(shí)期。“國(guó)外也是這樣,無論是北美還是歐洲,大家都沒有放棄”。
今年初,劉魯偉升任英飛凌(北京)有限公司執(zhí)行董事,將把工作重心移至北京。去年初,英飛凌汽車研發(fā)團(tuán)隊(duì)已從上海擴(kuò)展到北京,同期,英飛凌也在北京設(shè)立了大功率器件封裝工廠和相關(guān)實(shí)驗(yàn)設(shè)施,這讓北京研發(fā)團(tuán)隊(duì)有更多資源專注于電動(dòng)汽車的電機(jī)驅(qū)動(dòng)技術(shù)。繼電池管理等解決方案之后,今年他們將會(huì)繼續(xù)開發(fā)車載充電器,實(shí)現(xiàn)插入式電動(dòng)汽車的充電;還有車內(nèi)直流轉(zhuǎn)換器,可以把336V的汽車電池電壓轉(zhuǎn)換成汽車內(nèi)各部分需要的工作電壓。
除了電動(dòng)汽車,劉魯偉他們看到,伴隨節(jié)能減排、汽車安全完整性等級(jí)(ASIL)概念推廣以及2011年開始執(zhí)行的GB/T26149(汽車輪胎氣壓監(jiān)測(cè)標(biāo)準(zhǔn))等法規(guī)的推進(jìn),汽車電子的一輪新熱潮正滾滾而來。
高磊指著一張去年他們團(tuán)隊(duì)在美國(guó)一個(gè)技術(shù)研討會(huì)上的合影向記者逐一介紹著團(tuán)隊(duì)成員。在這個(gè)平均年齡30出頭的團(tuán)隊(duì)中,一些人在行業(yè)中已有相當(dāng)知名度。今年,這個(gè)團(tuán)隊(duì)將圍繞汽車安全技術(shù)展開更多的研發(fā)。去年11月, ISO26262國(guó)際標(biāo)準(zhǔn)推出,這是一個(gè)提高汽車電子功能安全的國(guó)際標(biāo)準(zhǔn),“這使得國(guó)內(nèi)在安全方面熱情更高”。為此,高磊他們會(huì)投入研發(fā)EPS(電子助力轉(zhuǎn)向)、安全氣囊、ABS(防抱死剎車系統(tǒng))等解決方案。下半年,他們還可能嘗試一些有預(yù)測(cè)性的安全系統(tǒng)——ADAS(高級(jí)駕駛輔助系統(tǒng)),這種系統(tǒng)包含自適應(yīng)巡航控制、前景停車輔助系統(tǒng)、駕車者監(jiān)控等技術(shù)。
而趙明宇團(tuán)隊(duì)今年的重點(diǎn)是節(jié)能和安全技術(shù),其中也包括了ADAS。同時(shí),由于日本車企已經(jīng)開始量產(chǎn)電動(dòng)汽車,為這些電動(dòng)汽車提供方案的瑞薩電子還將逐步與中國(guó)企業(yè)展開相關(guān)的研發(fā)合作。
由于汽車是一個(gè)非常復(fù)雜的工程系統(tǒng),在完成系統(tǒng)研發(fā)后,需要先進(jìn)的經(jīng)驗(yàn)和技術(shù)來測(cè)試和驗(yàn)證這些系統(tǒng)能否在安全、省油、性能和質(zhì)量上實(shí)現(xiàn)所設(shè)定的基準(zhǔn)目標(biāo),這是中國(guó)公司目前非常欠缺的,演進(jìn)也將比較緩慢。
在技術(shù)層面變化的同時(shí),中國(guó)汽車生態(tài)圈未來幾年可能會(huì)發(fā)生一些組織形態(tài)上的重大變化。目前,中國(guó)有整車廠150家,配套廠3000~4000家,而歐洲的數(shù)字分別是十幾家和一二百家。過于分散的產(chǎn)業(yè)鏈在成本競(jìng)爭(zhēng)日益加劇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下可能會(huì)被迫整合。
不過,對(duì)汽車制造熱情高漲的各地政府來說,整合似乎并不容易實(shí)現(xiàn),而且每家車廠都希望在自己周邊建立完整的配套產(chǎn)業(yè)鏈。在這種典型的中國(guó)環(huán)境中,如何建立一個(gè)高效的汽車產(chǎn)業(yè)鏈體系,仍然是中國(guó)汽車生態(tài)圈要面臨和思考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