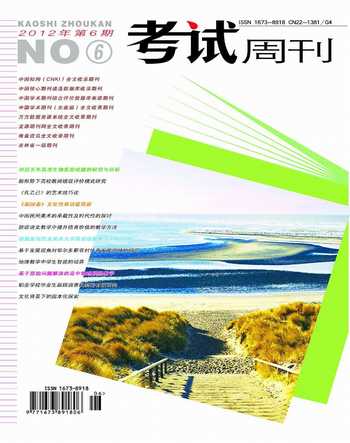女性哥特在《弗蘭肯斯坦》中的滲透
王曦
摘要: “女性哥特”被闡釋為體現以男權為主導的性別身份觀對女性個體造成的影響的有效載體。“女性哥特”恐懼的源泉就在于女性對自身性別身份的焦慮,在父權社會受到的禁錮。《弗蘭肯斯坦》通過塑造怪物這一形象與男權社會的代表弗蘭肯斯坦的斗爭,集中體現了這種矛盾。同時,利用“封閉意象”體現了女性所處的現實環境。女性哥特小說是時代的產物。
關鍵詞: 女性哥特小說《弗蘭肯斯坦》怪物性別身份封閉意象
一、引言
哥特小說屬于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個特殊流派,是一種恐怖和鬼怪小說,是“歷史傳奇的一種特殊形式,一種關于過去歷史與異域文化的幻想形式”,被評論家們稱為“黑色小說”。在情節上,它濃墨重色彩渲染暴力與恐怖;在主題思想上,它不是像一般浪漫主義那樣側重于正面表達其理想的社會、政治和道德觀念,而主要是通過揭示社會、政治、教會和道德的邪惡,揭示人性中的陰暗面來進行深入的探索,特別是道德上的探索。而“女性哥特”是哥特小說的一個特殊層面。她更加注重作品的現實主義特征,以哥特題材為載體,探究在父權制下女性的共同問題,如兩性關系、自卑情節、恐懼源泉、身份焦慮、女性意識、負性生存狀態等。
二、“女性哥特”定義的闡釋和產生背景
“女性哥特”這個詞語最早是英國女性主義文學評論家Ellen Moers在其著作《文學女性:偉大的作家》(1976)一書中提出:“18世紀以來女性作家創造的哥特小說。”她把哥特流派整體的核心界定在“恐懼”這種特殊的生理和心理閱讀體驗上,認為“女性哥特”恐懼的源泉就在女性對自身性別身份的焦慮,同女性在父權制度社會特有的成長經歷息息相關,影響到女性個體成長過程的各個階段。
女性哥特文本的切入點是密閉的空間意象,這個封閉意象既象征著禁錮女性自我的父權社會,又是父權文化壓抑下女性作家個人情感體驗的載體。Juliann Fleenor認為這是理解女性作家筆下的哥特小說的關鍵,Fleenor在文集的導言中對“女性哥特”做出定義:“它基本上是無形的,除非是作為一個尋找過程:它利用了破敗的古堡或封閉的房間等傳統空間意象來象征文化和女主人公二者;作為一種心理形式,它激發恐懼,憤怒,敬畏等各種情感,又是引發女性對自身性別角色,女性性欲,女性生理和生殖的恐懼和憎惡;它往往采用一種質疑敘事本身的合理性的敘事形式。它反映的是這樣一種范式,父親在場而母親缺席女性由于不是男性而殘缺不全。”其定義正是圍繞文本的主題特征展開的。
女性作家在哥特小說中更注意對環境處理上,充滿了“壯美”自然激發的“崇高”感。對自然環境的描寫有強烈的參與感,通過環境描寫來鋪墊情感,展示感情變化,并為后面的情節發展做鋪墊。在審美情趣上,女性作家更注重在心靈上得到的提升與成長。面臨恐懼,雖然膽怯,卻更有耐力,并最終戰勝恐懼,逐漸成熟。女性哥特小說家雖然對恐怖場景極力渲染,但是并非最看重恐怖本身,而是恐怖的經歷,以及這種經歷會帶來什么,更注重道德方面。女性哥特小說在作品中更加表現對安全感的渴求,而這種安全感正是來源于她們所處的社會。
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剛剛經過工業革命的變革,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中產階級的生活相對富裕。但婦女仍然是父權制社會的附屬品。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的婦女雖然不用被生存的壓力所迫去工作,但結婚后只能作為家庭主婦,活動范圍僅僅是家庭,以外的活動不被社會接受和認同,婦女并沒有社會地位。中產階級的婦女一生過著家庭生活,感到厭倦。生活的一成不變和缺乏激情,是婦女們渴望在幻想中尋求激情,這也是哥特小說有相當一部分是女性創造的部分原因。出自對自身地位的不滿,對現實社會的思考,女性作家創造的哥特小說更具有現實性。
三、《弗蘭肯斯坦》內容“女性哥特”的解讀
弗蘭肯斯坦是一位從事人的生命科學研究的學者,他力圖用人工創造出生命。他在實驗室里,通過無數次的探索,創造了一個面目可憎、奇丑無比的怪物。開始時,這人造的怪物秉性善良,對人充滿了善意和感恩之情。他要求他的創造者和人們給予他人生的種種權利,甚至要求為他創造一個配偶。但是,當他處處受到他的創造者和人們的嫌惡和岐視時,他感到非常痛苦。他憎恨一切,他想毀滅一切。他殺害了弗蘭肯斯坦的弟弟威廉,妻子伊利莎白,朋友克萊瓦爾,還間接殺死了弗蘭肯斯坦家收養的養女賈斯汀。弗蘭肯斯坦懷著滿腔怒火追捕他所創造的惡魔般的怪物。最后,弗蘭肯斯坦追隨怪物至北極,在饑寒交迫、疲憊不堪中死在船上。怪物得知主人的死訊,躍入大海自殺,悄然隨主人離去。小說《弗蘭肯斯坦》是怪物對自身被拋棄命運的控訴,也是女人對自己身份的反思。這部小說在一定層面上集中反映了“女性哥特”的特色。
1.怪物的身世。
一個生命的創造過程和開始都是由母體繁衍和賦予的。但是怪物并沒有母親,或者說他的出生是脫離母體,由父親——弗蘭肯斯坦所給予的。在古希臘神話中,眾神就對生育權展開了爭奪。宙斯把懷孕的妻子吞入,以便能夠自己親自生出孩子。另一位造物主普羅米修斯用黑水和黏土仿塑成天神的形體,借用動物的靈魂,造出人類。這些神話傳說表現了原始的男性對擁有生育權的渴望,而女性生育主題被隱匿,話語的主題部分由女性變成男性。這表現了男女兩性對此所進行的激烈斗爭。而怪物是被弗蘭肯斯坦用死尸的身體拼湊而成的,這本身就剝脫了女性的生育權,也正是Mary Shelley等女性作家在男權社會中的焦慮心態的映射。
在怪物被創造的過程中,弗蘭肯斯坦親力親為,全心投入,但當怪物被創造出來時,由于其丑陋的外表被主人無情地拋棄。他痛苦地呻吟:“我的朋友和親屬與配偶在哪兒呢?我小時候,沒有父親在一旁顧盼照看,也沒有母親的笑臉和親撫為我祝福……我到底算個什么呢?”怪物的身份正是象征著女性的性別身份。在出生前精心照顧,但由于性別原因在出世后被拋棄,處在社會的底層。女性作家對自身性別的焦慮,特別是生育的焦慮和恐懼反映了19世紀女性作家在以男性為中心的主流文化中的身份困境和極端心理體驗,傳達了自身在人際關系中的焦慮不安。
2.怪物的成長和反抗——弗蘭肯斯坦。
小說中怪物只讀過三本書——《失樂園》、《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普魯塔克名人傳》。這三本書的作者都是男性,對怪物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它們構建了怪物整個人生觀和世界觀的理論框架。尤其是《普魯塔克名人傳》,怪物把它當做真正的歷史傳記,舉止行為都模仿其中的人物。當怪物被人類社會所遺棄后,它遵從書中“智慧”的指引去反抗和殺人,最終和弗蘭肯斯坦同歸于盡。這正是對男權社會以單行歷史愚化女性,造就了女性的悲劇,也使得自己得到了應有的懲罰。這正是對男權社會的莫大諷刺。
怪物被弗蘭肯斯坦無情遺棄。他的矛頭直指他的父親,他的創造者——弗蘭肯斯坦。而弗蘭肯斯坦正是父權社會的代表人物。在《弗蘭肯斯坦》這部小說里,有三個跟弗蘭肯斯坦相關的重要女性人物:弗蘭肯斯坦的母親,弗蘭肯斯坦的妻子伊利莎白和傭人賈斯汀。而這三個人物看似都過著良好的生活,有著善良的人格,但實際都是父權社會的附屬品。弗蘭肯斯坦的母親一生都奉獻給家庭,伊利莎白是她從小收養的,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在她死后照顧好弗蘭肯斯坦家庭,延續她的責任,而這已經被認為是根深蒂固、理所當然的觀念。她們的生活中沒有自我,只有一味地服從,活動的場所也被局限在家庭。而賈斯汀更是父權社會的犧牲品。她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弗蘭肯斯坦家,但最后原本是清白無辜,卻被逼迫承認罪過,最終被男權社會處以絞刑。這正是對男權社會的控訴。弗蘭肯斯坦在想象世界里對女性實施生殖置換和性別清洗的同時,還對現實世界的女性深懷恐懼。他夢見美麗的伊利莎白變成了去世的母親。總之,這部小說體現了在以弗蘭肯斯坦為首的男權社會對女性在生存空間和情感空間領域的界定。不但把女性變為私有,還約束在狹小的家庭空間。另外,弗蘭肯斯坦和怪物的關系可以界定為父子關系。但最終弗蘭肯斯坦的死亡實際是宣告了父權文化的破產,揭示了現代社會仇恨和非理性的根源。
四、《弗蘭肯斯坦》寫作特點女性哥特的解讀
1.對環境的描寫和氣氛的渲染——人物心理。
哥特小說對環境的描寫是非常注重的,總是不惜濃墨地渲染環境。而女性作家在哥特小說中往往接觸自然景物表達自己的心情。《弗蘭肯斯坦》小說中,Mary Shelley既有對自然風光的長篇描寫,又會常常利用對環境的細致描寫來烘托氣氛,幫助配合表現主人公弗蘭肯斯坦的情緒變化。小說是以敘事口吻,第一人稱進行的,對環境的描寫有強烈的參與感。“太陽已經西斜……送來沁人肺腑的花草的醉人芬芳。當我們靠岸的時候,太陽已經下沉,墜落到天幕后面,而我的雙腳一踏上陸地,固有的重重憂慮和恐懼有驀地控制了我……”,美麗的風光給弗蘭肯斯坦帶來了暫時的愉悅,但甫一上岸就被拉回現實中,苦悶而無助。這正是暗示了主人公將與這一切永別,這種寧靜將永遠離他遠去。最后怪物和弗蘭肯斯坦的死又使一切歸于自然。
2.密室,荒原與無人之地——女性封閉意象的體現。
《弗蘭肯斯坦》的科學家和怪物都置身于封閉空間。在實驗室,弗蘭肯斯坦創造出了怪物,怪物被遺棄,后來走出密室,前往去南美荒原,最后去了北極。從密室到荒無人煙之地,看起來似乎慢慢走出封閉空間,但實際上是從一個小密室走到了一個大密室,并沒有突破空間這個限制。因為在封閉空間的特征是圍困,無法交流,孤獨,視野內景色單一,無處可逃。北極“海上一片片浮冰接連地從我們船邊掠過,預示著我們正開赴的那個地帶危機四伏”。實際上,怪物正是映射《弗蘭肯斯坦》的女作者Mary Shelley自己。怪物對自己被拋棄的命運控訴,也正是Mary Shelley對自己及身份的反思。Mary Shelley的母親是個女權主義者,被人指責是個“怪物”。當時在1793年的《世界箴言報》有這樣一個評論:“羅蘭夫人,一個哲學家,當時的女領袖,不管怎么看她,都是個怪物……盡管她是個好母親,可是她試圖提升自己,犧牲自然本性;想要博學多識的欲望使她忘記了自己的性別的美德。”Mary Shelley借怪物來發表自己的感慨。為了使作品順利發表,她曾一度用了男性假名字。在創造過程中,她的表妹因為私生女的身份被發現而自殺。而Mary Shelley自己合法妻子的身份又是因Shelley前妻自殺而獲得。她心中充滿了他人無法想象的痛苦。《弗蘭肯斯坦》是對女人身份和既定命運的思考,但無法擺脫父權意識的束縛,又不能無視親身經歷的痛苦,這種矛盾思想集中反映在怪物身上。Mary Shelley夫婦看起來是幸福的,但實際上Mary Shelley從一個封閉空間走到一個更大的封閉空間,與生俱來的性別和出身是無法改變的,Mary Shelley走進更大一個無法突破的困境,這正影射了怪物的無法走出的困境。后來,Shelly在意大利溺水身亡,Mary Shelley終生孀居。
五、結語
女性主義批評家借助哥特小說的特質——情節的怪誕,內容的虛幻等作為有效的載體表現自己的感受和對現實的批判。它強調給女性個體帶來焦慮和恐懼的“幽靈”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也并非家族的罪惡史,而是來自現實生活,源于性別角色的禁錮性規定和以性別為導向的人際關系、女性空間的束縛,特別是父權社會的家庭關系和婚姻制度等,從而揭示造成女性心理創傷和個性壓抑的社會根源。《弗蘭肯斯坦》正是借助怪物表達女性幻想、恐懼和對父權社會的抗議,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女性意識,鼓勵女性為自己的平等和自由而戰。
參考文獻:
[1]Ellen Moers.literary woman[M].NewYork:Oxford UP,1976:90-110.
[2]Juliann Fleenor.The female Gothic[M].Montreal and London:Eden Press,1987.
[3]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論女性主義性別與體裁理論[A].外國語,2005,(2).
[4]郭方云.怪物魔鏡中的自我——《弗蘭肯斯坦》造物神話中的女性主義解讀[A].重慶交通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4).
[5]張巖冰.女權主義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6]羅婷.女性主義文學與歐美文學研究[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
[7]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