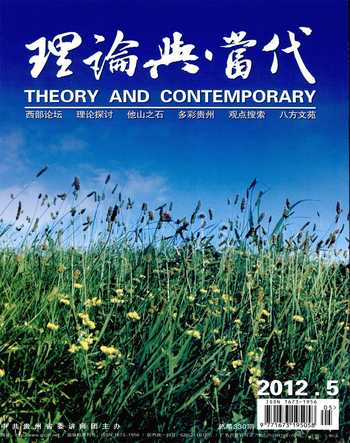為什么我們恐慌于平凡的人生
2012-04-29 00:44:03
理論與當代 2012年5期
關鍵詞:文化
梁曉聲在其著作《郁悶的中國人》(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中介紹了一段對話:“如果在30歲以前,最遲在35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么我就自殺。”“可什么又是不平凡呢?”“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要有什么樣的房,要有什么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這,我還沒認真想過……”。梁曉聲說,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受邀做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志向。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都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士們了,而且,最終,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歷的文化方面的后遺癥。以至于某些呼風喚雨于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行徑茍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盡管他們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么,這樣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遺余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贊歌了,并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面與他們聯系在一起。于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這乃是中國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
猜你喜歡
中國德育(2022年12期)2022-08-22 06:16:18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金橋(2022年1期)2022-02-12 01:37:04
英語文摘(2019年1期)2019-03-21 07:44:16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西部大開發(2017年8期)2017-06-26 03:16:12
西部大開發(2017年8期)2017-06-26 03:15:50
人民中國(日文版)(2015年10期)2015-04-16 03:53:52
人民中國(日文版)(2015年9期)2015-03-20 1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