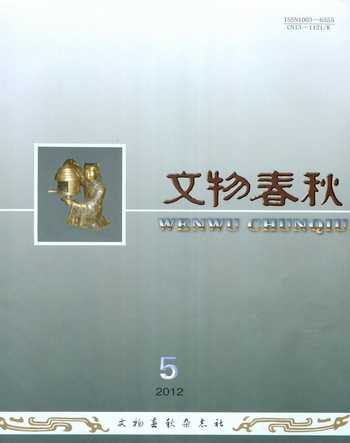先商文化源頭考辨
【關鍵詞】先商文化;源頭;古博水;漳河;發祥地
【摘要】《世本·居篇》云:“契居蕃。”蕃即河北保定的古博水;契“封于商”,商即漳,即冀南豫北的漳水。博水流域是商部族先王契的祖居之地,漳水流域是商部族由博水流域逐步南遷后的居地。在夏末商初時商湯南渡黃河來到鄭洛地區,并在這里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這樣,隨著商部族的逐步南遷,留下了三個階段的商文化,即保北型先商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鄭洛地區的先商及早商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是南遷過程中的中間站,不應該成為尋找先商文化源頭的出發點;立足于保北型先商文化,并探尋它與河北龍山文化的承襲關系,才是尋找先商文化源頭的正確途徑。
先商文化的來源,目前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李伯謙先生在談到先商文化的來源時說:“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形成淵源是很復雜的,既可能是當地先行文化的自然延續,也不排除源自早于它的周鄰某文化,當然也可能是以某文化為主、多種文化融合發展的結果。目前已有后崗二期文化說、山東龍山文化說、晉中龍山期文化說、啞叭莊類型文化說等不同意見,以現知先商文化最早期遺存向前追溯,盡量縮短其與龍山期文化的時間距離,看其在文化面貌上與何種龍山期文化更接近更密切,也許就有可能作出比較接近實際的判斷。” [1]這就是目前先商文化研究的現狀。在先商文化起源這個問題上,我有一些不太成熟的意見,現不揣谫陋寫在下面,以就正于方家。
一、由“契居蕃”和契“封于商”談起
亳在什么地方?《世本·居篇》云:“契居蕃。”丁山先生說:“博、薄、蒲、番、蕃五個字,漢初寫法,尚無刻定之形。所以,‘契居蕃,我認為應在
《荀子·正論》:“湯居亳,武王以
《荀子·王霸》:“湯以亳,武王以
《荀子·議兵》:“古者湯以薄,武王以
《孟子·梁惠王下》:“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者,湯是也。”
《管子·輕重》:“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
《淮南子·泰族訓》:“湯處亳,七十里。”
其中所說的“七十里”、“百里”,都應該是針對百里長的古博水流域而言。
誠然,丁山先生對商族發源地的考證也出現猶疑,他曾經說:“我敢論定商人發祥地決在今永定河與
說博水流域是商人的發祥地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它“與葛為鄰”。
《孟子·滕文公下》云:“湯居亳,與葛為鄰。”歷來說葛者,多從西晉皇甫謐說:“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皇甫謐依據的也僅僅是《漢書·地理志》,東漢著作而已。與湯為之鄰的葛,其地在今河北保定白洋淀邊的安州鎮。《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十九年(前247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集解引徐廣曰:“葛城在高陽。”正義引《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洲高陽縣西北五十里。”《水經注》卷11:“
此葛城處于博水下游。《水經注》引《漢書·地理志》云:“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河。”此“河”指黃河。黃河在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改道南移,“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漢書·溝洫志》)。禹時的黃河,經葛城合
契“封于商”在漳河流域。
《史記·殷本紀》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契由于“封于商”而舉族遷往商。那么,商在何處呢?
古今文字學家釋商為“漳”,殆無疑義。丁山先生說:“商之為商,得名于
二、釋“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自來說湯都者,皆以“湯居亳”為據。此語出自《尚書·商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就亳,從先王居。”我們看到,湯與亳的關系在這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其中的“始”是開始的意思,是說湯在此前未曾居亳;二是亳為先王的居地,湯來到亳是來到祖先的居地。既然已經證明“契居蕃”之“蕃”乃是博水,那么,“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所包含的本事,自然是說湯從冀南豫北的漳水流域,北上來到祖先發祥地的今保定地區的古博水流域。
商湯為什么要離開漳水北上到祖宗發祥地的博水?商湯時期,正當夏朝末年,夏桀暴虐,《史記·夏本紀》有云:“桀乃召湯而囚之于夏臺。”據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十三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條,有:“《書鈔》十引《尚書大傳》:‘桀無道,囚湯,后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尚書·湯誓》云:“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這是湯滅夏誓師時說的話,由此可見民眾的反抗情緒是多么高漲。
商湯北上祖宗發祥地,應該是在夏桀囚湯而釋之以后。他為了讓夏桀少找自己的麻煩,減少和夏王朝的接觸,于是躲得遠遠的,來到祖宗發祥之地的博水流域,為滅夏做著韜光養晦的準備工作。
商湯的目的應該說是達到了。商湯伐葛,既是滅夏前的一次軍事演習,又是政治上解民于水火的宣示。據《孟子·梁惠王下》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而西怨;南面而征,而北怨,曰:‘奚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商湯不但得到了下層民眾的擁護,而且得到了上層諸侯的支持,“諸侯遂賓于商”、“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就是證明。
在來朝的六國諸侯中,其中之一應該就有東夷人,因為商人與東夷是近鄰。屬于東夷部落的岳石文化分布范圍是:“以山東為中心,南面包括江蘇的淮北地區,北面可能進入河北,東北抵達遼東半島的旅大地區,有著同山東龍山文化基本一致的分布范圍。”[9] 關于進入河北的地域,李伯謙先生說:“其影響所及,往北可到河北省保定地區白洋淀附近。”[10]先商文化本就分布在太行山東麓的山前平原的狹長地帶,東以古黃河為界與岳石文化為鄰,白洋淀至任丘一線更是先商文化與東夷文化交錯地區。容城白龍先商文化遺址中存在岳石文化因素,給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例證。發掘報告說:“白龍遺址中的盤內有凸棱的豆與分布于山東一帶的岳石文化的豆相似。”還說:“多種文化因素的共存,是保北地區夏商時期遺存的一個特點。”[11]據宋豫秦、袁廣闊、王立新等先生考證,漳河型先商文化南渡黃河來到豫東后,迅即有東夷人加入。由豫東西進鄭州再到偃師,都可以看到商夷文化的結合 [12] 。凡此種種,都可證明商夷聯盟的建立,不可能是在豫東地區的臨時磋商,而是早有準備、早有協定的會師。其協定的具體時間,應該是在“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的“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時期。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湯始居亳”是說湯來到祖先契的居住地。亳是商族人對居住地的稱呼。《說文解字》釋亳:“從高省,乇聲。”《說文解字》釋高:“崇也,像臺觀高之形。”而“亳”字的下半部分顯然是“宅”字的略寫。二者結合起來,意思是建在高處的住宅。博水下游地勢低洼,夏商時期的黃河由今河南進入河北后呈南北走向,經白洋淀東流至天津入海,白洋淀即是黃河改道后的孑遺。另外由徐水南莊頭遺址看,白洋淀西部的徐水地區“在全新世之初是淺水湖泊環境”[13] 。由此可知商族人生活環境的一般。地勢低洼是促使商族人把住宅建在高地的原因,也是商族人將自己的居民點稱之為亳的原因。
由現有的資料可知,隨著商族人的遷移,他們將自己作為居住地的“亳”帶到新的駐地,就像我們現在把名字帶到新的駐地一樣自然。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古文獻中看到許多帶亳字的地名,考證起來,這些帶亳字的地名都直接或間接與商族人曾經于其地居住有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亳是商族人對居住地的專有稱呼,并不是商族人稱呼都城的專有名詞;也就是說,商族人的都城可以名“亳”——因為它也是商族人的居住之地,但名“亳”者卻不一定是都城。比如在陜西關中地區,春秋時期還有商族人后裔在活動。《史記·秦本紀》載:“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引徐廣曰:“蕩音湯。社,一作‘杜。”《索隱》云:“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史學界“湯居亳”之“杜亳”說,即源于此。
活動在陜西關中地區的這支商族人,不稱商王而稱亳王,這是有講究的。商王是中央政權的稱號;亳是商族人對于居住地的稱呼,亳王即亳地之王,其源出于商族祖先發祥之地——河北保定的古博水。不稱商王稱亳王,說明他們出身于正統的商貴族。其邑曰湯社,明含尊湯之意,說明他們以湯為始祖。《索隱》稱其為“成湯之胤”是完全正確的。
有的研究者不明白亳只是商族人對居住地的稱呼,不明就里地把亳和商都劃上了等號,于是形形色色的商湯都城被制造出來。除上面的杜亳說外,還有陜西的商州說,山西晉南的垣亳說,山東境內的博縣說、曹縣說,河南的內黃說、湯陰說、南亳說、北亳說、鄭亳說、西亳說等。事實的真相是:商湯的都城必定名亳,但名亳者不一定是商湯的都城。所以以上諸說有正確者,但大部分是望風捕影。即如杜亳說,亳王只是亳地之王,而非商王,其非都城明矣。
我們的一些研究者沒有深究“湯始居亳”的真正含義,想當然地把亳和商湯滅夏后所建立的都城聯系起來,在亳和商湯都城之間劃上了等號,從而把它所包含的真實內容——商湯舉族由漳水北上到博水——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實掩蓋了起來。這是我們對這一問題非辯不可的原因。
三、商族南遷的考古學證據
在夏商對決前后發生在黃河以南鄭洛地區的先商與早商文化遺址中,人們能看到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和輝衛型因素,比如豫東杞縣鹿臺崗遺址的先商文化屬于漳河型 [14] ,鄭州南關外期遺存的商文化屬于輝衛型[15],大師姑的商文化不僅有二里崗下層文化,還能分辨出輝衛型因素 [16] ,偃師商城一期一段的商文化因素中,有漳河型也有輝衛型 [17] 。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不禁要問:保北型或曰岳各莊型先商文化怎么不見了,它到哪兒去了?
張翠蓮先生曾說,保北型先商文化不是商族文化,她認為“下岳各莊文化可能是由有易氏創造的”[18] 。果真如此,問題就簡單了:它不屬于商部族,沒有參加商湯滅夏的戰斗,所以在夏商對決時不見他們的身影。可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
對比保北型和漳河型兩種文化,它們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說它們是各不相屬的兩種文化,讓人實在不能信服。
“契居蕃”與契“封于商”這樣兩個事實,說明商部族有一個從冀中博水流域逐步南遷的歷史過程。商部族在南遷的過程中有三個比較集中的定居地,最初是冀中的博水流域,其后是冀南豫北的漳河流域,最后是黃河以南的鄭洛地區。我們的結論是:就像漳河型先商文化在渡過黃河以后變成了鄭洛地區的先商及早商文化一樣,保北型先商文化隨商湯南遷到冀南豫北以后,變成了漳河型先商文化。這就是說,保北型先商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以及黃河以南的先商及早商文化,都是同一個商部族的文化,其名稱不同,代表的僅僅是時代的早晚而已。
商部族不是漳河流域的原住民,我們還可以從漳河型先商文化的年代得到證明。關于其年代,鄒衡先生說:“先商文化(漳河型)的第一段第Ⅰ組約相當于夏文化晚期第三、四段之間,而先商文化(輝衛型、南關外型)的第一段第Ⅱ組約相當于夏文化晚期第四段。” [19]后來,鄒先生針對河北磁縣下七垣發掘報告將該遺址第四層認定為二里頭文化的結論,發表不同意見:“我們認為,從第四層的文化全貌來看,因其絕大部分因素均不同于二里頭型和東下馮型,顯然不能稱為二里頭文化,而應該歸之為先商文化漳河型;惟其年代(主要指T7④)乃稍早于漳河型第Ⅰ組,與第Ⅰ組同樣受到二里頭文化的影響。這一發現自然是重要的,至少是把漳河型先商文化又提早了一個階段。” [20]這就是說,漳河型先商文化最早的年代提到了二里頭文化第二段與第三段之間。即便如此,漳河型先商文化距先商文化的早段(以契為代表的文化)仍然有相當一段距離。漳河型先商文化不是商族人的文化源頭明矣。
那么,保北型先商文化的年代又如何呢?
李伯謙先生將保北型遺存歸人漳河型先商文化,并統一劃分為三期,認為三期的年代相當于二里頭文化的二、三、四期。為了問題簡化,關于李先生的分期原則我們僅以鬲為例:第一期皆高領,鼓腹,分襠靠下;第二期領部變矮,分襠上移,仍為鼓腹厚胎;第三期領部消失,腹壁近直,等等。按照這樣的原則檢視先商文化,保北型的陶鬲高領鼓腹特征明顯,越往南這一特征逐步消失,到了鄭州商城及偃師商城早商期的陶鬲,皆為無領且腹壁近直[21]。對于商部族的三大居住地來說,越往南年代越晚;反之,越往北年代越早。相比較而言,保北型早于漳河型,漳河型早于鄭洛地區的先商及早商文化。
四、先商文化的源頭應該以
保北型為坐標尋找
最早探尋先商文化源頭的學者是鄒衡先生。他從類型學的角度將漳河型先商文化與周鄰文化對比后得出結論說:“看來,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來源并不是單一的,它應該有三個主要來源:一是河北省的河北龍山文化澗溝型;二是山西省的河北龍山文化許坦型;三是山西省的夏文化東下馮型。同時,還有兩個次要來源:一是河南省的夏文化二里頭型;二是山東省的山東龍山文化。后面兩個次要來源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結果。前面的三個主要來源中,有兩個屬于河北龍山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先商文化漳河型來源于河北龍山文化。但若就地區而言,這三個主要來源中,有兩個在山西省,因此在另一意義上又可以說,先商文化漳河型中的不少因素是從山西省來的。”[22]
如果從文化因素分析的角度看待上面的結論,我們不能不佩服鄒衡先生思維的縝密和結論的準確。由于當時保北地區先商文化的發現還是零星的,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由于先商遺址的大量發現而形成了一種類型的文化——“保北型先商文化”,從而影響到鄒先生對先商文化源頭的判斷。后來的學者以漳河型作為先商文化的最早源頭,與鄒衡先生的結論不無關系。因此我們說,鄒衡先生在生前沒有像分析漳河型先商文化那樣分析保北型先商文化的因素構成,是十分遺憾的事。
對于太行山東麓地區夏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張翠蓮先生針對南北一體的觀點表示了不同意見:“經過相關資料分析后,本人認為以滹沱河為界的南北二區在文化面貌上差異較大,似不宜作為同一支考古學文化來看待。”[23]這個判斷已經被越來越多的考古材料證實。
河北境內發現的先商文化遺址已經不少,但我們對太行山東麓北區先商文化(保北型先商文化)的研究還顯得薄弱。就在我們苦苦尋找先商文化與河北龍山文化具有承繼關系的地層時,任丘啞叭莊遺存的發現似乎給我們帶來了希望。發掘者將該遺址第一期遺存稱為“龍山時代啞叭莊類型”。中原文化區的龍山文化有這樣幾個基本類型:后崗二期文化、王灣三期文化、造律臺文化、陶寺文化、三里橋文化、客省莊文化等 [24],太行山東麓的南北兩區都在后崗二期文化的范圍內。對于發掘者所定性的“龍山時代啞叭莊類型”與后崗二期文化的關系,暫時還無法理清。其第二期遺存,發掘者定性為“燕南夏家店下層文化啞叭莊類型”,但同時又指出“啞叭莊二期遺存與中原地區的先商文化和二里頭文化遺存也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對于第一期遺存與第二期遺存的關系,發掘者說:“二者區別明顯,代表著不同時期的兩種文化的兩個類型”;同時又說:“但兩種類型間又有一定的聯系……我們認為二者是一種淵流關系。” [25]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為源、先商文化為流,抑或反之呢?發掘報告顯然主張的是前者。《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將啞叭莊二期重新定性為先商文化。這樣,我們雖然可以由此作出這樣的推論:太行山東麓北區的先商文化(保北型先商文化)來源于“龍山時代啞叭莊類型”,可是這樣的結論總覺得牽強,因為它證據薄弱,或者說代表性不充分。但不管怎么說,啞叭莊遺存中有先商文化因素,而且還與龍山文化建立了聯系,理應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
類似的遺存還有蔚縣壺流河流域夏商時期遺存。發掘者將該遺存劃分為四個階段,先商文化研究者關注的是前兩段遺存。發掘者認為,“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遺存的面貌相近,文化成分也基本相同”,其主體成分“與海河水系地區目前稱之為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遺存同屬于一系統文化”,另外兩種成分“分別與太行山脈東麓漳河流域地區的先商文化和太行山西麓汾河中游地區的考古文化有聯系” 。關于其年代,發掘者說:“經過反復驗證的蔚縣壺流河流域夏商時期遺存間的層位關系清楚,年代明確。”第一階段的層位晚于本地的龍山時期。蔚縣龍山時期的碳14測年為距今4000年左右,第一階段要晚于這個年代;第二階段的樹輪校正年代為1560±125年[26]。顯然,這里的兩期遺存延續時間較長,在相對年代上早于漳河型先商文化。但我們目前還不能理清這兩種遺存與當地龍山文化的關系。正像張忠培先生針對河北的考古現狀所說:“目前所見到的龍山時期的遺存還比較零碎。所以,遠不能清楚地說明先商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起源問題。”[27]但是蔚縣的發現仍然是重要的,因為這里的遺存所包含的先商文化因素明顯早于漳河型先商文化。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太行山東麓北區的先商文化(保北型先商文化)才是先商文化的源。
任何一種文化在其形成發展的過程中,都必然受周鄰文化的影響,從而形成有源有流的局面。其中的流可以有多個,因為它是源這個主體身上的附加成分;而源卻只能是唯一的,只有抓住源才能探尋到源頭。我們探尋先商文化的源頭,首先應該區分何者為源,何者為流。對于漳河型先商文化來說,它的源只有一個,那就是太行山東麓北區的先商文化(保北型先商文化);除此而外,附加在其身上的其他文化因素都是流。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表現為一個過程,都可以劃分出頭、腰、尾三部分。對于先商文化來說,黃河以南以鹿臺崗開始的先商文化處于尾的部分,漳河型先商文化處在腰的部分,太行山東麓北區的先商文化(保北型先商文化)即使不是頭,但也包括在頭的范圍內 [28] 。因此,我們對先商文化源頭的探尋不應該從腰出發,而應該以頭——事物開始的地方——為出發點。二里頭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省。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河南省就宣布“發現了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直接發展為二里頭文化早期的承襲關系”[29]。豫北地區的先商文化遺址數量也不少,但那里的先商遺址最早者也僅與河北的漳河型先商文化年代相當——不是先商文化最早期的遺存;而黃河以南的先商遺存更是處于先商文化的最末期。所以,在河南省不可能找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直接發展為先商文化早期的承襲關系。先商遺址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尤其冀中的博水流域還是商部族的“先王居”——祖宗發祥之地。但直到如今,我們還沒有發現河北省龍山文化晚期直接發展為先商文化早期的承襲關系地層。換句話說,在先商文化早段與河北龍山文化晚段之間還存在著不小的缺環。任丘啞叭莊和蔚縣壺流河的發現給我們帶來了些微曙光,但材料并不典型,還不足以說明問題。考古學是面對實物說話的學問,它不討論不存在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在先商文化研究方面不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漳河型先商文化在太行山東麓的南區,保北型先商文化在太行山東麓的北區;而南區的先商文化是由北區遷移過去的。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探尋先商文化源頭不能從南區出發而應立足于北區,就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了。另外,還要努力探尋北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譜系,尤其搞清北區的河北龍山文化的面貌。易水流域史前遺址北福地的發掘為建立這一譜系提供了可能。發掘者認為北福地一期文化與磁山文化“兩者屬南北相鄰的兩支基本同時代的不同系統的新石器文化”[30]。黃運明先生也認為:“磁山文化是一支僅分布在太行山東麓地區南部的考古學文化。具體來說,該文化主要集中在冀南地區的
————————
[1][10]李伯謙:《先商文化研究的新征程》,載《文明探源與三代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2] [4]丁山:《商周史料考證》,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17頁。
[3]尚友萍:《“契居蕃”考》,《文物春秋》2004年2期。
[5]a.沈勇:《論保北地區的先商文化》,北京大學考古系碩士學位論文,1988年;b. 沈勇:《商源淺析》,《文物春秋》1990年3期。
[6]《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55頁。
[7] 安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安新縣志》,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11-12、79-80頁。
[8]同[2],第13-14頁。
[9]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前進中的十年》,載《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68頁。
[11]保北考古隊:《河北容城白龍遺址試掘簡報》,《文物春秋》1989年3期。
[12]a.宋豫秦:《夷夏商三種考古學文化交匯地域淺談》,《中原文物》1992年1期;b.袁廣闊:《關于先商文化洛達廟類型形成與發展的幾點認識》,載《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6年;c.王立新,胡保華:《試論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載《考古學研究(八)》,科學出版社,2011年。
[13]《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92頁。
[14]鄭州大學文博學院,開封市文物工作隊:《豫東杞縣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8-116、254-259頁。
[15]同[6],第167頁。
[16]a.鄭州市考古研究所:《鄭州大師姑》,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75-334頁;b.王文華:《從大師姑遺址的發掘看二里頭四期文化的性質》,載《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6年。
[17] 參見[12]c。
[18] [23]張翠蓮:《太行山東麓地區夏時期考古學文化淺析》,載《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學出版社,1999年。
[19]鄒衡:《試論夏文化》,載《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二版),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27頁。
[20]同[19],第168-169頁。
[21]李伯謙:《先商文化探索》,載《商文化論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
[22] 同[19],第148頁。
[24]董琪:《虞夏時期的中原》,科學出版社,2000年。
[2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滄州地區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丘市啞叭莊遺址發掘報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6]張家口考古隊:《蔚縣夏商時期考古的主要收獲》,《考古與文物》1984年1期。
[27]張忠培:《河北考古學研究與展望》,《文物春秋》1991年2期。
[28]李伯謙先生將下七垣文化分為三期,第一期的第一個標本就是鞏固莊的陶鬲(見[21]),屬于保北型;《中國考古學·夏商卷》將下七垣文化分為四期,第一期就包括保北型的徐水鞏固莊和任丘啞叭莊遺存(見該書第149頁)。可見保北型在下七垣文化中年代是最早的。但有人或許會說:保北型先商文化的年代也有早有晚,這如何解釋?答:或許當年南遷的并不是所有的商族人,而只是契所統領的部族。想一想成吉思汗、努爾哈赤在早年也沒有將本民族所有的部落統一起來,便不難理解上面的疑問。
[2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近十年河南文物考古工作的新進展》,載同[9]。
[3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遺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31]黃運明:《磁山文化分布范圍探析》,《文物春秋》2009年4期。
〔責任編輯: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