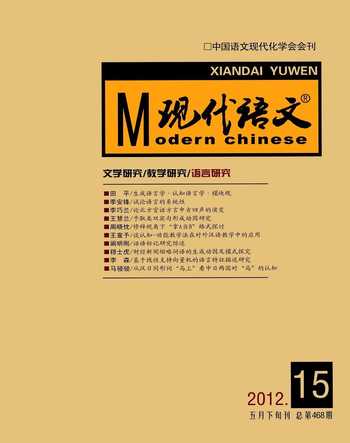修辭視角下“拿A當B”格式探討
修辭是在語言的使用過程中產生的。語言交際者在言語交際中總是有意或無意地追求一種最佳的表達效果,為了達到這種最佳的表達效果,他們就會對語言材料進行選擇加工,這種加工的過程就是修辭活動,而在修辭活動中對語言材料加工的方法就是修辭手段。運用不同的修辭手段對語言材料進行加工會產生不同的表達效果。
修辭學考察的對象一般是圍繞句子展開的,具有修辭效果的句子有時會以格式的形式出現,而且某些格式隨著時間的沉淀會賦有修辭效果。正如高再蘭所說:“詞在使用過程中會發生虛化,由實義詞變成功能詞。句子在使用中也會發生虛化,由實義格式虛化為修辭格式。”本文將要討論的“拿A當B”即屬于這一范疇中的一類。含有修辭效果的“拿A當B”是如何表達修辭效果的呢?本文將對“拿A當B”這種固定格式的修辭手段進行解釋分析。
一、“拿A當B”格式中的比喻修辭
王希杰《漢語修辭學》指出:“語言的聯系美可以從多種角度來實現,達到這種聯系美的手法也是多種多樣的。”比喻作為修辭學中一種體現聯系美的修辭手段,在“拿A當B”這種格式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我們先來看幾個例子:
(1)要武和環環并肩站著,拿細樹枝當“香火”,拱手磕頭,作揖燒香,歡歡樂樂地拜起天地來。
(2)那位白白胖胖的女兵圖書管理員,常常納悶地望著這個黑皮膚瘦個子報務員,心里思忖道:“他是拿書當飯吃不成?”
(3)白沙撤字是用手捏著沙子,拿手當漏斗,白沙子漏下去形成字。
通過觀察這些例句,我們發現,例(1)中“拿細樹枝當‘香火”,“細樹枝”和“香火”從外觀上來看具有相似性,抓住了這個相似點形成了這個比喻句,形象、貼切、生動,語氣上歡快明亮。例(2)中“拿書當飯”用在疑問句中,將女圖書管理員心中的佩服、驚嘆的感情流露其中,從這個句子整體語氣看,呈現出來的也是一種積極向上的感情。再看例(3)中“拿手當漏斗”,“手”和“漏斗”本來是沒有任何關聯的,但是在這里,我們如果將“手”想象成“漏斗”,便形成了具有比喻含義的比喻句。
從以上例句來看,比喻視角下的“拿A當B”從語氣上表現出來的歡快、愉悅的感情色彩是通過包含這個格式的整個句式形成的,有時這種感情色彩也要通過上下文的語言環境表現。
既然“拿A當B”這個格式有表示歡快、愉悅的比喻效果,那么這個格式在某些環境中是否會呈現出不同的表達效果呢?先看下面的例子:
(4)哎呀呀,怎么老拿“蛤蟆坑”當“聚寶盆”呢!
(5)拿尊嚴當賭注,拿身體當道具,這種近乎悲壯的行為瞬間在網絡走紅,想必在多數人的意料之中。
(6)現在重表面,為面子的政績工程屢見不鮮,原因就是有關政府和官員在決策時,考慮自己的前途多些,考慮百姓的利益少些。為了官位和升遷,腦門一熱亂拍板,甚至不惜拿百姓當墊腳石和梯子,打著為民的旗號損害百姓利益。
例(4)中拿“蛤蟆坑”當“聚寶盆”,是將“蛤蟆坑”比喻成“聚寶盆”。從語氣上來看,“拿A當B”格式用在這里有濃厚的諷刺意味。“拿A當B”格式用在了表示反諷的感嘆句中,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句子的諷刺意味并不全是由“拿A當B”格式體現出來的,這個感嘆句式同樣增強了整個句子的反諷意味。例(5)中拿“尊嚴”當“賭注”、拿“身體”當“道具”,這里將“尊嚴”和“身體”分別比喻成“賭注”和“道具”,細致觀察這個句子后我們發現,這里的本體分別是由抽象名詞“尊嚴”和具體名詞“身體”構成的,喻體由表示兩個概括性的名詞充當。將社會中的丑陋現象以一種比喻的方式表現出來,諷刺意味濃厚。如果說例(4)中的諷刺意味不全是由“拿A當B”這個構式形成的,那么例(5)中的諷刺意味是完完全全的由這個構式表現出來的。例(6)中“拿百姓當墊腳石和梯子”,將百姓比作官僚主義者向上攀登官位的工具,這個句子所表現出來的諷刺意味是通過這個構式形成的比喻義表達的。
通過對以上例句的分析,我們發現,“拿A當B”這個構式可以表現出兩種比喻含義:一種是表示積極向上的比喻義,這種比喻義是在語言環境和句式的影響下形成的;另外一種是表示諷刺效果的比喻義,這種比喻義是通過“拿A當B”這個構式本身形成的。
二、“拿A當B”格式中的回環修辭
“拿A當B”格式中的A和B有時會以回環往復的表現形式出現,這種修辭在修辭學中被稱為回環,這種修辭方式是通過回環往復的形式表現兩種事物或現象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的辯證關系,用以加深讀者對陳述事實的認識和理解。例如:
(7)二十年來,反動的統治階級認賊作父,拿敵人當朋友,拿朋友當敵人;中國人民受盡了壓迫,也受盡了欺騙。
(8)你拿我當什么,我就拿你當什么。
(9)男人拿女人當什么,女人就拿男人當什么。
例“拿敵人當朋友,拿朋友當敵人”中,“敵人”和“朋友”相互之間形成回環的修辭格。“敵人”和“朋友”在語義上是一對相反相成的詞語,這種對立的辯證關系在“拿A當B”這種格式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筆者還發現,“拿A當B”格式中,A和B呈現出反復回環的修辭格,“拿A當B”這種格式在形成回環修辭手段時本身會重復出現。同樣,例(8)和例(9)中的“你”和“我”、“男人”和“女人”在“拿A當B”格式中也是反復出現。如果說例(7)中的A和B是相互排斥對立的辯證關系,那么例(8)和例(9)中的A和B在語義上則是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正如闡釋回環修辭手段本身時所講的那樣,這種修辭方式表現了兩類現象相互排斥、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
筆者在分析解釋回環修辭手段下“拿A當B”這種格式時發現這種格式呈現出一系列有規律的特征:
1.“拿A當B”格式中,A和B會呈現出回環往復的外在形式,“拿A當B”這種格式在形成回環修辭格時本身也會重復出現。
2.“拿A當B”格式中的A和B常常是體詞,這些體詞主要包括名詞、代詞兩種類型。
3.“拿A當B”格式中A和B在語義上表現為相互排斥、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
4.回環修辭格下的“拿A當B”從功能上來講主要是為了強調讀者對陳述事實的認識。
三、“拿A當B”格式中的引用修辭
引用修辭是一種傳統的修辭手段,古人在寫文章時總會引用一些前人經典的“語句或故事來提高文章的表達效果。”引用分為正引和反引,正引是所引用內容與作者文章表達的思想內容一致,反引與正引正好相反。“拿A當B”格式中的引用多半是自古流傳下來的熟語,“拿A當B”這種格式存在于引用的熟語中。例如:
(10)那是我開玩笑的,你怎么就“拿棒槌當針(真)”了?
(11)關造武“拿雞毛當令箭”,用陸區書說過的話來回擊曲世青,著著實實敲了一杠子。
(12)我不便露面,你把這藥給馬媽,偷偷給二少爺灌了,也別管它嘛脈了,“拿死馬當活馬醫”,活一天算一天吧。
例(10)中的“拿棒槌當針(真)”,例(11)中的“拿雞毛當令箭”,例(12)中的“拿死馬當活馬醫”都是自古流傳下來的熟語,這些熟語中的“拿A當B”格式作為整個句子中引用的一部分也可以分為正引和反引。例(10)、(11)中的熟語在古語流傳下來時是帶有貶義色彩的,用在這兩個句子中正合作者寫作意圖,表達了一種諷刺的修辭效果,符合引用中的正引。而例(12)中的“拿死馬當活馬醫”則帶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引用到這里則表現“我”對“二少爺”病情的關心,和這條熟語本身的話語含義是相反的,是反引。
總之,“拿A當B”這種格式在我們日常言語交際中很常見,這種格式表達的修辭效果也會因為修辭手段不同而有所區別。
參考文獻:
[1]王希杰.漢語修辭學[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2]高再蘭.一種新的暗喻格式:“有一種A叫B”[J].修辭學習,2007,(4).
[3]俞燕,仇立穎.框填式流行語何以如此流行?[J].修辭學習,2009,(6).
(周曉忱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1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