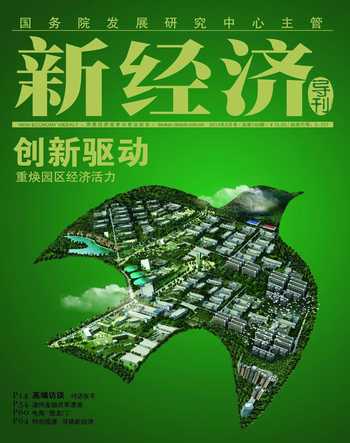火炬照耀高新區(qū)
林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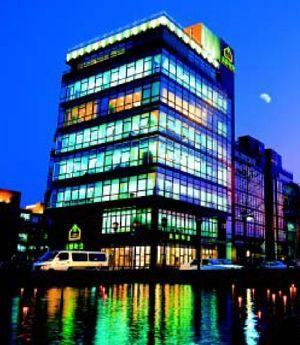

科技如何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如何推進(jìn)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發(fā)展?高新區(qū)提供了最佳的嘗試模式
春日,北京,前門東大街車水馬龍,11號(hào)院卻獨(dú)自幽靜。這是國務(wù)院參事室駐地。石定寰匆匆走出會(huì)議室,未作休整,便在一間休息室內(nèi)開始了本刊專訪。他精力充沛、清晰思路,說話剛勁且語速極快,與其已近古稀的年齡并不相稱。他已經(jīng)為中國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奉獻(xiàn)了30年的青春,如今又在為低碳經(jīng)濟(jì)、新能源科技的推廣而奔走呼吁。
在他的履歷上,除了“總理高參”、“低碳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的光環(huán),最讓人記憶猶新的是,他在中國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的貢獻(xiàn):曾長(zhǎng)期負(fù)責(zé)國家工業(yè)及高新技術(shù)領(lǐng)域科技計(jì)劃與重大項(xiàng)目組的組織實(shí)施,主導(dǎo)參與國家火炬計(jì)劃、國家高新區(qū)的策劃與實(shí)施;而科技企業(yè)孵化器、生產(chǎn)力促進(jìn)中心、大學(xué)科技園等機(jī)構(gòu)的建設(shè),也是在其推動(dòng)下提上日程的。以下是他的自述。
科技園應(yīng)運(yùn)而生
上世紀(jì)20年代初,奧地利的熊彼特首創(chuàng)技術(shù)創(chuàng)新理論,在上世紀(jì)百年之中有力地推動(dòng)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該理論把技術(shù)創(chuàng)新過程看成有效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過程,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看成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一個(gè)鏈條,將發(fā)明創(chuàng)造面向市場(chǎng)進(jìn)行產(chǎn)業(yè)化,進(jìn)而帶動(dòng)經(jīng)濟(jì)的新一輪增長(zhǎng)。
我們也曾系統(tǒng)地宣傳了技術(shù)創(chuàng)新概念,強(qiáng)調(diào)了它的創(chuàng)新性、實(shí)用性、系統(tǒng)性,并強(qiáng)調(diào)了以市場(chǎng)需求為基礎(chǔ)。因?yàn)榭茖W(xué)發(fā)明有很多,但首先應(yīng)對(duì)其中能對(duì)市場(chǎng)、人們未來生活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成果加以應(yīng)用,而應(yīng)用情況則通過市場(chǎng)檢驗(yàn),如果市場(chǎng)能夠接受,則說明創(chuàng)新成功。
二戰(zhàn)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更加依賴科技發(fā)展、技術(shù)進(jìn)步,而每次技術(shù)進(jìn)步,如蒸汽機(jī)、信息技術(shù)、新材料、生物技術(shù)等新技術(shù)革命,都帶來新一輪經(jīng)濟(jì)發(fā)展。2008年,溫家寶總理也指出,全球金融危機(jī)預(yù)示著人類正在進(jìn)入新一輪技術(shù)革命,而這又能帶來新一輪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
其實(shí),過去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中國學(xué)習(xí)蘇聯(lián)的模式,科技與經(jīng)濟(jì)分割,科技體系與經(jīng)濟(jì)體系兩者之間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礙,科技與經(jīng)濟(jì)“兩張皮”。在改革開放后,我們力求改變這種“兩張皮”的狀況。1978年,科技大會(huì)召開,迎來了科技的春天。鄧小平同志很快提出,科技是生產(chǎn)力,后來又進(jìn)一步提煉、闡述科技的作用,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chǎn)力”。
如何更好地促進(jìn)科技與經(jīng)濟(jì)的結(jié)合?國務(wù)院在上世紀(jì)80年代初提出了“依靠、面向”的方針:經(jīng)濟(jì)建設(shè)要更好地依靠科學(xué)技術(shù),科學(xué)工作要更好地面向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方針的提出就是為了促進(jìn)兩者結(jié)合,打破過去“兩張皮”的現(xiàn)象。到1984~1985年,先后進(jìn)行了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而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要解決科技與經(jīng)濟(jì)脫節(jié)的問題。
科技體制改革通過很多辦法。包括改變完全靠國家全額撥款養(yǎng)人的方式,減少事業(yè)單位,鼓勵(lì)研究機(jī)構(gòu)面向市場(chǎng),國家更多通過對(duì)項(xiàng)目的支持,對(duì)科技工作的支持,而不再采用人頭費(fèi)的辦法。面向市場(chǎng)尋找研究成果,通過研究成果的產(chǎn)業(yè)化,再來支持科學(xué)研究的發(fā)展。
過去,科技人員都是隸屬大學(xué)、研究所,基本上是終身制,很難自由流動(dòng)。當(dāng)時(shí),科技人員被封鎖在院墻里,很難進(jìn)入市場(chǎng)。隨著改革的推進(jìn),鼓勵(lì)人才合理流動(dòng),鼓勵(lì)他們?yōu)槭袌?chǎng)、為企業(yè)提供服務(wù)。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中期后,陸續(xù)有一批科技人員下海,創(chuàng)辦了一批科技型企業(yè),如聯(lián)想、四通、三環(huán)、京海等,后來形成了中關(guān)村一條街,這是很好的苗頭。
再往后,中國進(jìn)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發(fā)揮科技的力量,去參與國際經(jīng)濟(jì)大循環(huán)(當(dāng)時(shí)提出兩大循環(huán),即國內(nèi)經(jīng)濟(jì)大循環(huán)和國際經(jīng)濟(jì)大循環(huán)),以迎接世界新的技術(shù)革命(信息技術(shù)革命、美國的高速公路,星球大戰(zhàn)計(jì)劃等)的挑戰(zhàn),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后,中國迫切需要融入世界經(jīng)濟(jì)大循環(huán),而國內(nèi)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也迫切需要科技為經(jīng)濟(jì)服務(wù),加強(qiáng)科技與經(jīng)濟(jì)結(jié)合。現(xiàn)在,科技創(chuàng)新對(d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影響越來越大,但科技與經(jīng)濟(jì)脫節(jié)的問題雖然有了很大改善,但實(shí)際上仍然沒有最終解決。溫家寶總理曾在多次會(huì)議上指出,我們的科技體制改革,主題仍然要圍繞科技與經(jīng)濟(jì)結(jié)合的問題,加強(qiáng)科技對(duì)經(jīng)濟(jì)的支撐和引領(lǐng)作用。
那么,怎樣才能更有效地推動(dòng)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讓科技與經(jīng)濟(jì)更好地結(jié)合?隨著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的深入,科技如何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被推到時(shí)代的風(fēng)口浪尖。轉(zhuǎn)化有多種形式,怎樣來促進(jìn)?很多國家做了很多探索,科技園就是最佳嘗試之一。
1987~1988年間,國務(wù)院專門組織了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教育部、中科院等機(jī)構(gòu)聯(lián)合進(jìn)行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調(diào)研,形成的報(bào)告提出要關(guān)注世界上成功的經(jīng)驗(yàn)——建立科技園區(qū)。科技園區(qū)就是把科技力量、資源等集中在某地區(qū),為這個(gè)地區(qū)提供更好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建立科技公司,把科技成果更好地轉(zhuǎn)化,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
科技園不是中國首創(chuàng),國際上已有高新技術(shù)園區(qū)的雛形,如美國的硅谷、128公路,中國臺(tái)灣的新竹等,通過孵化器來促進(jìn)科技成果的轉(zhuǎn)化。這些新現(xiàn)象引起中國科技主管部門、專家的高度關(guān)注。在此形勢(shì)下,我們提出在中國建設(shè)中國自己的科技產(chǎn)業(yè)園區(qū)。
多年前,時(shí)任國家領(lǐng)導(dǎo)人江澤民在APEC會(huì)議上,對(duì)科技園就給出了很高的評(píng)價(jià)。他說,科技園是20世紀(jì)人類的一個(gè)重大發(fā)明。其意義在于,能將科技成果更好地推向產(chǎn)業(yè)化、推向應(yīng)用。其實(shí),過去我們也提出建立科學(xué)城,但聚焦在研究層面,而現(xiàn)在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不是單純的研究,是用科技促進(jìn)產(chǎn)業(yè)發(fā)展,加快科研成果的產(chǎn)業(yè)化進(jìn)程,更好地為經(jīng)濟(jì)服務(wù)。
1988年3月,中央做出了建立科技園區(qū)的決定,5月正式批準(zhǔn)建立“北京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試驗(yàn)區(qū)”,具體地點(diǎn)就在中關(guān)村。當(dāng)時(shí),國務(wù)院確定,這樣的園區(qū)可以再辦兩三所,但不要太多,因?yàn)闆]有經(jīng)驗(yàn),還在摸索。國務(wù)院要求各部門開綠燈、給政策(包括經(jīng)濟(jì)政策、稅收金融政策等),以鼓勵(lì)促進(jìn)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后來,批準(zhǔn)了武漢、南京、上海、深圳等幾個(gè)試點(diǎn)。
火炬計(jì)劃浮出水面
然而,對(duì)于如何發(fā)展高新區(qū),中國沒有任何經(jīng)驗(yàn)。為此,科委又開始醞釀一個(gè)更大的計(jì)劃。過去,科研計(jì)劃主要有“科技攻關(guān)”計(jì)劃(83年開始推動(dòng))、“863”計(jì)劃(86年開始推動(dòng))等,但這些都是研究計(jì)劃。當(dāng)時(shí),科委開始醞釀?dòng)懻摚懿荒芨阋粋€(gè)促進(jìn)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促進(jìn)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新計(jì)劃,這是提出火炬計(jì)劃的最初設(shè)想。
當(dāng)時(shí),為區(qū)別于“星火計(jì)劃”,我們提出“火炬計(jì)劃”(兩把火:“星火”是重點(diǎn)推進(jìn)科技成果在農(nóng)村的應(yīng)用,“火炬”是推進(jìn)高新技術(shù)成果的商品化、產(chǎn)業(yè)化、國際化)。火炬計(jì)劃是以市場(chǎng)為導(dǎo)向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計(jì)劃,主要不是靠國家撥款來支持,雖有部分國家資金引導(dǎo),但更多是利用銀行貸款、社會(huì)資金支持,動(dòng)員各方面力量來支持科技成果的產(chǎn)業(yè)化。
計(jì)劃確立后,國家科委組織了一幫人來具體實(shí)施。到1988年6、7月份,原航天部部長(zhǎng)李緒鄂調(diào)到科委,原科委主任宋健讓他具體負(fù)責(zé)火炬計(jì)劃,后來大家習(xí)慣稱他為“火炬司令”。我那時(shí)在工業(yè)科技司,任副司長(zhǎng),工業(yè)科技司就具體負(fù)責(zé)火炬計(jì)劃的籌備工作,我們擬定《火炬計(jì)劃綱要》,當(dāng)時(shí)就搞了六七稿。后來,國家科委決定在工業(yè)科技司建設(shè)第一個(gè)火炬辦,這是一個(gè)非常設(shè)機(jī)構(gòu),方便把部?jī)?nèi)各機(jī)構(gòu)協(xié)調(diào)起來負(fù)責(zé)計(jì)劃的組織和實(shí)施。
1988年8月8日,我們?cè)诒本┻h(yuǎn)望樓賓館開了國家第一次火炬計(jì)劃的工作會(huì)議,這標(biāo)志著火炬計(jì)劃正式出臺(tái)。而在該計(jì)劃出臺(tái)前幾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戴河分別聽取了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教育部、國家計(jì)委、科學(xué)院等部門就中國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集中性研究的匯報(bào)。當(dāng)時(shí),會(huì)議紀(jì)要明確:“攻關(guān)”計(jì)劃、“863”計(jì)劃和火炬計(jì)劃是中國推進(jìn)高新技術(shù)研究發(fā)展及產(chǎn)業(yè)化的三個(gè)主要計(jì)劃。三個(gè)計(jì)劃要相互銜接、相互配合,共同支持中國高新技術(shù)從研究發(fā)展到產(chǎn)業(yè)化的過程,這確立了火炬計(jì)劃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火炬計(jì)劃跟過去的科技計(jì)劃有很大不同:第一,不是單純的科學(xué)研究計(jì)劃,是促進(jìn)研究成果商品化、產(chǎn)業(yè)化的計(jì)劃,是推進(jìn)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計(jì)劃,是為產(chǎn)業(yè)發(fā)展服務(wù)的,是為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服務(wù)的,不是單純?yōu)榭茖W(xué)研究服務(wù)的。第二,該計(jì)劃也不是以政府為導(dǎo)向,而是以市場(chǎng)為導(dǎo)向。第三,發(fā)展方針是放手發(fā)揮企業(yè)的主體作用。我們當(dāng)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兩條腿走路”:一是,充分利用國家在經(jīng)濟(jì)建設(shè)中,結(jié)合軍工、國防高科技形成的骨干高技術(shù)企業(yè)的研究力量,比如航空航天、計(jì)算機(jī)、原子能、兵器等,以作為發(fā)展高科技的主力軍。二是,發(fā)揮改革開放后形成的民辦企業(yè)(民營(yíng)企業(yè))在創(chuàng)新中的生力軍作用。
同時(shí),火炬計(jì)劃重點(diǎn)在于扶持和支持民辦企業(yè)。為什么?因?yàn)槊褶k企業(yè)以“四自原則”(即“自由組合,自主決策,自籌資金,自負(fù)盈虧”)作為基本運(yùn)行機(jī)制,不同于計(jì)劃經(jīng)濟(jì),新機(jī)制符合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且這些企業(yè)都是科技人員下海創(chuàng)辦的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不同于過去的傳統(tǒng)企業(yè),更有利于促進(jìn)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該計(jì)劃的主要經(jīng)費(fèi)來源不靠政府撥款,主要是政府引導(dǎo)基金、銀行貸款以及社會(huì)資本、風(fēng)險(xiǎn)投資(盡管當(dāng)時(shí)只有概念,并沒有理解怎么做)。
火炬計(jì)劃更重在創(chuàng)造有利于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政策環(huán)境,有別于過去計(jì)劃經(jīng)濟(jì),靠政府拿錢,搞項(xiàng)目的科技計(jì)劃。創(chuàng)造政策性環(huán)境包括:一是,創(chuàng)造局部?jī)?yōu)化的環(huán)境。通過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園區(qū)這種形式來優(yōu)化政策環(huán)境,給科技企業(yè)發(fā)展提供更好空間。二是,我們也學(xué)習(xí)了解了一些國外的好的做法,建設(shè)孵化器(我們將孵化器從國外引進(jìn)來,怕大家聽不懂,改了個(gè)名,叫高新技術(shù)創(chuàng)業(yè)服務(wù)中心(1987年,中國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第一個(gè)孵化器,在武漢東湖)。三是,實(shí)施一批創(chuàng)新的火炬計(jì)劃項(xiàng)目,不是研究項(xiàng)目,而是成果轉(zhuǎn)化、產(chǎn)業(yè)化項(xiàng)目。這些項(xiàng)目不是以撥款,而是以貸款為主。因?yàn)楫?dāng)時(shí)貸款是有指標(biāo)的,分配到不同的部門,所以很難。科技部沒有錢,我們只拿到400萬,作為引導(dǎo)基金,支持孵化器的發(fā)展。四是,培養(yǎng)復(fù)合型人才,以及相應(yīng)的科技型的企業(yè)家。此外,還有加強(qiáng)國際交流等多項(xiàng)內(nèi)容。
火炬計(jì)劃是新的、市場(chǎng)導(dǎo)向的計(jì)劃。當(dāng)時(shí),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剛剛提出向市場(chǎng)過渡,在以計(jì)劃為主,市場(chǎng)為輔的情況下,火炬計(jì)劃第一次把市場(chǎng)概念引入科技領(lǐng)域,具有很強(qiáng)的先導(dǎo)性。當(dāng)時(shí)《科技日?qǐng)?bào)》發(fā)表一篇社論,題目就是宋健定的,我記得是《創(chuàng)造有利于高技術(shù)發(fā)展的良好的環(huán)境》。這樣,就把火炬計(jì)劃定位在創(chuàng)造環(huán)境的計(jì)劃、引導(dǎo)性的計(jì)劃,而不是單純的項(xiàng)目計(jì)劃,這與過去所有科技計(jì)劃不同,也是一個(gè)創(chuàng)新。
坎坷的“火炬?zhèn)鬟f”
當(dāng)時(shí),我們提出火炬計(jì)劃,有人并不理解,包括我們科委就有人提出,我們是不是要搞產(chǎn)業(yè)化,產(chǎn)業(yè)化不是科技部門的義務(wù)。而經(jīng)濟(jì)部門更不能理解,有人認(rèn)為搞產(chǎn)業(yè)是經(jīng)濟(jì)部門的事,是計(jì)委的事,不是科委的事,認(rèn)為科委不應(yīng)該搞火炬計(jì)劃等反對(duì)聲音很多。但科委堅(jiān)信這是正確方向,把科技引進(jìn)經(jīng)濟(jì)的一個(gè)重要舉措,是深化科技改革的重要內(nèi)容。
當(dāng)時(shí),還有一些小插曲。就是在“高新”兩字上,還經(jīng)過一番討論,有人提出中國沒有高技術(shù),都是新技術(shù),應(yīng)該叫“新高技術(shù)”。后來李緒鄂指出,雖然我們的高技術(shù)少,但高技術(shù)是未來方向,所以就把“高”放在前面了。
1988年,火炬計(jì)劃剛剛實(shí)施,我們上報(bào)了武漢東湖、南京浦口等高新區(qū),國務(wù)院正在審批時(shí),動(dòng)亂發(fā)生了,許多動(dòng)亂分子來自中關(guān)村的民營(yíng)企業(yè)。當(dāng)時(shí)有人說,中關(guān)村搞資產(chǎn)階級(jí)自由化,培育了好多動(dòng)亂分子,所以高新區(qū)不能再支持了,就把這與政治聯(lián)系起來了。
我們當(dāng)時(shí)很著急,認(rèn)為不能把政治與之聯(lián)系起來。科委當(dāng)時(shí)與北京市政府聯(lián)合組成調(diào)查組,對(duì)高新區(qū)一年多時(shí)間發(fā)展的情況進(jìn)行調(diào)研。通過調(diào)查研究,聯(lián)合給國務(wù)院寫了一個(gè)報(bào)告,對(duì)高新區(qū)一年多的發(fā)展取得的成績(jī)給予肯定,澄清了其與政治運(yùn)動(dòng)的關(guān)系,表明高新區(qū)是未來發(fā)展方向,是在國家社會(huì)主義公有體制發(fā)展起來的,希望國家給予支持,這才穩(wěn)住了態(tài)勢(shì)。
當(dāng)時(shí),我們不敢提民辦企業(yè),說企業(yè)還是姓公為主,民辦企業(yè)大多還是集體的,還是姓公,國有民營(yíng)不是經(jīng)濟(jì)制度概念,而是管理運(yùn)行機(jī)制的概念。我們說盡量別把它與資產(chǎn)階級(jí)自由化,跟資本主義聯(lián)系在一塊,少數(shù)人的問題不能代表全部,而且他們也照章納稅。
這樣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我們認(rèn)為,不能只搞兩三個(gè)開發(fā)區(qū),而應(yīng)該在全國智力密集的地區(qū)通過這樣的科技園區(qū)來帶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促進(jìn)成果轉(zhuǎn)化,發(fā)展新興產(chǎn)業(yè)。值得欣慰的是,到1991年,國務(wù)院一下子批準(zhǔn)了26個(gè)開發(fā)區(qū),并且發(fā)布了配套政策。
要知道,在當(dāng)時(shí)配套政策很難。我們協(xié)調(diào)了財(cái)政部、稅務(wù)局、外事辦等十多個(gè)部門。李緒鄂親自帶隊(duì),去了很不受重視,還坐冷板凳。我們到某些財(cái)大氣粗的部門,連坐都不讓。我們帶稅務(wù)部門等到上海漕河涇、深圳調(diào)研,告訴他們減免稅收是為了以后增加稅源。當(dāng)時(shí),稅務(wù)總局在千方百計(jì)增加稅收,要它放水養(yǎng)魚很難。而經(jīng)過一年多努力,終于還是給了支持。
當(dāng)然,我們要感謝時(shí)任國務(wù)院領(lǐng)導(dǎo)給予的很多支持。比如原國務(wù)院副秘書長(zhǎng)徐志堅(jiān)親自幫助做了很多協(xié)調(diào)工作;時(shí)任國務(wù)院總理李鵬也很關(guān)注,當(dāng)時(shí)他給高新區(qū)幾個(gè)定位:改革開放的試驗(yàn)區(qū)、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的重要基地、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要基地等。
經(jīng)過三年發(fā)展,我們?cè)谥醒腚娨暸_(tái)搞了一個(gè)火炬計(jì)劃巡禮,小平同志看到后甚至破例主動(dòng)給火炬計(jì)劃題詞:“發(fā)展高科技,實(shí)現(xiàn)產(chǎn)業(yè)化。”大家很受鼓舞,這是對(duì)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化的充分肯定,把科技是第一生產(chǎn)力的作用凸顯出來,指明了今后高新技術(shù)發(fā)展方向。
20多年來,火炬計(jì)劃取得了很多成績(jī)。可以說,如果沒有火炬計(jì)劃形成的高新區(qū)以及這一整套推動(dòng)產(chǎn)業(yè)化的措施和做法,很難想象今天中國的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會(huì)是什么樣,至少要晚好多年。應(yīng)該說,火炬計(jì)劃是改革開放的產(chǎn)物,學(xué)習(xí)了國際經(jīng)驗(yàn),符合中國國情的需要,是在改革開放推動(dòng)下,形成中國特色的推動(dòng)科技成果產(chǎn)業(yè)化的一面旗幟。
通過20年的探索,我們摸索出在中國的國情下—工業(yè)基礎(chǔ)比較落后、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不高、經(jīng)費(fèi)更有限的情況下,如何發(fā)展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有利于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有利于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升級(jí),逐漸凸顯其經(jīng)濟(jì)作用;提高了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在國民生產(chǎn)總值中的戰(zhàn)略地位,在工業(yè)增加值中的比重,形成幾萬億的生產(chǎn)總值。這是當(dāng)時(shí)難以想象的。
現(xiàn)在,很多地方都離不開高新區(qū)了,高新區(qū)甚至成為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發(fā)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成為國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重要?jiǎng)恿Γ诒本虾5鹊赜殖蔀榻?jīng)濟(jì)增長(zhǎng)引擎。中央也看到,高新區(qū)發(fā)展到現(xiàn)在,不能只看到規(guī)模,其也存在很大的問題,就是成為地方經(jīng)濟(jì)追求GDP的手段,忽視了其創(chuàng)新作用。這種情況下,批準(zhǔn)了北京、上海、武漢東湖等地作為自主創(chuàng)新示范園區(qū),希望高新技術(shù)園區(qū)成為推動(dòng)自主創(chuàng)新,擔(dān)負(fù)起建設(shè)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重任,而不是簡(jiǎn)單是擴(kuò)大產(chǎn)業(yè)規(guī)模,擴(kuò)大規(guī)模還是要靠產(chǎn)業(yè)園區(qū)、經(jīng)濟(jì)園區(qū)。
高新區(qū)的發(fā)展經(jīng)驗(yàn),為今后戰(zhàn)略新興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在發(fā)展戰(zhàn)略新興產(chǎn)業(yè)的過程中,也要充分利用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園區(qū),特別是自主創(chuàng)新示范區(qū),以引領(lǐng)高新技術(shù)。其實(shí),戰(zhàn)略新興產(chǎn)業(yè)就是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只是新的概念、新的提法。為適應(yīng)新的科技革命的要求,戰(zhàn)略新興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一定要吸取20多年來推進(jìn)火炬計(jì)劃,通過推進(jìn)高新技術(shù)園區(qū)建設(shè),培育企業(yè)發(fā)展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的經(jīng)驗(yàn)。這是在群眾創(chuàng)造基礎(chǔ)上形成的符合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應(yīng)該很好地繼承和發(fā)揚(yáng),不要再另搞一套。
現(xiàn)在,國家已經(jīng)批準(zhǔn)88個(gè)國家級(jí)高新區(qū),131多個(gè)經(jīng)濟(jì)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進(jìn)一步促進(jìn)科技力量集聚。園區(qū)為企業(yè)創(chuàng)建、孵化提供了很好的環(huán)境。現(xiàn)在全國已經(jīng)建立好幾百家孵化器,往前還有苗圃,往后有加速器,有生產(chǎn)力促進(jìn)中心,有創(chuàng)新聯(lián)盟,這些都是創(chuàng)新體系不同階段的重要形式。我們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到很多地方去都要進(jìn)高新區(qū)視察,因?yàn)楦咝聟^(qū)代表這個(gè)地區(qū)和我們國家的未來。
當(dāng)然,這要?dú)w結(jié)于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gè)很好的平臺(tái)。知識(shí)創(chuàng)新集中在大學(xué)研究所,成果轉(zhuǎn)化要通過技術(shù)創(chuàng)新,技術(shù)創(chuàng)新要以企業(yè)為主體,以市場(chǎng)為導(dǎo)向,產(chǎn)學(xué)研合作。這樣的體系應(yīng)該是將來形成戰(zhàn)略新興產(chǎn)業(yè)的核心力量,也是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建設(shè)的重要組成部分。
開發(fā)區(qū)去往何方?
《新經(jīng)濟(jì)導(dǎo)刊》:現(xiàn)在,國家、各地政府批了很多開發(fā)區(qū),而以優(yōu)惠政策帶來的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正逐漸下降,開發(fā)區(qū)將如何走?
石定寰:開發(fā)區(qū)要形成良好的環(huán)境。環(huán)境是通過政府政策,通過服務(wù),通過軟硬件建設(shè)等各方面來體現(xiàn),這樣對(duì)產(chǎn)業(yè)形成集聚效應(yīng)、產(chǎn)業(yè)集群,形成上下游結(jié)合的產(chǎn)業(yè)鏈,在不同園區(qū)形成不同的特色產(chǎn)業(yè),形成新興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良性機(jī)制。
政策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采購、金融財(cái)稅、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法規(guī)等。任何時(shí)候政策都很重要,政策不會(huì)退出。當(dāng)然減免稅的政策可能在一段時(shí)間。比如企業(yè)所得稅從原來的“三免兩減半”變成現(xiàn)在的統(tǒng)一按15%征收。任何國家對(duì)新興產(chǎn)業(yè)都是有政策扶持的,如果沒有扶持,很難發(fā)展起來,但政策扶持只是一個(gè)過程,將來一定要走向市場(chǎng)。
在不同時(shí)期,政策內(nèi)容不同,特點(diǎn)不同。怎樣引導(dǎo)社會(huì)資本,包括私募股權(quán)投資基金參與支持發(fā)展?金融、進(jìn)出口政策等怎樣支持?政策環(huán)境需要不斷完善,服務(wù)水平需要提高。比如建立孵化器,現(xiàn)在不光是幫它租個(gè)樓,而是要對(duì)它進(jìn)行服務(wù),進(jìn)行輔導(dǎo)。孵化器種類等越來越多,將來朝專業(yè)孵化器方向發(fā)展,園區(qū)對(duì)企業(yè)發(fā)展服務(wù)水平要求越來越高。
開發(fā)區(qū)的發(fā)展,首先要強(qiáng)調(diào)創(chuàng)新,未來在關(guān)鍵技術(shù),在核心技術(shù)方面,我們要擁有主導(dǎo)權(quán),但這不等于不要國際合作,從根本上要提高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園區(qū)在發(fā)展中,要形成產(chǎn)業(yè)群、產(chǎn)業(yè)鏈,在創(chuàng)新中不斷發(fā)展,形成有利于創(chuàng)新的基地,這對(duì)開發(fā)區(qū)非常重要。
《新經(jīng)濟(jì)導(dǎo)刊》:比較普遍的問題是,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績(jī)工程、惟GDP主義的驅(qū)使下,還是比較急功近利,對(duì)開發(fā)區(qū)盲目擴(kuò)張,搞圈地運(yùn)動(dòng)。您如何看待這種現(xiàn)象?
石定寰:隨著落實(shí)科學(xué)發(fā)展觀,轉(zhuǎn)變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方式,地方政府逐漸看到創(chuàng)新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驅(qū)動(dòng)力,特別是園區(qū)在推動(dòng)創(chuàng)新方面,有很好的手段和土壤,各地方會(huì)更加重視創(chuàng)新的作用。現(xiàn)在有些地方解決得比較好,更有戰(zhàn)略發(fā)展眼光,發(fā)揮科技園區(qū)對(duì)創(chuàng)新的支撐、引領(lǐng)作用,而不是急功近利,光讓它去創(chuàng)造GDP。
很多開發(fā)區(qū)有看重GDP的傾向,如果對(duì)GDP過分看重,就可能忽視其對(duì)創(chuàng)新的促進(jìn)作用。創(chuàng)新的培養(yǎng)需要過程,不可能今天種下一棵種子,明天就長(zhǎng)成大樹,因此需要長(zhǎng)遠(yuǎn)支持,起碼要將近期、中期的支持與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結(jié)合起來。不搞長(zhǎng)遠(yuǎn),沒有方向,只搞長(zhǎng)遠(yuǎn),沒有后勁,因此要遠(yuǎn)近結(jié)合,使產(chǎn)業(yè)有效、有序、可持續(xù)發(fā)展。這需要園區(qū)在發(fā)展戰(zhàn)略上研究布局。
另外,各園區(qū)要辦出特色,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shì),不要雷同,全都是一樣的東西,那就是無序競(jìng)爭(zhēng)。要在區(qū)域中加強(qiáng)總體規(guī)劃,在區(qū)域經(jīng)濟(jì)之中,加強(qiáng)優(yōu)化的布局,產(chǎn)業(yè)鏈的形成要更好關(guān)注。這給地方經(jīng)濟(jì)發(fā)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導(dǎo)建設(shè)整個(gè)區(qū)域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要跟中國整個(gè)戰(zhàn)略新興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更加有機(jī)地結(jié)合起來,而不是獨(dú)立看待地方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
《新經(jīng)濟(jì)導(dǎo)刊》:目前經(jīng)濟(jì)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和高新區(qū)功能定位有些模糊,分不清各自扮演的角色。
石定寰:現(xiàn)在很多經(jīng)濟(jì)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光靠引進(jìn)顯然不夠,都把高新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的要素(如科技孵化等)拿進(jìn)去了。事實(shí)上,經(jīng)濟(jì)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與高新區(qū)的融合也是一種趨勢(shì),兩者應(yīng)該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開發(fā)區(qū)更要重視自主創(chuàng)新,把自主創(chuàng)新作為自己更大的特色,而經(jīng)濟(jì)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更注重產(chǎn)業(yè)發(fā)展。有的地區(qū)把兩者融合起來了,效果很好。地區(qū)內(nèi)要總體布局,不要讓兩者爭(zhēng)項(xiàng)目,互相打仗,要有合理布局。地方政府需要做很多工作。
《新經(jīng)濟(jì)導(dǎo)刊》:另一種現(xiàn)象是,很多開發(fā)區(qū)獨(dú)立于城市的功能之外,甚至與城市脫節(jié)。有人擔(dān)心這樣是否不利于挽留優(yōu)秀人才,甚至影響開發(fā)區(qū)長(zhǎng)遠(yuǎn)發(fā)展?
石定寰:這個(gè)問題值得注意。長(zhǎng)期以來,城市建設(shè)強(qiáng)調(diào)“先生產(chǎn),后生活”,只管生產(chǎn),不管生活,把園區(qū)變成產(chǎn)業(yè)區(qū)了,造成白天熱鬧,晚上一片漆黑,沒有人氣,這樣對(duì)城市長(zhǎng)遠(yuǎn)的發(fā)展,對(duì)城市交通的發(fā)展都非常不利。發(fā)展初期,開發(fā)區(qū)想要兼顧兩者,沒那么多精力。
將來高新區(qū)也是綠色發(fā)展區(qū)、低碳發(fā)展區(qū)、適宜人居區(qū),高新區(qū)聚集的都是知識(shí)型、科技型的產(chǎn)業(yè),更多的是研發(fā)、設(shè)計(jì)或關(guān)鍵技術(shù)制造、總裝、銷售等,將來更多依靠人的智力,不可能與人離得太遠(yuǎn)。將來,居住、產(chǎn)業(yè)、研發(fā)在一個(gè)區(qū)內(nèi),并且更加有機(jī)結(jié)合,盡可能就近工作,就近生活。當(dāng)然,有些制造環(huán)節(jié)可以放到其他地方,與經(jīng)濟(jì)開發(fā)區(qū)進(jìn)行結(ji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