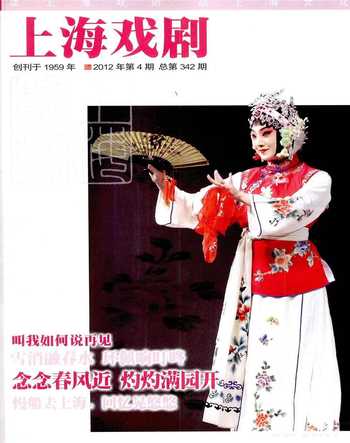無為而治與多管閑事
聞韶
孫虹江從小生活在一個文藝家庭。父親在解放初是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文工團的領導,之后在上海成立的華東戲曲研究院中,擔任副秘書長一職,和周信芳、袁雪芬同事,多年后還是周信芳的入黨介紹人。用孫虹江的話說,從小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即使再不留意,也不可能不感受到藝術的熏陶。
1960年,11歲的孫虹江進了上海京劇院學館,開始學小生。年輕時候的他長得英俊,嗓子也好,又加上從小就“腦子活絡”,很快便在同輩學生中脫穎而出。那個時候的世界,對于年輕的孫虹江而言,正等著他大展拳腳。意氣奮發的他,沒有想到呂布也要唱《白門樓》,周瑜也會魂斷巴丘。一場“文革”,將孫虹江的生活徹底翻了個個一父親被打倒了,他自己~個優秀的小生,一下子淪落到了靠邊站的地位。生活的突變令孫虹江一時難以招架,他苦悶、頹廢。就在這個時候,來了一位“知心朋友”,單純的孫虹江將自己心中的煩惱向“朋友”一五一十地傾訴。令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朋友”剛向他告別,一轉身就將兩人的對話全部匯報給了領導。這下,原本籍籍無名的孫虹江成了逍遙派不逍遙的典型,有領導放出話來:“像孫虹江這樣的人,絕對不能留在文藝界。”
在當時,這句話等于是給孫虹江判了死刑,盡管心中有怎樣的不甘,卻不得不接受現實。1970年,21歲的孫虹江進了上海四方鍋爐廠,開始當一名工人,學做車床、銑床。夏天的時候,他和同事兩個人一組,拉著人力平板車,一個車間一個車間地換保溫桶里的酸梅湯,整個廠子十幾個車間換下來,人都已經累得散了架。就這樣一干三年多。恨歲月蹉跎,消磨了英雄志。
孫虹江說,他的生命中有兩位“貴人”。一位是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而另一位則是他的恩師,著名越劇導演吳琛。孫虹江至今說起袁老師,依舊難掩激動和感激之情。“如果沒有袁老師,絕不會有我的今天”。1973年,上海越劇院學館對外招生,學生有了,卻缺少師資。這個時候,袁雪芬想到了“故人之子”孫虹江,經她推薦,孫虹江離開工廠,來到學館當老師,負責教趙志剛、陳穎他們這一批學生。
“十多年之前進京劇院唱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家庭的影響,我自己并沒有什么明確的目標;十多年之后來到越劇院學館教書,我多多少少是憋著一口氣的——你們不是說孫虹江不能留在文藝界嗎?我還是回來了,既然回來了,就要搞出些名堂來。”孫虹江深知機會的來之不易,因此也比別人更為勤奮用心“在學館當老師那幾年,我沒有請過一天假,積攢下來的調休單,放在桌上有厚厚的一摞。”除了教戲課,他還經常要頂別的課——政治課、文化課。到后來,簡直成了無所不能的“萬能替補”。而幽默風趣的“孫老師”,也特別受學生歡迎,“同學們都特別喜歡我,因為我會給他們講故事”。
因為表現突出,很快,孫虹江便從一名普通教師被提拔做了學館的領導,令孫虹江感到特別自豪的是“當了領導之后,我和袁老師在一個辦公室里辦公,兩人的辦公桌面對面。”也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孫虹江開始嘗試編劇導演的創作。不久,上海戲劇學院開始面向專業藝術院團招生。得知這個消息,袁雪芬和學館的另一位老師項彩蓮不約而同地打電話向時任戲劇學院院長蘇堃和導演系系主任章琴推薦孫虹江。當時,戲劇學院計劃開兩個進修班,一個是導演進修班,另一個是編劇進修班。孫虹江當時對于寫劇本和當導演都挺感興趣,自己也難以取舍,索性把決定權交給了命運——哪個班先開就去哪里。結果,導演班先開始招生,由此便決定了孫虹江后來的事業。
在一年半導演進修班的學習中,孫虹江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位“貴人”——恩師吳琛:“記得第一次接觸到吳琛老師,是他來給我們上的課,說他怎么排《祥林嫂》。一堂課有40多個學生,我和他并沒有面對面的接觸,估計那個時候他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我。”
然而,又是袁雪芬,把夢變成了現實。1979年,吳琛正在越劇院導演《西廂記》,孫虹江經常利用學校放假的機會,來到排練場看吳琛怎么給演員排戲。一天,袁雪芬把孫虹江帶到吳琛面前,對吳琛說:“你這一肚皮的東西,不能讓它爛在肚子里啊。”就這么簡單,因為袁雪芬的一句話,孫虹江成了吳琛的關門弟子,在老師身邊呆了八年。孫虹江清楚地記得他獨立當導演的處女作《何文秀》開排時,對于給誰排、怎么排,大家的意見很不統一。這個時候,吳琛對孫虹江說了一句話“你先排起來再說,只要你排得好,一切都不是問題。”于是,在一切都是未知數的情況下,初出茅廬的孫虹江,帶著同樣剛嶄露頭角的趙志剛等青年演員“自說自話”地排了起來——燈光、道具、服裝都是后來才一一到位的。不過令孫虹江頗感得意的是:“雖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何文秀》的導演手法還是有很多不足的。但是越劇院的《何文秀》一直演到今天,用的還是我們當年的版本。”
說起吳琛導戲,孫虹江最深的印象是,吳琛一直堅持“一名好的導演是應該化在演員之中的”。一出戲,如果讓觀眾總是感覺到導演的存在,那就算不得是好戲。吳琛導戲有個特色,就是剛開排的幾天里,他根本不會給演員具體指導,而是要求演員根據劇本先寫角色分析,琢磨人物,待演員有了自己的想法感覺之后,他再予以輔導。這種導演風格也深深影響到孫虹江的工作習慣。不少演員在開排之初,會覺得孫虹江是一個“無為而治”的導演。“基本上我在排練場很少發火,會給演員很大的創造空間。以至有些演員在一開始的時候,顯得松松垮垮,我一般也不會去指責、干預。”孫虹江說,他自己也做過演員,因此明白往往這個時候,演員正是在尋找感覺:“一旦找到了,他們馬上就會像換了個人似的。不過,如果你是心里在想別的事情,而不用心排練,那我訓斥起來也是不留情面的。”孫虹江說他自己人緣很好,很少得罪人,尤其和演員關系都特別鐵:“在越劇院的時候,我和老演員、小演員都打得火熱了。”要說好脾氣的孫虹江有沒有什么壞毛病?他自己承認有一個,就是身為導演卻喜歡“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去改劇本。不過,雖然也因此得罪過人,但更多的時候,大家都能理解是為了追求藝術質量,必要的修改對于整體藝術的提高,還是有很大幫助的。
最近這段時間,孫虹江一直忙著袁雪芬九十周年誕辰的專場導演工作,而當年吳琛老師排演的《祥林嫂》也正在他的主持下進行復排。在這時候,孫虹江又感覺自己和兩位恩師、恩人離得很近、很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