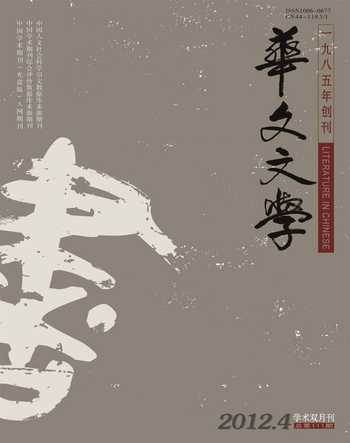莊子現代命運概說
劉劍梅
摘要:莊子在現代中國經歷了一個和現代知識分子大體相同的命運,其命運充分體現了個體精神在中國的沉浮,折射出中國文學在二十世紀的跌宕起伏,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復雜的思想變遷和坎坷的精神歷程。《莊子的現代命運》試圖超越文學,而跨入大文化領域,涉及文史哲諸人文向度,涵蓋的中國作家學者包括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林語堂、廢名、關鋒、劉小楓、汪曾祺、韓少功、阿城、閻連科、高行健等,展示了莊子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與現代思想史上的命運變遷,以此暗示個體自由獨立精神在中國現代社會中的困境。
關鍵詞:莊子;老子;禪宗;梭羅;個人主義;自由精神;逍遙游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2)4-0103-08
一、課題選擇的歷史語境
甲午海戰之后,中國知識分子一直為國家失敗的大恥辱所煎熬,所以內心便形成一種家國情結,用夏志清的語言表達,這是“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情結。這種情結導致了近代中國文學發生一大“偏執”現象,那就是文學藝術只有家國空間,而缺少個人獨立、自由的精神空間。
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然也有愛國內容,但從文化核心精神上說,它的特點,是強調個體,突出個體。辛亥前后的啟蒙者,他們的思想重心,不是側重于個體,而是側重于群體,即側重于“民族——國家”這一大群體。個人不是目的,國家才是目的,如梁啟超在《新民說·論自由》中所言:“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①他后來更是轉成國家至上主義者,認為伯倫知理的強調犧牲個體以利國家的思想在中國的語境中比盧梭的民權思想高明。②就連嚴復翻譯穆勒的《自由論》時,也“修正”了穆勒突出個人的思想,而把個人當做服務于國家的手段。本杰明·史華慈比較了穆勒的原文和嚴復的譯文,得出結論道:“假如說穆勒常以個人自由作為目的本身,那么,嚴復則把個人自由變成一個促進‘民智民德以及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③
不同于晚清民初強調“群”,五四強調的是“己”,高舉的是個人主義的旗幟。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紛紛質疑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比如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中,就把“國家”視為應該加以破壞的一種“偶像”:“國家是個什么?……我老實說一句,國家也是一種偶像。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或數種人民集合起來,占據一塊土地,假定的名稱。若除去人民,單剩一塊土地,便不見國家在那里,便不知國家是什么。可見國家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他本身亦無什么真實能力……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④在隨后發表的《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陳獨秀更加徹底地表白說:“近來有一部分思想高遠的人,或是相信個人主義,或是相信世界主義,不但窺破國家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沒有價值,并且眼見耳聞許多對內對外的黑暗罪惡,都是在國家名義之下做出來的。”⑤五四知識分子之所以把尼采和易卜生當作旗幟,也是為了張揚個人,把個人放在先于國家的地位。如胡適就提出:“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⑥周作人在《人與文學》中,明確地提出他所說的人道主義不是“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⑦他堅決反對國家偶像,認為現代中國“最需要的愛國心應該是個人主義的而不是國家主義的,——為了自己故而愛國,非為國家故而愛國”。⑧當時創作社的郭沫若、郁達夫提出兩個基本口號,一個是為自我而藝術,一個是為藝術而藝術。郭沫若寫的《天狗》和《鳳凰涅槃》都把自我放到了頭等重要的地位。
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中國的社會危機并未解除,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在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前,五四新文化的先鋒們紛紛感到繼續張揚自我、突出個體已不合時宜。1925年創造社主將郭沫若公開宣布:“我的思想,我的生活,我的作風,在最近一兩年內可以說是完全變了。我從前是尊重個性、信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⑨基于這種認識,左翼作家們紛紛接受馬克思主義,自覺地把文學當作服務于政治的工具。二十年代中后期出現的“革命文學”,意味著階級意識的覺醒,在此意識之下,人被定義成有階級性的人,被分成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樣,作為個體的、獨立的人的觀念越來越沒有生存的空間,就連倡導“革命加戀愛”的蔣光慈也因為涉及“個人”的“小資產階級觀念”而被開除出黨。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和魯迅對梁實秋“人性論”的激烈批判說明個體意識已無立足之所。到了延安時期和新中國時期,“個人主義”更是成了必須清除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最后,隨著經濟的國有化,個體心靈也被國有化,自我意識和個體自由幾乎被全面消滅。
直到八十年代,個人意識才重新回歸。“人”、“人性”、“自我”、“主體性”這些被視為“異端”的人文話語才重新走上歷史平臺。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理論呼喚個性話語,呼喚“在文學的各個環節中,恢復人的主體地位,以人為中心,為目的。”⑩在文學創作上,朦朧詩、尋根小說和實驗小說等都脫離了政治式寫作和“集體經驗語言”,而找到了“個體經驗語言”,逐漸回到了文學“自性”,從而與五四的思想相通相接。
在這種大的歷史語境下,我選擇中國知識分子對待莊子的態度作為研究課題,因為莊子在現代中國經歷了一個和現代知識分子現代作家大體相同的命運。在我看來,莊子精神的核心就是突出個體、張揚個性、解放自我的精神。莊子是最早把個體存在區別于群體存在的中國哲學家。李澤厚說,莊子“關心的不是倫理、政治問題,而是個體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問題。”{11}徐復觀也指出“莊子為求得精神上之自由解放,自然而然地達到了近代之所謂藝術精神的境域。”{12}正因為如此,可以說,莊子在現代中國的命運,正是中國個體存在、個體精神的命運。莊子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折射著中國文學在二十世紀的起落浮沉,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復雜的思想變遷和坎坷的心路歷程。
二、我對莊子的基本認識
第一,儒道的區別
正如劉再復所言,“中國文化有兩大脈:一脈是以儒家為代表,重秩序、重教化、重倫理;另一脈以老莊為代表,重個性、重自由,重自然。”{13}后一脈是前一脈的補充,所以李澤厚才在《華夏美學》中提出“儒道互補”的理念:
表面上看,儒、道是離異而對立的,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一個樂觀進取,一個消極退避;但實際上它們剛好相互補充而協調。不但“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經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補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與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也成為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常規心理及其藝術意念。但是,儒、道又畢竟是離異的。如果說荀子強調的是“性無偽則不能自美”;那么莊子強調的卻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強調藝術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藝術的獨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狹隘實用的功利框架,經常造成對藝術和審美的束縛、損害和破壞;那么,后者則恰恰給予這種框架和束縛以強有力的沖擊、解脫和否定。{14}
儒家強調“自然的人化”,強調社會規范,強調個人納入群體道德倫理秩序,而莊子講的是“人的自然化”,強調個人可以超越既定秩序而贏得個體自由。{15}儒家要求個體服從社會秩序的規范,而莊子則支持個體脫離社會關系的束縛,回歸生命的本真本然,從而得到個體精神的解放。這兩者正好可以互相補充。莊子所說的逍遙游乃是“無所待”,即絕對的自由,可以說,莊子在兩千五百年前就占據了人世間自由思想的制高點。他的《逍遙游》所描述的“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于四海之外”的境界乃是精神大超脫與大自由的境界,是與宇宙相通的個體精神大飛揚的天馬行空境界——這是人類史上最早的心靈自由的境界。只有精神得到超脫,內心得到自由,才能獲得真正的快樂,也就是“至樂”——最大的快樂。他不僅很早就占領了人類思想史上“自由”的至高點,同時也占領“平等”思想的至高點。他的《齊物論》采用宇宙的眼光看事物,齊物我、泯是非、化善惡,拒絕用本質主義的尺度衡量萬物萬有,很了不起,莊子不愧為中國早期的偉大哲學家,他的自由精神與平等思想,至今仍然給人類社會以啟迪。
第二,莊子和老子的區別
平時人們總是把老莊放在一起談論。他們同屬道家,有很多思想是相通的,比如他們都以“道”為宗,都崇尚自然,“道法自然”,主張回歸于“無極“,回歸人類初始的純樸天性,然而,他們也有很大的區別,老子既是一位宇宙哲學家,更是一位政治哲學家,他的《道德經》有許多政治話語、政治策略、政治理想,它為圣人君臨天下提供治理之道;而莊子哲學則遠離是非,既不提供政治策略,也無其他政治話語,全部論說的中心集中于個體的內心自由和精神自由,本質上是一種審美哲學。
錢穆曾經這樣區分老莊:“莊子乃一玄想家,彼乃憑彼所見之純真理立論,一切功利權術漫不經心,而老子則務實際,多期求,其內心實充滿了功利與權術。故莊周之所重在天道,而老子之所用則盡屬人謀也。”{16}即使都談“無為”,可是老子的“無為”是教導圣人如何統治人民,如何追求天下“大順”;而莊子的無為,則是從自我到忘我——“吾喪我”,從而達到個體高度逍遙的境界。即使兩者都談到“圣人”,老子的圣人“卻決不肯退隱無為,又不能淡漠無私”,{17}還是從權術和利益上打算,并沒有超越世俗社會的是是非非;而莊子的圣人則“無所待”,完全超功利、超社會、超古今、超生死,超越世俗的一切好惡、是非等限制,不背負任何社會責任,也不講究任何權術與智謀,而是像大鵬一樣瀟灑自得,達到與宇宙自然合一的“至樂”。這不僅代表了一種超凡脫俗的對待人生的審美態度,也代表了一種絕對自由的個體價值觀。即使老子和莊子都著眼于“自然”,老子的自然是為了教育統治者應該順應自然規律,用“無為而治”的方式去管理社會,實現天下大治,他所說的“反者道之動”是告誡世人要返回純樸,遵循事物存在的自然之道,即“道法自然”;莊子的自然觀則是遵循自然和宇宙的規律,以進一步開辟一條個體心靈絕對自由之路,他強調人的自然本色和心的逍遙狀態,認為只有心無所求、無所待、無所執,不為外物所束縛所異化,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
如果說,老子哲學傾向于政治哲學,那么,可以說,莊子的哲學則更傾向于心靈哲學。陳鼓應說,“老子的‘道,重客觀的意義;莊子的‘道,卻從主體透升上去成為一種宇宙精神。”{18}莊子對文學藝術之所以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第三,莊子和禪宗的區別
莊禪常常被人并提,因為莊子哲學與禪宗的確有許多共同之處。比如二者都超越二元對立,追求回到生命本真的人生境界。莊子所說的“圣人無己”和“吾喪我”是通過忘記欲望與知識而進入,這和禪宗所說的“破我執”和“破法執”有相通之處;莊子的《逍遙游》和禪宗的心游、神游,追求的都是“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的與大自然和宇宙相融合的天地境界;莊子的《齊物論》所倡導的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跟禪宗的不二法門更是相通,都強調不被世俗的概念和分類所束縛,也都強調揚棄“分別相”而回到“整體相”。
然而,二者又有差別,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這樣概說二者的差別:“第一,莊子的破對待、齊生死等等,主要仍是相對主義的理性論證和思辨探討。禪則完全強調通過直觀領悟。……第二,莊所樹立夸揚的是某種理想人格,即能做‘逍遙游的‘圣人、‘真人、‘神人,禪所強調的卻是某種具有神秘經驗性質的心靈體驗。”{19}李澤厚指出的這兩點差別都很重要,但是還需補充一點的是,莊子的“圣人”、“真人”、“神人”都是達到與宇宙共生這一高度的理想人格,可是禪宗則不追求這些人格理想,而是回歸“平常心”,從日常生活中感悟人生的真諦,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要用“平常心”來面對,在頓悟中體會到人生形而上的意義。“即心是佛”的說法意味著“此‘心被轉換成了平常心。”{20}馬祖及其弟子們提出“平常心是道”,與真人載道、至人載道、神人載道的思路大不相同。如果說莊子還需要“真人”、“至人”、“神人”來充當“道”的載體,那么,到了慧能、馬祖,則自我之心便是道的載體。禪宗在這里實際上又找出了另一條心靈自由之路。很個人化,但又可以抵制自我膨脹。禪宗這種得道仍當平常人的思想比尼采那種得道后便當“超人”的思想,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第四,莊子和梭羅的區別
美國近代的卓越散文家梭羅很像西方的莊子。他雖然沒有讀過《莊子》,可是許多觀念卻與莊子哲學相契合。首先,他們都熱愛大自然。莊子追求“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梭羅受到愛默生的超驗主義的影響,其心目中的自然是有靈性的,他認為自然可以不依賴人類存在,而人卻離不開自然,所以人們要與自然和諧相處,要摯愛大自然,保護大自然,并感悟大自然。
其次,莊子和梭羅都是反異化的先鋒,他們都同樣選擇過最簡單最質樸的生活,而沉浸在豐富的精神世界中,避免被外部力量所物化、所異化。莊子“抗議‘人為物役,他要求‘不物于物”,要求恢復和回到人的‘本性。這可能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反異化的呼聲,它產生在文明的發軔期。”{21}莊子感慨人們“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弛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22}他認為以物易性,“喪己于物”,追求外物而迷失自己的本性,是極其可悲的。梭羅所生活的時代正是美國工業化迅速發展、物欲橫流的時代,人在不斷地掠奪大自然以滿足自己膨脹的欲望,同時也淪落為欲望和金錢的奴隸。梭羅對工業社會進行了諷刺:“我們沒有乘坐鐵路,鐵路倒乘坐了我們。”{23}“人類已經成為他們的工具的工具”,{24}“除了做一架機器之外,他沒時間來做別的,”{25}“我常想,不是人在放牛,簡直是牛在牧人。”{26}梭羅厭惡這種被外物異化的生活,主張人應該把自己從物欲中解放出來,過最簡單而樸素的生活。他自己就身體力行,在瓦爾登湖過了兩年多的遠離塵囂的孤獨而簡樸的生活,回歸生活的本真狀態。
雖然梭羅和莊子在自然觀上有許多相通之處,可是他們還是各有偏重。莊子哲學是以人為本位的,從人的角度來體認自然,歸根結蒂,莊子還是人生哲學,關心的是“個體的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問題”,{27}是從人的角度出發,尋找內心的自由境界,達到精神的超越,獲得一種最高的審美境界。說到底,還是生命自然本體論。而梭羅則是“外部自然本體論”,一切以大自然為中心。一方面他跟愛默生一樣,認為大自然之中有一種“超靈”的宇宙精神,“最接近萬物的乃是創造一切的一股力量”,自然本身是一種權利主體,“我腳下所踩的大地并非死的、惰性的物質;它是一個身體,有著精神,是有機的,隨著精神的影響而流動。”{28}所以他反對人類中心論,不認同把自然視為人類可以利用的資源,而是擁有明顯的生態中心論的思想,認為自然是自足的、實在的、具體的,自然不屬于人,人卻屬于自然,“人是什么?還不是一團溶解的泥土?”{29}所以,他認為人要跟自然和諧地相處:“要保證健康,一個人同自然的關系必須接近一種人際關系……我不能設想任何生活是名副其實的生活,除非人們同自然有著某種溫柔的關系。”{30}“難道禽獸不是跟人類一樣,也存在著一種文明嗎?”{31}在梭羅的心目中,大自然比人類純潔,比人類美好。他贊美自然說:“他們真太純潔,不能有市場價格,他們沒被污染。它們比起我們的生命來,不知美了多少,比起我們的性格來,不知透明了多少!”{32}
莊子在《逍遙游》中,用大鵬的高飛來俯視人間,采用的是宇宙的視野,他所描述的“乘云氣,御飛龍”不只是形體上的自由,而且是心靈的自由,讓心從萬物的羈絆中脫離出來,獲得大自在。梭羅希望從工業文明中逃離出來,但是他的逃離之路不是莊子那種精神逍遙,而是投身于大自然之中即可。
三、莊子現代命運的階段表述
莊子在現代中國的命運大致經歷了下列幾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第一,莊子的“新裝”時期;第二,莊子夢的破滅時期;第三,莊子的厄運時期;第四,莊子的回歸時期;第五,莊子的凱旋時期。
第一,莊子被披上現代哲學“新裝”的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個突出個人的運動,他們選擇了儒家——孔家店作為主要打擊對象。于是,先秦諸子中,孔子是最倒霉的,他承擔了中國舊文化的全部罪惡。而莊子、墨子則比較幸運。墨子為魯迅所崇尚,莊子則為郭沫若所崇尚。郭沫若在新文化運動中,用最浪漫和最熱情的語言把老子和莊子封為“極端反對迷信思想之純正哲學家”,稱他們擁有一種現代的“革命”的反抗的精神,而他們的哲學思想也被闡釋為是“解放個性”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哲學”。{33}在他的詩作《三個泛神論者》中,他為莊子貼上了“泛神論”的標簽,把莊子哲學和斯賓諾莎的“泛神論”相提并論。郭沫若所理解的泛神論是這樣的:“一切的自然只是神底表現,我也只是神底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現。人到無我的時候,與神合體,超越時空,而等齊生死。”{34}這種理解與莊子反對物役、追求自由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于是,被貼上“泛神論”標簽的莊子承載了郭沫若所理解的五四的浪漫激情和個人主義。他把莊子理解成一個無限擴大的“超人”的個體,一種充滿自我擴張和叛逆精神的性格——這種對莊子的浪漫性闡釋與他當時的文學觀是一致的,那個時期的郭沫若認為“生命底文學是個性的文學,因為生命是完全自主自律的”,{35}那時候的郭沫若,自己倡導文學的自主精神,把莊子描述成自由的先驅。
五四時期的胡適則給莊子換上了“進化論”的新裝。自從嚴復的“天演論”問世,“進化論”一直是時髦的現代理論。胡適在1919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一書的莊子章節中,首次把莊子思想連接上“生物進化觀”,他認為“‘自化二字,是《莊子》生物進化論的大旨。”{36}胡適講述的重心當時是從杜威的實用主義角度審視莊子,但也用進化論來檢驗莊子哲學是否能夠符合現代社會的要求,是否對拯救中國和建設現代中國有幫助。不過,胡適拿達爾文主義來丈量莊子實在是非常勉強的。莊子雖然承認生物在自化(這一點不違背進化論),但在社會層面上,莊子卻完全不認為社會總是在進化。他在《大宗師》中提出一個重大思想,就是“無古今”思想,{37}也就是認為不要人為地分別古代和現代,莊子認同的時間觀是永恒的“天人合一”的時間觀,既然無古無今,當然也就無所謂進化不進化,這自然不同于線性的進步的時間觀。更重要的是,無論是老子還是莊子,實際上都是社會退化論者,老子的“小國寡民”是反對進步的,而莊子也認為技術的進步會產生“機心“,會帶來人性的異化,他的理想國一點都沒有“進化”的步驟,反而是返回純樸的自然。很明顯,把進化論的標簽貼在莊子的臉上完全是硬貼硬套。不過,胡適為莊子換上了“進化論”的新裝后,還是用杜威的實驗主義照見了莊子對中國國民性的負面影響,這就是“差不多”的籠統態度,缺乏嚴謹的科學分析精神,所以胡適干脆給莊子封為“東方的懶惰圣人”。在胡適眼里,雖然可以給莊子貼上西方的進化論的標簽,但是莊子還不真正“現代化”,還不能成為中國現代性的合適的文化資源,他說:“莊子是知道進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進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為人力全無助進的效能,因此他雖說天道進化,卻實在是守舊黨的祖師。他的學說實在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38}實際上胡適還是把“進化論”看得比莊子的哲學高,用“進化論”來看莊子,而忽視了莊子物質發展和精神發展不平衡的文化精神。
第二,莊子夢的破滅時期。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壇才剛剛樹立起個人主義的旗幟,不久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產生分化,有的從“提倡啟蒙”走向“超越啟蒙”(如魯迅),有的拋棄個人主義而高舉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如郭沫若),有的則逃入“自己的園地”(如周作人)。最后這部分作家實際上想當現代莊子,可是他們都經歷了莊子夢的破滅。五四過后,左翼知識分子投入到“革命文學”的時代潮流中,自然就得告別莊子,郭沫若于1923年寫了歷史小說《柱下史入關》和《溪園吏游梁》,對老莊哲學不再采取熱烈擁抱與浪漫謳歌的態度,而是與老莊拉開了一定的距離。老子和莊子在這兩篇小說中不再是浪漫的“革命思想家”,而是在生活中磕磕碰碰,連日常生活中的溫飽都成問題的可憐蟲。1924年,郭沫若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完全放棄了五四的“為自我而藝術”的主張,自然也就不再認同“文學的莊子”。到了四十年代,郭沫若在《莊子的批判》中對于莊子進行了學術性的梳理,用馬克思唯物主義重新評判莊子,認為莊子哲學到了后期,變成了陰陽家和道教蠱惑人心的工具,成為神仙和“滑頭主義哲學”的源頭,說得實在太過份了。
與左翼作家的路向不同,周作人等一些“五四”的弄潮兒,選擇“退隱”到“自己的園地”中談龍說虎,抄書寫作。周作人原先在《人的文學》中立足于“個人”而表達人道主義精神,到了1921年之后,他更是從入世的啟蒙角色中抽離,與時代中心疏遠,轉向個人主義,當起了現代隱士。他所選擇的退隱立場,更加接近莊子。有些學者把周作人界定為“半是儒家半釋家”,我完全不認同這一界定,反而認為周作人雖然在“五四”高潮時期表現出“儒”的傾向,即有一定的社會關懷,但骨子里還是“莊”。所以五四之后,他便很快地進入“談龍說虎”的避世角色。我們頂多只能說周作人是先儒后莊。只可惜他既非真儒,也非真莊,更不是真釋,因為他最后的行為語言,大大出格了,這既是莊子夢的徹底破產,也說明他沒有大慈悲與大關懷,離佛很遠。他的“隱居”生活,以及回到小品文的個人選擇,在當時的文壇上已備受爭議,尤其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評。而真正可悲的是,到了日本侵略中國期間,他出任偽職,淪落為文化漢奸。他的復雜經歷是現代文人莊子夢徹底破碎的一個縮影。
1932年,林語堂創辦《論語》,大力提倡幽默,把莊子尊為“幽默”的始祖,通過幽默,他嫁接了中西文化,不僅把莊子現代化,而且試圖在中國文壇開辟一個較為輕松的文化空間。他欣賞明代“公安”、“竟陵”派的性靈文學,主張“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認為文學與政治是對立的。倘若處于平常時期,這些主張實在無可非議。然而,林語堂對莊子的這一闡釋遭到了魯迅的堅決抵制,魯迅認為只是為了“尋開心”或只是“為了笑笑而笑”的“幽默”根本不適合當時的中國,在殘酷的現實中,他主張要有鮮明的是非觀,而不辨別是非的“幽默”乃是“化兇殘為一笑”。魯迅對莊子一直采取拒絕和批判的態度。他雖然反對儒家對人性的束縛,可是他骨子里卻接受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自始至終都主張文學應該干預社會,關注社會問題,療治國民性,自始至終都熱烈擁抱是非,嫉惡如仇,所以他最痛恨老子的“不攖”和莊子的“無是非觀”。在他的小說《起死》中,他把莊子塑造成了一個表面上超脫其實攀附權貴的市儈小人,并用辛辣的筆調諷刺莊子的“無是非觀”。魯迅對待莊子的這種極端批評的態度,襯托出他對中國黑暗現實不妥協的立場,以及對重塑現代中國國民性的迫切希望,但同時也反映了魯迅不夠寬容的態度,以及他自身的“偏執”。他對所謂“第三種人”的無法容忍,對周作人、林語堂等提倡的性靈文學的排斥,對施蟄存為青年介紹莊子的強烈反映,對文人的隱逸權力的剝奪等導致了中國文人的生存空間變得更加狹小,導致中國文壇的文化空間充滿了寧左勿右的斗爭氛圍,缺少多元和諧的共存關系,使得中國現代文人連做莊子夢都不可能。
第三,莊子的厄運時期。1949年中國政權產生更替,馬克思主義取得思想統治地位。這個時期,在文化觀念上,是階級意識完全壓倒個體意識。在這個時代里,莊子的倒霉是不可避免的了。到了六十年代,莊子正式被送上政治審判臺。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是關鋒把莊子放到政治意識形態法庭上加以嚴酷批判。他把莊子打成“奴隸主殘余勢力”,比地主階級還落后反動。除此之外,關鋒還用專制的語言給莊子扣上了“滑頭主義”、“阿Q精神”等大帽子。關鋒對莊子的批判是專橫獨斷的政治批判,是強權對個體心靈的專政和扼殺。這種政治批判,無孔不入,就連富有哲學意味的郭小川的詩作《望星空》都被他批判為“是不折不扣的莊子的虛無主義、主觀唯心主義。”{39}關鋒把莊子送上政治法庭加以審判,說明在那個時代,個人自由和個體脆弱的心聲不僅毫無立足之地,而且被普遍看作是一種罪惡,這是極左思潮對莊子的一次徹底否定。郭沫若到了六十年代也出于政治的動機,決定與泛神論劃清界限,拋棄早期的自我追求。他竟然斷定泛神論是“階級騙局”,認為泛神論有欺騙和麻痹人民的作用。
莊子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間遭受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到了八十年代,劉小楓又從另一極審判莊子,這種審判,與關鋒的政治審判不同,屬于宗教審判。劉小楓首先把基督教精神“絕對”化,把“神圣價值”標準化,然后以此為參照系,整體地否定莊子,認為莊子是導致心靈冰冷的邪惡之源。劉小楓的這一思路乃是宗教獨斷論的思路。他高揚基督教思想中的拯救精神,這本來無可非議,因為這一價值體系確實充滿了崇高性與超越性,但以此而完全否定莊子的自由逍遙的精神,并把立足于“自救”思路的莊禪精神完全貶低成“石頭人格”,則是極端武斷的理念。這種理念完全不顧莊子價值體系中高揚個體心靈自由、反抗外物奴役的思想精華。在劉小楓的這一非此即彼的思路下,莊禪的價值被視為異端,莊子、陶淵明、曹雪芹均被牽連而受到了一次空前嚴峻的宗教裁判。
第四,莊子的回歸時期。從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莊子的現代命運與中國的現代政治命運息息相關。莊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和西方文化參照系所丈量、所選擇、所扭曲、所妖魔化,可以說,莊子的現代命運乃是被割裂、被利用的可憐命運。不過,八十年代,莊子在學術領域和文學創作領域有了一次回歸。在學術上,李澤厚和陳鼓應等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還原了一個本真的莊子。在文學創作上,汪曾祺在小說中描述的市井中的自然溫馨的人際關系,幾乎人人都可以成為莊子;韓少功早期的作品《爸爸爸》鞭笞的是中國當代政治生活中的病態的二極思維方式,莊子的“齊物論”對他超越這種二極思維有很大的影響,不過當時的韓少功還是繼承了魯迅批判國民性的精神,對落后和愚昧山里人進行調侃,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他就回歸到大自然,在《山南水北》中歌詠接近大自然的民俗文化;阿城的小說描述了一個個政治壓力下的“自然人”,把老莊和道家的韻味帶入現代漢語的寫作中。這三位作家通過回歸“大自然”而讓莊子以正面形象重新走進文學。閻連科的《受活》則是集體莊子進入社會被社會所異化之后的集體回歸。通過“受活村”村民們的入社和退社的舉動,把看似消極的莊子似的隱居行為變成了一種積極的對社會荒誕的反抗;而他的《711號院》更是像韓少功的《山南水北》和梭羅的《瓦爾登湖》,尋求的是在大自然中贏得內心的大自由。
第五,莊子的凱旋時期。2000年的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通過《靈山》的寫作,通過《逍遙如鳥》的詩歌實踐,把莊子的大自由、大自在精神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發現,莊子乃是從中國官方文化與正統文化網羅中站立起來的異端文化,兩千多年前的莊子早就占領了人類自由精神的制高點。中國現代文學史與莊子的關聯始終未斷,或褒或貶,或頌或刺,或宣傳或批判,但是沒有一個作家像高行健這樣明確地界定莊子的精神乃是個性飛揚的大自由精神。高行健不是一般地肯定莊子,而是充分認識到大逍遙便是大自由精神。他暗示,靈山在內不在外,要通過內心的覺悟才能找到靈山,也就是說,大自由不是他人給予的,而是自給的,自由在自己的心中,要靠自己把它開掘出來。高行健的“自救”精神,與莊子精神息息相通,高行健不僅回歸自然,而且再造一個自然,文學藝術賦予“再造”的可能性。高行健把自己的創造視為再造的伊甸園。現實生活中沒有自由,只有在文學領域中,作家才能超越現實的種種束縛,充分得到大逍遙和大自由。所以,高行健的成功,乃是現代莊子的凱旋。
四、總結
莊子在現代中國的命運,具有很豐富的象征意蘊。在現實社會層面上,莊子哲學如果掌握不好,確實可能產生消極影響,所以魯迅在那樣惡劣的社會環境中,完全拒絕莊子的無是非觀,是有他的道理的。然而,正因為現實生活沒有自由,所以才需要文學來調節人類的心靈,高揚個體精神的莊子哲學也才變得更有意義。可以說,莊子的精神才是文學的真精神。縱觀莊子在現代中國的歷程,可以看到,盡管個體自由獨立的精神歷盡坎坷,但最終還是被中國作家詩人接受。今天的莊子,在中國的精神界,還是放射著他的不滅的光彩。
① 梁啟超:《新民說·論自由》,《飲冰室合集·飲冰室專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4頁。
② 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文集全編》(第四冊),廣益書局1948年版。
③ 本杰明·史華慈著,沈文隆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臺灣:長河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頁。不同于晚清的同仁,章太炎對國家學說有批判,反對把國家凌駕于個人之上。他的國家學說完全對立于梁啟超所主張的伯倫知理的“國家至上論”。
④ 陳獨秀:《偶像破壞論》,《新青年》5卷2號,1918年8月15日。
⑤ 陳獨秀:《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每周評論》第25號,1919年6月8日。
⑥ 胡適:《介紹自己的思想》,選自洪治綱主編《胡適經典文存》,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1頁。
⑦ 周作人:《藝術與生活·人的文學》》,《周作人自選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頁。
⑧ 周作人:《對于戲劇的兩條意見》,《戲劇》第2卷第3號,1922年3月31日。
⑨ 郭沫若:《文藝論集》序,見王訓昭等編《郭沫若研究資料》(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頁。
⑩ 劉再復:《論文學主體性》,《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11}{19}{21}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第202頁,第169頁。
{12}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頁。
{13} 劉再復:《〈紅樓夢〉的哲學要點》,《國學新視野》第一期,2011年12月,第69頁。
{14}{15}{27} 李澤厚:《美學三書》,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頁,第266頁,第171頁。
{16}{17} 錢穆:《莊子通辨》,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36頁。
{18} 胡道靜主編:《十家論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頁。
{20} 賈晉華:《古典禪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頁。
{22} 莊子:《齊物論》。
{23}{24}{25}{26}{28}{29}{30}{31}{32} 梭羅:《瓦爾登湖》,徐遲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80頁,第31頁,第4頁,第47頁,第256頁,第269頁,第209頁,第240頁,第176頁。
{33} 郭沫若:《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見《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5-257頁。
{34} 郭沫若:《〈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見王訓昭等編《郭沫若研究資料》(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149頁。
{35} 郭沫若:《論詩三扎——致宗白華》,張澄寰編選《郭沫若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頁。
{36}{38} 胡適:《胡適全集》第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413頁,第429頁。
{37} 《莊子·大宗師》。“南伯子葵問乎女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無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無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朝徹,而后能見獨;見獨,而后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后成者也。”
{39} 關鋒:《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附編中《談〈望星空〉的靈魂》,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10頁。
(責任編輯:莊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