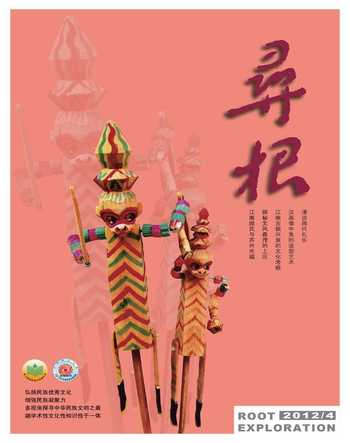圖文并茂的《耕耘》
余冰
《耕耘》是抗戰時期在香港出版的雜志,主編是當時23歲的女畫家郁風。
抗戰爆發后,內地一批文化人轉移到香港。1939年,在靠近西環的半山上一個叫學士臺的地方,有一排陳舊的樓房,住著上百戶人家。畫家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丁聰,作家葉靈鳳,詩人戴望舒、徐遲,翻譯家馮亦代等,有的是拖家帶口,有的是單身一人,大都住在這里。
郁風,1916年生于北京,浙江富陽人。父親郁華曾為著名法官,上海淪陷后被日偽特務暗殺。叔父就是著名作家郁達夫。她從北平藝專畢業后,又到南京中央大學深造。抗戰開始后在第四戰區政治部宣傳組,1939年7月初日本人占領廣州后,她到香港。學士臺是她經常去串門的地方。
《耕耘》是怎樣創刊的?郁風回憶:大家聚會在一起閑談,既然這么多人中有作家、詩人、畫家、設計家,何不辦一個刊物?從內容到形式,幾經醞釀,刊物定名《耕耘》。這年年底,剛好夏衍從桂林到香港為《救亡日報》購買印刷器材,郁風去征求他的意見。夏衍認為辦這樣一個以文藝的多種形式宣傳抗日的刊物非常好,還可以團結更多的人,成為一個統一戰線的文藝陣地。“于是我們決定了編委的名單:丁聰、徐遲、黃苗子、張正宇、葉淺予、郁風、夏衍、張光宇、葉靈鳳、戴望舒。”(郁風:《永遠值得記取》)郁風當時還沒有找到正式工作,大家推舉她任執行主編。從未編過雜志的郁風就走馬上任了。
《耕耘》沒有編輯部,各人準備自己的文章和畫作,定時交稿,同時分頭發信向全國各地的朋友們約稿。郁風負責集稿、發排、跑印刷所、看校樣、開郵箱、通訊、算稿費等一切事務。經費是大家湊的。本來馮亦代還拉了藥行的廣告,后來大家考慮,放上一點不三不四的廣告,破壞整個版面,索性放棄這個收入。經過幾個月的籌備,第一期在1940年3月印出,因為向內地和海外發行需要時日,版權頁上的出版時間是“4月1日”。兩千冊雜志大都由生活書店發行到內地,大受讀者歡迎,美術界的朋友更是如獲至寶,輾轉傳閱。
第二期《耕耘》因為經費和稿件的周轉,遲到8月才出版。第三期編好之后,郁風說:“終因戰地阻隔,賣出的書資金轉不來,眼睜睜地因為掏不出錢而看著它夭折了。”(《曾經有過這樣一本雜志:(耕耘)》)
《耕耘》僅出兩期,卻以獨具的特色在中國期刊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創刊號沒有發刊詞,郁風寫的《編后記》中說:內地“由于印刷制版條件的漸趨困難,使得不少好作品埋沒了,國外的可供參考的作品更無從輸入,各地方的藝術宣傳的新發展很難得到互相交換的好處,而這些是提高藝術水準的必要條件。同時,抗戰之后在刊物中常見的只有文學和漫畫木刻,其他姐妹藝術如雕塑、音樂、油畫或中國舊形式的水墨畫、舞俑等雖然還是鳳毛麟角,但是也應該盡量發掘介紹,使它們同樣也能得到普遍的愛好和認識,成為民族解放斗爭的武器。所以《耕耘》將試著成為上述這些工作任務的支柱之一。當然理論的建設和檢討也將是《耕耘》的主要內容”。
第二期的《致讀者》中說:“在目前中國的藝術戰線上,有兩個并重的工作任務:對于大眾的鼓勵、宣傳、教育,和促進自身進步的介紹、研究,各種表現形式的創造及嘗試。任何刊物都有一定的篇幅限制,依照編輯和印刷上不同的便利條件,或稍稍偏重于前者,或稍稍偏重于后者;在一個總的共同目標下的分工,我們相信是無害而且合理的。”
上面兩段話說明了刊物的性質和任務。《耕耘》是一本綜合性的文學藝術雜志,介紹漫畫、木刻及音樂、油畫、中國畫、舞蹈等姐妹藝術,研究這些藝術形式的創造和嘗試,為民族解放斗爭服務。
兩期《耕耘》有徐遲、韓北屏的小說,艾青、袁水拍的詩,司馬文森的散文,但篇什不多,占用最大篇幅的是兩個內容:
一是藝術的評論和研究。思慕(劉思慕)的《藝術工作者的政治武裝》,提出當前藝術工作者光是宣傳敵人的殘暴和我們戰士的英勇已經不夠了,必須對形勢有深刻的認識。巴人(王任叔)的《靈魂的探險》強調“探險者還得從個人的靈魂中出來,看看這造成罪惡的靈魂的社會階級和階級社會”。《對于現階段中國繪畫的意見》總題下刊載了盧鴻基、特偉、所亞等8位畫家針對當時美術戰線存在的問題的意見。景宋(許廣平)的《魯迅與中國木刻運動》,論述了魯迅對中國現代木刻發展的貢獻。葉靈鳳編譯的《木刻論輯》,介紹當代英美木刻家的創作經驗和技巧方法。西諦(鄭振鐸)的《關于“太平山水詩畫”》是對《中國版畫史圖錄》中一卷的介紹,意在為中國新興木刻提供中國木刻版畫的藝術遺產。適夷的《文藝和繪畫的結合——關于文藝插圖、連環圖畫》、林林的《關于民間文藝的斷想》、鄭可的《浮雕和牌雕》、吳曉邦的《中國舞俑》,分別討論了一般不常論及的藝術門類。還有常任俠作詞、張曙作曲的歌曲和戈忻(陳歌辛)為魯迅詩《慣于長夜過春時》譜的曲,發表時都用五線譜制版,并附有作者對演唱和伴奏要求的詳細說明。
一是多種形式的美術作品。漫畫、速寫、木刻等,形式多樣。張光宇、葉淺予、陽太陽、周令釗、廖冰兄、小丁、黃苗子、李樺、張望、新波、古元、沃渣等畫家幾乎是“一網打盡”。刊載的詩、散文和短篇小說都有插圖。還先后介紹了英國漫畫家大衛·羅(David Low)和美國漫畫家威廉·格羅泊爾(William Gropper),同時配發了他們的漫畫。第二期特別加了葉淺予的《魯迅六十誕辰紀念畫像》和郁風的《高爾基逝世四周年紀念畫像》,兩張全版素描插頁贈送讀者,這在當時是少有的“壯舉”。
《耕耘》封面為裝幀大家張光宇設計。郁風雖說是第一次編雜志,但在張光宇指導下出手不凡。16開本48頁的篇幅,圖版在一半以上,版面圖文穿插,美觀大氣,真正是圖文并茂。郁風說:“每篇文章盡可能有圖版配合,而且要舍得篇幅,不是鬼頭鬼腦的小豆腐干。單獨發表的美術作品就更是常用滿版。”今日看來,依然賞心悅目,充滿魅力,編輯出版行家為上世紀40年代就有如此新的設計水平而驚訝不已。
《耕耘》的版權頁列出:出版者耕耘社,編輯人郁風,發行人黃苗子。“《耕耘》之能出版,全靠黃苗子的支持。”馮亦代回憶,“他當時是國民黨在港出版的《國民日報》經理,由他的關系找到一家印刷廠承印,對外則稱這個刊物是桂林出版的。”(《我的文藝學徒生涯》)徐遲說:黃苗子“既愿意幫忙籌款,并可以去辦理那個比較難辦的在香港政府登記的手續。因為香港政府有一個出版法,刊物登記要給出三千元港幣的保證金。這事后來他也沒有辦成。但他找到了一個印刷廠承印,冒充這是一個在桂林編輯、印刷、出版的刊物,是郵運來香港出售的。這樣一來,就免交此項巨款了”。(《我的文學生涯》)刊物出版時黃苗子已由香港去重慶,版權頁的通訊處“重慶中二路224號”實際就是黃苗子的地址,虛晃一槍,再加一個“轉香港郵箱1558號”。
黃苗子,原名黃祖耀,1913年生,廣東中山人。他和郁風因為對藝術的共同愛好,在《耕耘》之前早已是朋友,《耕耘》之后而成戀人,1944年在重慶結婚。一對藝術家,甘苦相守一個甲子。“文革”中夫婦冤獄7年,同被關押在一個監獄,彼此卻不知對方身在何處。2007年,郁風遠行;2012年,黃苗子百歲去世。滄桑閱盡,《耕耘》已成清流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