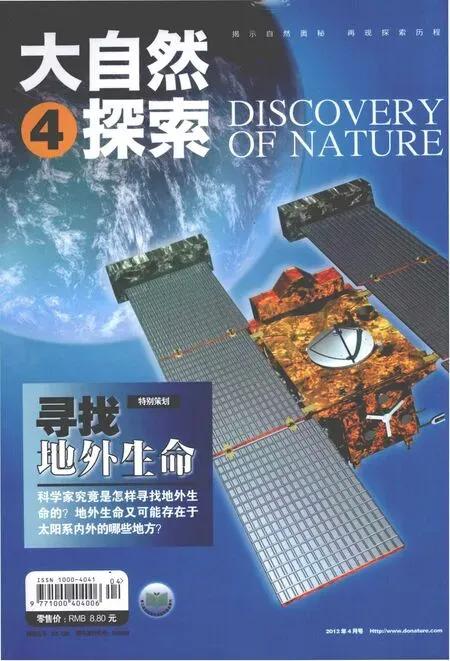我們與細(xì)菌共生共存
林聲



我們和我們體內(nèi)的微生物一起,作為一個(gè)整體,共同經(jīng)營(yíng)著不斷進(jìn)化演變的人類-微生物集居地。
在人體的許多部位都生活著細(xì)菌。我們一出生,細(xì)菌就進(jìn)入了我們體內(nèi),它們幾乎無孔不入,占據(jù)著我們的消化道、呼吸道,生活在我們的牙齒上、皮膚里,它們?cè)谖覀凅w內(nèi)建立起日益復(fù)雜的細(xì)菌群落“棲息地”,并且像森林那樣蔓延開來,當(dāng)我們長(zhǎng)到幾歲時(shí),這些細(xì)菌群落“棲息地”已經(jīng)將我們體內(nèi)的幾乎所有“空地”都覆蓋了,我們一生都將攜帶這些細(xì)菌一起生活,或多或少,相伴相隨,不離不棄。
居住在我們體內(nèi)的細(xì)菌數(shù)量十分驚人,尤以腸道中數(shù)量最多——超過100萬億個(gè),這個(gè)數(shù)字大約是人體細(xì)胞總數(shù)的10倍!然而,這個(gè)驚人的事實(shí)往往引不起我們的注意——人體細(xì)菌盡管數(shù)量龐大,但個(gè)體十分微小,總重量很輕,幾千克而已,而且我們用肉眼是看不到它們的。正因此,人體細(xì)菌對(duì)人體的作用以及影響很容易被我們所忽視。長(zhǎng)期以來,對(duì)于少數(shù)傳染性細(xì)菌的破壞性影響的研究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而科學(xué)家對(duì)那些“好”的微生物的研究似乎就不那么重視了。
然而,運(yùn)用各種新的檢測(cè)手段,現(xiàn)在科學(xué)家已經(jīng)能夠?qū)ι钤谖覀兩眢w表面和內(nèi)部的微生物進(jìn)行觀察檢測(cè)和分析研究,并且取得了共識(shí):人體內(nèi)的細(xì)菌雖然微小,卻是一個(gè)個(gè)強(qiáng)大的“化學(xué)工廠”,能夠從根本上影響人體的各項(xiàng)機(jī)能。它們?cè)谖覀凅w內(nèi)不是簡(jiǎn)單地、隨機(jī)性地?fù)竦囟樱切纬闪艘粋€(gè)個(gè)有組織的細(xì)菌“社區(qū)”,與我們一起進(jìn)化,并代代傳承。那些生活在人體腸道內(nèi)的數(shù)以百萬億計(jì)的小小微生物,它們將在幾十年時(shí)間里與我們?nèi)梭w共生共存。更重要的是,它們將永不懈怠地行使幫助我們消化和防止感染等職能。可以說,它們是長(zhǎng)期生活在我們身體里的“嘉賓”。
現(xiàn)在,醫(yī)療微生物學(xué)和環(huán)境微生物學(xué)之間的界限正日趨模糊。科學(xué)家認(rèn)識(shí)到,人體就是這些微生物群落的生存環(huán)境,它們被迫適應(yīng)了我們的飲食習(xí)慣和生活方式;反過來也成為我們生存環(huán)境的一部分,我們的身體也在適應(yīng)它們。
此外,隨著人類和微生物之間深刻的相互關(guān)系日趨明顯,宿主和寄生生物體之間的區(qū)別和界限也顯得越來越不那么重要了。2011年6月,在美國(guó)波士頓召開的第108屆微生物學(xué)大會(huì)上,微生物學(xué)家瑪格麗特·麥克福爾·尼蓋指出:人類與微生物共生的研究是一門新興科學(xué),其重大意義在于,人類不是一個(gè)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而是由各種有機(jī)體構(gòu)成的生態(tài)群落。也就是說,我們的身體并不只是為其他生物體提供了一個(gè)可以共生的棲息地,我們也和其他生物體一起,組成一個(gè)整體,共同經(jīng)營(yíng)著一個(gè)不斷進(jìn)化演變的人類-微生物集居地。
我們的身體不斷地與體內(nèi)共生的微生物進(jìn)行著溝通,健康或疾病或許正是我們和微生物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變化的結(jié)果。
人類基因組的30億堿基對(duì)序列圖譜在2000年成功繪制后,被譽(yù)為“人類生命的藍(lán)圖”。然而,不過十年的時(shí)間,大多數(shù)科學(xué)家現(xiàn)在不得不承認(rèn),在我們的基因組里,只有一部分是真正屬于我們自己的。過去,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了多種表觀遺傳現(xiàn)象(如胚胎發(fā)育、基因沉默等)對(duì)遺傳物質(zhì)的最終表達(dá)所起的作用。而如今,在這些影響因素中,還應(yīng)該加上小小的人體微生物。
科學(xué)家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法忽略人體微生物在人類基因庫(kù)中所起的作用,有科學(xué)家甚至將人體稱為“超有機(jī)體”。所謂“超有機(jī)體”,指一群相互依賴并以共同行為構(gòu)成一個(gè)單位的有機(jī)體, 如像群居的昆蟲,其復(fù)雜程度遠(yuǎn)遠(yuǎn)超出單一的基因編碼。“超有機(jī)體”理論與傳統(tǒng)的人體理論有著很大的不同。舉例來說,在生理機(jī)能上,某些人體功能被看作是共生伙伴之間協(xié)調(diào)的結(jié)果,而疾病則被看作是溝通失敗的結(jié)果。
最近有證據(jù)表明,人體的肥胖可能與人體消化道微生物有關(guān)——消化道微生物不只是直接幫助處理食物,還對(duì)能量最終是否以脂肪形式儲(chǔ)存在體內(nèi)產(chǎn)生影響。科學(xué)家發(fā)現(xiàn),在實(shí)驗(yàn)小鼠的消化系統(tǒng)中,體瘦小鼠和體胖小鼠體內(nèi)的各種微生物的比例是不同的,體胖小鼠體內(nèi)的某些微生物似乎更擅長(zhǎng)于從食物中獲取能量,如果將這類微生物轉(zhuǎn)移到體瘦小鼠體內(nèi),它們的體重就會(huì)很快增加。類似的模式在人體研究也發(fā)現(xiàn)了。一項(xiàng)最新研究結(jié)果顯示,胖瘦不同的雙胞胎兄弟,其體內(nèi)的細(xì)菌群落明顯不同。
人們?cè)絹碓角宄卣J(rèn)識(shí)到,我們的身體在不斷地與體內(nèi)的微生物進(jìn)行著溝通,健康或疾病可能正是我們和我們的共生微生物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變化的結(jié)果。科學(xué)家曾猜測(cè),動(dòng)物體與其共生細(xì)菌之間通過分子“語言”進(jìn)行溝通。而現(xiàn)在,有科學(xué)家進(jìn)一步指出,我們與有害或有益細(xì)菌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如何,不在于使用的溝通“語言”不同,而在于“語氣”不同——是爭(zhēng)論的“語氣”,還是友好交談的“語氣”。細(xì)菌產(chǎn)生的一些被稱為“致病因素”或“毒素”的產(chǎn)物不一定就是進(jìn)攻信號(hào),它們有可能只是微生物和宿主之間“對(duì)話”的一部分。
微生物研究的發(fā)展
對(duì)人體微生物群落的研究始于1683年。當(dāng)時(shí),荷蘭博物學(xué)家、顯微鏡發(fā)明者安東尼·范列文虎克在寫給英國(guó)皇家學(xué)會(huì)的一封信中說,他在顯微鏡下觀察自己的牙菌斑時(shí),看到了許多活動(dòng)著的微生物。但是,在接下來的三個(gè)世紀(jì)里,對(duì)人體微生物群落的研究興趣主要限于如何將細(xì)菌從其天然生存環(huán)境中移出來,在實(shí)驗(yàn)室的培養(yǎng)皿中進(jìn)行培養(yǎng)。這或許是當(dāng)時(shí)唯一的觀察和了解細(xì)菌的方法,但卻極大地限制了科學(xué)家對(duì)細(xì)菌真實(shí)生活的了解,因?yàn)樗麄兞私獾降闹皇桥囵B(yǎng)皿中的微生物,而忽略了在真實(shí)生存環(huán)境中微生物與宿主之間產(chǎn)生的高度復(fù)雜和多樣化的共生形式。這種研究方法就好比是將人困在斗室里進(jìn)行研究,而忽略了人的自然生存環(huán)境——城市和社會(huì)。
直到基因測(cè)序技術(shù)問世之后,情況才有所改變。研究人員獲得了對(duì)大量基因迅速測(cè)序的能力,可以從提取的環(huán)境樣本中,對(duì)成千上萬的基因片段進(jìn)行測(cè)序,從中直接獲取關(guān)于微生物的信息,而無需將它們與環(huán)境隔離開來。這類研究顯示,微生物世界之大,完全超乎人們的想象。
如今,環(huán)境微生物學(xué)家使用新的研究手段,開始涉足于一些之前未曾涉足的領(lǐng)域——生命可能存在的一些極端之地(如酸性湖泊、深海熱液口、凍土地帶等),以及人類和其他生物體共生的環(huán)境生態(tài)(從后臼齒、鼻腔到腸道……)。隨著這些研究項(xiàng)目的推出,醫(yī)學(xué)研究和環(huán)境微生物學(xué)領(lǐng)域已經(jīng)漸漸開始融合。
或許有一天,一個(gè)人的體內(nèi)微生物生態(tài)會(huì)成為他(她)的天然識(shí)別標(biāo)簽。正如有科學(xué)家所說:它“是你的身份和身世的簽名”。
人體微生物研究具有一些特別的意義——在我們服用抗生素后,胃部的不適是否是體內(nèi)一場(chǎng)內(nèi)戰(zhàn)開始的信號(hào)?我們往牲畜飼料中加入了大量的抗生素,它們最終去了哪里?這些抗生素是否會(huì)破壞微妙的生態(tài)平衡?在整個(gè)進(jìn)化史上,我們都與微生物生活在一起,而且使用了大量的會(huì)殺死這些微生物的化學(xué)物質(zhì),這是否會(huì)改變我們與它們長(zhǎng)期形成的共同進(jìn)化關(guān)系?……
1683年,荷蘭博物學(xué)家、顯微鏡發(fā)明者安東尼·范列文虎克在顯微鏡下觀察自己的牙菌斑時(shí),發(fā)現(xiàn)了微生物。當(dāng)代微生物學(xué)家的任務(wù)之一,就是區(qū)分哪些微生物是與我們共同進(jìn)化的,哪些只是我們身體中的匆匆“過客”。然而,人體微生物的種類之多令人驚訝,而且因人而異。不同的人體以及人體的不同部位,為細(xì)菌提供了一個(gè)個(gè)多樣化的棲息地,比如營(yíng)養(yǎng)豐富的人體腸道是相對(duì)穩(wěn)定的細(xì)菌“社區(qū)”,而生存環(huán)境較為嚴(yán)酷的皮膚則是細(xì)菌們匆匆來去的“流動(dòng)社區(qū)”。而且,與罕有流動(dòng)的深海棲息環(huán)境不同的是,人體微生物群落還會(huì)不斷受到外部環(huán)境微生物的影響,比如腸道微生物會(huì)與隨同食物一起進(jìn)來的其他微生物產(chǎn)生交集,這些新來者代表著巨大而不可預(yù)知的因素。如此看來,微生物是一種不斷變化的動(dòng)態(tài)生命形式,科學(xué)家很難對(duì)他們所看到的微生物進(jìn)行分類,發(fā)現(xiàn)并界定人類微生物的種類是一項(xiàng)異常艱難的工作。
不過,在人體微生物的個(gè)性化因素使人類與微生物關(guān)系的研究變得相當(dāng)復(fù)雜的同時(shí),也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機(jī)遇。在未來,醫(yī)生或許可以根據(jù)每個(gè)人體內(nèi)特定的微生物生態(tài)環(huán)境來制定出有針對(duì)性的治療方案。屆時(shí),人體的微生物生態(tài)就如一份份遺傳基因檔案,成為每個(gè)人的天然識(shí)別標(biāo)簽。正如有科學(xué)家所說:它“是你的身份和身世的簽名” 。
細(xì)菌往往被認(rèn)為是簡(jiǎn)單低級(jí)的生命體,除了其傳染性外,我們很少去重視它們的存在。現(xiàn)在,科學(xué)家指出,微生物以不同尋常的機(jī)制,在進(jìn)化之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微生物群落中充滿了為群體利益而自甘犧牲的例子,一些細(xì)胞的存在僅僅只是為其他細(xì)胞提供結(jié)構(gòu)支撐或保護(hù)。這種“命運(yùn)的相互交織”值得人類借鑒和考慮,人類是否應(yīng)該向它們學(xué)習(xí),更注重人類社會(huì)的整體發(fā)展,而不是只熱衷于個(gè)人的身份地位和事業(yè)成功?
以硫化氫為食的深海微生物
科學(xué)家于1977年首次發(fā)現(xiàn)了生活在深海熱液口附近的生機(jī)勃勃的生命形式,包括生活在高溫并彌漫著硫化氫氣體環(huán)境中的巨大管狀蠕蟲。科學(xué)家無法解釋這些在極端條件下生存的生命形式。過去,所有的生命都被認(rèn)為只能依靠來自太陽的能量才能生存下去。那么,在遠(yuǎn)離任何光線的海底棲息地,管狀蠕蟲等生物是如何生存的呢?科學(xué)家發(fā)現(xiàn),在管狀蠕蟲的體內(nèi),共生著一些以硫化氫為食的微生物,它們將硫化氫這種“毒藥”變?yōu)槠渌问娇梢越邮艿哪芰俊_@一發(fā)現(xiàn)表明,所有的生命形式都離不開微生物,無論是在深海底,還是在人體腸道內(nèi)。我們?cè)?jīng)忽略了我們身體內(nèi)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員,現(xiàn)在是該拋棄這種一葉障目偏見的時(shí)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