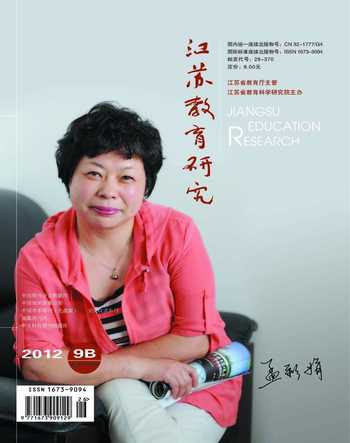牽手智趣數學,兒童需要什么?
智趣數學就好比味美而富有營養的核桃。核桃好吃殼難開,如果直接把整個核桃塞進嘴里啃咬,根本無法品嘗到核桃仁的美味,而且口感之差簡直令人無法忍受。如果教師將數學“成人化”地呈現給孩子,就好比直接把沒有打開的核桃塞進學生嘴里,學生不僅無法體驗到數學內在的“智”與“趣”,還會導致兒童拒數學于千里之外。
波利亞說:“教師講什么不重要,學生想什么比這重要一千倍。”教師有必要研究兒童,滿足其必要的心理需求,投其所需教數學,讓兒童自然而然走進數學大門,欣賞并體驗到數學內在的神奇智趣之處,兒童才有可能悅納并牽手智趣數學。那么,牽手智趣數學,兒童到底需要什么呢?在這方面,筆者做了一些探索。
一、兒童需要小的故事,不需要大的道理
兒童有很強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但兒童有意注意的持續時間是比較短暫的。數學課堂上,教師最頭疼的是總有一部分學生的神情游離在課堂之外,他們對同學的交流、老師的講解充耳不聞。雖然教師一再強調專心聽講的重要性,但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其實,兒童喜歡小的故事,不需要大的道理。數學課堂中,如果借用故事情境的形式呈現教學過程中的一些環節,可以有效吸引兒童的注意力,讓兒童興致勃勃地參與到課堂討論中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不管什么時候,只要教師一說,“下面老師給大家講個小故事”,學生的眼睛就會立即放光,神情立馬專注起來。
比如一年級的“認識鐘表”,為了讓孩子討論鐘面上時針和分針指示時間的方法,我故意說:“下面我給大家講一個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小故事——我經常不小心做壞了事情。有一個星期天,我在家打掃衛生,擦桌子時,一不小心把桌上的鬧鐘碰翻了,小鬧鐘‘哐當一聲掉到了地上。我拿起一看,鐘面上的分針、秒針都摔掉了,只剩下了一根時針。不過,小鬧鐘的心臟沒有摔壞,還能聽到小鬧鐘嘀嗒嘀嗒的轉動聲。這個時候,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如果鐘面上只有一根時針,能不能告訴我們是幾時或者是大約幾時呢?”接著課件先出示只有一根時針的鐘面,讓學生判斷時間。學生注意力集中,參與討論的積極性異常高漲。討論交流中,學生明白了:時針指著幾,就是幾時整;時針走過幾,就是幾時多;時針靠近幾,大約就是幾。
古今中外一個個趣味橫生的數學史料故事、數學趣題故事以及數學家幽默小故事,都是數學寶庫當中的朵朵奇葩,如果將這些有趣的小故事融入單純的數學知識的學習過程中,都能有效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因為學生渴望弄明白故事結果,注意力就會高度集中。另外,有的數學故事還反映了數學知識形成的過程,課堂中融入這樣的數學故事,不僅能激發學生對數學的興趣,還能讓學生加深對相關數學知識的理解,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二、兒童需要游戲活動,不需要枯燥演練
斯賓塞說:“在所發生的一切教育的變革中,最值得人們注意的是,把知識的獲得當成一種快樂的,而不是苦惱的事情。”兒童最快樂的事情莫過于游戲活動。“要是數學學習就像玩游戲那樣,那該多好呀!”這是兒童發自內心的渴望。兒童需要快樂的游戲活動,不需反復演練枯燥的數學習題。
新課程改革后,教材中安排了不少的游戲活動,但不少教師為了節省時間,常把游戲過程刪掉,只把這類題目當成普通的練習題,讓學生一“練”而過。實際上,游戲的過程,正是兒童思維活躍的過程。兒童在游戲活動過程中,能積極地探索與思考,有效理解數學知識并獲得輕松愉悅的學習體驗。
比如一年級教材中有道“10的分與合”的題目,不少教師讓學生看書說一說,或用筆在書中連連線就完了。我在課堂中把10張數字卡片發給一些學有困難的學生,讓學生玩找朋友的游戲。雖然這只是個簡單游戲,但學生玩得不亦樂乎,玩了一輪又一輪,依舊不肯罷休。游戲過程中,還遇到了這樣有趣的小插曲:一位孩子舉著數卡2問:“誰是2的好朋友?”一位孩子舉著數卡7跑上來說:“7是2的好朋友。”一位孩子舉著數卡8跑上來說:“8是2的好朋友。”一見上來兩人,我隨口就問:“誰是2的真朋友?誰是2的假朋友?”全班孩子邊笑邊說:“8是2的真朋友,7是2的假朋友。”舉著數卡8和數卡2的兩位小朋友手拉手成了一對好朋友,舉著數卡7的孩子急著問:“誰是7的好朋友?”“3是7的好朋友!”舉著數卡3的學生邊說邊跑到“7”的身邊,與“7”牽手成朋友。我乘勢追問:“誰是7的真朋友?”孩子們笑著大聲回答:“3是7的真朋友!”孩子們在辨別“真朋友”與“假朋友”的過程中,明晰并有效鞏固了10的分與合。
數學課堂不應該是枯燥演練的代名詞,而應該是數學思維的運動場。一些教學環節不妨設置成鮮活有趣、充滿活力的游戲活動,使教學過程游戲活動化、兒童趣味化,讓學生在活動中玩,在玩中愉悅思考,讓抽象嚴謹的數學變得生動有趣,用“生動”有效演繹“深刻”,學生就會興致勃勃地與智趣數學牽上手。
三、兒童需要具體幫助,不需要簡單指令
兒童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因為先天素質或家庭環境的不同,難免會出現差異。一些數學學習困難的孩子,在數學學習遭遇障礙的時候,需要得到教師具體耐心的幫助,而不是簡單粗暴的指令。
我班上的小周濤在一年級學習認數時怎么也記不住10以內數的分與合,一天放學后,請家長過來交流。家長唉聲嘆氣,說孩子意外早產,先天發育不良,頭腦很笨,雖然天天在家背,也只能記住5以內的分與合,6就分不清了。我數出6枝鉛筆給小周濤,幫她分出1枝放在左邊,她挨個點數后,說:“6可以分成1和5。”我再幫著分一個過來,問:“6可以分成幾和幾?”她一一點數后說:“6可以分成2和4。”就這樣,分一次點數一次,一直分到5和1。我告訴她,就這樣反復分,邊分邊說,就會記住6的分合。她不斷地分、點數、說分的結果,分了若干次后,明顯有了長進,因為她可以不點數,也能直接說出分的結果。又分了若干次,我用書將她每次分后右邊的部分遮蓋住,讓她說出被蓋住的鉛筆數量。開始,她說得很猶豫,經過若干次后,她也能很快說出正確的結果。最后,她終于可以脫離鉛筆,能按分筆的順序全部正確說出6的分合。我告訴她:“每天重點分一個數,6的記住了,分7,7的記住了分8,只要天天在家像剛才這樣邊分邊說,7、8、9、10的分合,很快都能記住的。”以后,周濤在家天天分,一周多點時間,就完全記住了10以內數的分與合。
兒童之所以記不住10以內的分與合,不是沒有花時間去記憶,而是10以內的數感還沒有建立起來。如果教師發現周濤這樣的孩子10以內的分與合記不住,只是簡單地指令她回家背,而沒有具體的幫助,像周濤這樣的孩子是很難記住的。反復指令后,學生還是記不清,久而久之,教師對這樣的學生就會失去信心,認為孩子的智力天生有障礙,數學學困生也就形成了。
四、兒童需要經歷成功,不需要習得無助
20世紀6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塞利格曼用狗做了一項經典實驗,起初把狗關在籠子里給以難受的電擊,狗逃避不了。多次實驗后取消逃避障礙,仍給以電擊,此時狗本可以逃生,卻非但不逃,反而不等電擊出現就先倒在地上,絕望無助地等待痛苦的來臨。這就是“習得性無助”。隨后的很多實驗也證明,這種“習得性無助”在人身上同樣會發生。當一個人發現無論如何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時,他的精神支柱就會瓦解,斗志也隨之喪失,最終會放棄所有努力。
兒童在數學學習過程中,如果一次次把題目做錯,一次次遭遇失敗,也會導致“習得性無助”。這樣的兒童就會認為自己天生愚笨,智力低下,不是學習數學的材料,從而遠離數學,甚至痛恨數學。成功乃成功之父,兒童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經歷成功,而不需要習得無助。
一次教學20以內的退位減法,讓學生思考怎么算出20—9的得數,有的孩子用“破十法”,有的孩子“想加算減”,坐在最后一排很少舉手的鄭志越舉起了小手,因他是數學作業經常需要單獨再輔導的學生,我立即請他起來發言。他說:“我是這樣想的:20—10=10,10+1=11,所以20—9=11。”一年級的孩子能通過比較想到“多減的要加上”,是我沒有想到的。我故意說:“我有點不明白,你說的是什么意思呀?”鄭志越手舞足蹈解釋說:“因為20—10=10,那減9,結果就是11。”一些同學明白過來幫著解釋:“對,因為20減的是9,減10后,結果要加上1,就是11。”我用贊嘆的口氣說:“鄭志越用比較的方法算出了20—9的得數,老師也沒有想到這種方法,鄭志越真是太善于思考了!”大家給了他長時間熱烈的掌聲,課后我又通過“家校通”給他的家人發去了報喜的信息。
鄭志越這一次成功的經歷,得到了老師、同學、家長的高度認可,他那被人承認、被人欣賞的心理需求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大大增強了他的自我認同感,他內心深處積極向上的內驅力好像被充分激發,他像獲得了一種神奇的力量,完全變了樣。此后,他變得自信陽光,愛思考、愛表達。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心目中,他成了善于思考的學生,而不再是糊里糊涂的數學學困生。
兒童是天真爛漫的,數學是抽象嚴謹的。在有些人看來,讓兒童與數學牽手簡直是難于上青天。其實,人人都有數學基因,只要方法得當,每個人都能學好數學。數學家、科普作家基思·德夫林在他的《數學猶聊天——人人都有數學基因》一書中指出:人們生來就有“數的本能”,如同他們具有“語言天賦”一樣。另外,數學也是神奇的,比魔術還有趣,一旦牽上了手,就會入迷,再也不想放手。很多數學家正因為從小就迷戀上數學,才窮其一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研究數學。只要數學教師能把兒童當“兒童”,讀懂兒童的心理需求,順其天性而為,順其所需而教,就能當好“紅娘”,讓天真爛漫的兒童都不討厭抽象嚴謹的數學,讓一部分兒童主動與之傾情牽手,進而享受在研究智趣數學的過程之中。
(吳汝萍,金湖縣實驗小學,21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