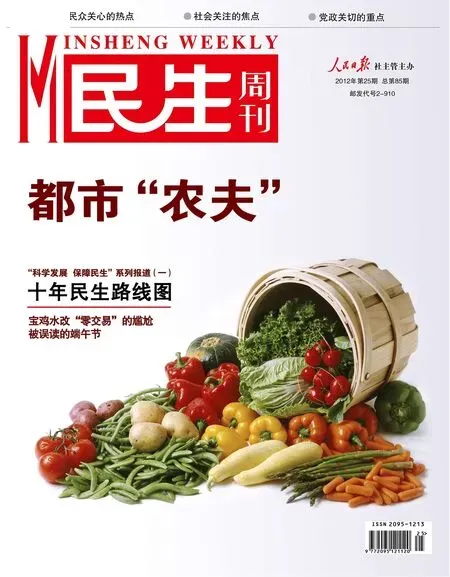新農夫引“農業回歸”
熊帥
“不打農藥、不施化肥”,都市農民與屋頂農業踐行者正試圖通過傳統的耕種方式,掀起一場“農業回歸”運動。
在過去4年里,關于食品安全的討論從未停止過,也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舌尖上的安全與健康。
在遠離城市中心、靠近鄉鎮村落的地方,涌現出一批“不打農藥、不施化肥”的都市農民與屋頂農業踐行者。他們正在試圖通過傳統的耕種方式,恢復農業的原始狀態,掀起一場“農業回歸”運動。
豆漿老板徐明
清晨,經過一晚暴風驟雨洗滌的村莊,萬籟俱寂。徐明從枕頭底下摸出手機,看了一下時間,指針剛好指向4點。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煮黃豆。”徐明用特制的木棒,不斷攪動大鐵鍋中的黃豆,同時撈出越來越厚的黃豆泡沫。大約一小時后,將柴火抽出,爐灶里的火勢慢慢降了下來。
長期以來,徐明家的豆漿因為純天然、綠色,一直深受消費者喜愛。在北京東北部平谷區的岳各莊、北崗子一帶,提起徐明做的豆漿,幾乎無人不曉。目前,徐明的固定客戶超過百家,每天銷售豆漿200—500杯。
做豆漿很辛苦,程序也很復雜。選料上,徐明用的是產自黑龍江黑河地區的非轉基因大豆;泡制上,從泡豆到熬煮起碼超過8個小時,需通宵趕制;磨制上,使用的是傳統的大理石石磨。每一杯豆漿都力圖回歸原始的制作方式,純手工打磨。
為了增加豆漿的美味,在磨豆之前,徐明還會在黃豆中添加一些來自貴州惠水的紫糯米,據說這樣能夠借助稻米的清香和糯米的粘質,進一步增加豆漿的粘稠感,使豆漿不用添加除泡劑和增稠劑,就有甜香、綿密的口感。
早晨6點,200多份豆漿已經陸續灌瓶擺好。徐明和兒子一起,將昨晚整理好的黃瓜、西紅柿、青椒、茄子等蔬菜裝運上車,開始了一天的送貨旅途。
三年來,這是徐明每天都要重復的工作:上午磨豆漿、送菜;下午整理菜園子、豬圈;晚上采摘,準備第二天需要配送的蔬菜。這樣的經營,讓徐明每個月的盈虧基本平衡。
誰也無法想象,眼前這個穿著灰色T恤、腳踩廉價拖鞋的中年農夫,之前是一家世界500強企業的高級主管。
徐明出生在河北保定農村,畢業后,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城市擁有了穩定的工作和生活。改變發生在2006年。那一年,徐明放棄了年薪不菲的工作,在北京近郊平谷租了10畝地,辦起了自己的農場。這個近似瘋狂的行為,被他自己解釋為“出于對農產品新鮮度和安全性的憂心”。
當時,在西方和日韓等地,社區支持農業(CSA)已經流行了近半個世紀;在中國,則剛剛起步。作為國內最早一批綠色、有機農業的踐行者,徐明的創業之路幾乎是摸著石頭過河,充滿艱辛。
“第一年養雞就虧了5萬元。”2007年春季,徐明買了500只小雞,在離農場最近的山坡上進行天然飼養,不使用飼料。每天,這些散養的小雞在山野間啄食蚯蚓、青草。
徐明沒有想到,還沒到秋季母雞下蛋時節,突然爆發了雞瘟,500只雞“陣亡”了1/3之多,投資損失近半。等到母雞可以下蛋時,很多雞又因為營養不足而長不大,以至當時能下蛋的雞只有80多只,且多數雞蛋體積小,重量很輕。
當徐明把這批雞蛋運到菜市場,以10元/斤的價格對外銷售時,消費者并不買單。有人認為價格過高,普通工薪家庭消費不起;而更多的人對于有機雞蛋的說法產生質疑。最后,徐明只好找到熟識的親戚朋友,低價賣出甚至免費贈送,才“解決”了這批雞蛋。
在這之后,徐明種過蘑菇,賣過土豆,在過街天橋兜售過圓白菜……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傾注心血最多的豆漿,最終成為農場最為持久的產品。
碩士農民馬建偉
最近,“農場主”馬建偉收到一位顧客的投訴:小白菜長得老,嚼起來費勁;菜的品種少,每天都是黃瓜、西紅柿,都吃煩了。好吃的豆角、青椒是不是一直壓著不送?
通過溝通,馬建偉了解到這位顧客的老家在江西,當地人習慣吃20公分長的鮮嫩小白菜,馬建偉送來的30公分長的小白菜明顯已經老了。在江西,一般從4月開始,餐桌上就有了新鮮的四季豆、青椒等蔬菜;而在北京,到了5月份還吃不上四季豆。
馬建偉趕忙向顧客解釋,北方春天的氣溫沒有南方回升快,一般到5月中旬,四季豆、青椒才成熟,且自己不用溫室大棚,所以現在吃不到。“在強調綠色、有機的生態農業中,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馬建偉保證,將來送菜一定考慮顧客的飲食習慣,盡量滿足顧客要求。
“在當農民之前,從未想到會有這些情況。”馬建偉感嘆,搞生態、做有機、當農民,遠比自己當年考北大來得辛苦。
2007年,還在北京大學化學專業讀研究生的馬建偉,第一次從媒體上認識了生態有機農業。那段時間,媒體每天都在報道河北農民安金磊的事跡。對于安金磊“順應自然、合其天性”的農作法,馬建偉很感興趣。“特別是不用除草劑、化肥、農藥的生態有機農業實踐,這是解決農產品安全問題的有效方式之一。”
“當時我就和安金磊聯系,但很快發現這樣解決不了問題。”馬建偉告訴記者,雖然自己出生于農村,但對農業一竅不通。安金磊講的生態農業,及他對土地和作物的感情,馬建偉聽的是一知半解。“還不如自己多看看書,先充實一下知識。”
直到2011年,在朋友的引薦下,馬建偉才在北京市海淀區的上莊鎮租了4個大棚,種植自己的有機蔬菜,并承諾不使用任何農藥、化肥、除草劑和激素。
“每月五百塊,吃上放心菜”,是馬建偉農場的對外宣傳口號。目前,農場主要配送黃瓜、西紅柿、茄子、水蘿卜、圓白菜、土豆、豆角等20多種時令菜;每周一、周四,為東部城區的顧客送貨;每周三、周六送往西部城區。
據馬建偉介紹,一開始農場只有4、5個客戶,還都是幾個認識的朋友,所以自己一直擔心農產品的銷售問題。隨著人們對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主動找到馬建偉,紛紛表示愿意訂購有機蔬菜。不到半年,馬建偉手頭的客戶已經擴展到了上百人。
今年,農場實現了轉虧為盈,股東們每個月也都能拿到農場帶來的利潤分成。對未來有機農場的發展,馬建偉表示,“還是充滿信心的。”
打假斗士孫德偉
地里正待采摘的黃瓜,受春季大風影響,一夜之間都蔫了。孫德偉雇傭的農民跑過來問他,要不要打一些激素,讓黃瓜外表看著光鮮些,保證銷售。
“不打!我們有機農場不打激素、農藥和化肥。”孫德偉堅決地說。
農民不理解:不打激素,黃瓜肯定產量低;樣子蔫,一定賣不上錢。“幾畝地的黃瓜就這樣打了水漂,多可惜。”
這樣的情景幾乎每天都會在孫德偉的農莊里發生,但孫德偉明白,即使虧了,也不能毀了翡翠灣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有機農業系統。
“做有機農場4年多了,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完全說服農民擺脫化肥和農藥。”這個網上出了名的有機農業打假斗士,面對現實卻也難掩失落。
從2009年創辦翡翠灣永續農場開始,孫德偉就意識到,做有機農業,隨時都要面臨來自化學農業的巨大經濟誘惑。
孫德偉舉例說,同樣為一畝菜地進行除蟲,普通農場中,農民只需要選擇幾種特定的農藥,在田間走幾趟、用噴霧劑灑兩下,不到一小時就能將菜地里的害蟲消滅干凈,既簡單輕松,又節省成本。
有機農場中,為了踐行不打農藥、不使用化肥的原則,孫德偉每天需多花費70元的人力成本。兩個農民低頭彎腰,需兩天時間才能完成上述工作。即使這樣,最后長出的蔬菜也往往不好看,蟲眼多,消費者不喜歡。
而在終端市場,使用過農藥的蔬菜與有機蔬菜外觀上并沒有明顯區別。商家只要用上印著“有機”字樣的包裝,就能賣出有機菜的價格。
于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僅自家農民,就連孫德偉的一些同行也認為,既然打農藥也能賣出有機蔬菜,為何不試試,反正沒人管。
“沒人管,那我管。”2009年,孫德偉用“鐵鳥狼軍”的網名,開始了有機農業體系的網絡打假之路。
在孫德偉提供的打假名單里,沱沱工社、小毛驢市民農園、樂活村王申福等一批知名農場都赫然在列。其糧食的農作方法,蔬菜的種植方式,牲畜的喂養飼料等,都遭到過孫德偉的質疑。
孫德偉表示,面對食品安全問題,老百姓都把有機農業當做“救命稻草”,卻不知某種意義上的食品安全,由于巨大的利益誘惑,早已偏離了有機農產品安全、健康的本質。
“2010年‘開花大蔥事件中,沒有一個農場主站出來告訴消費者,開花的大蔥營養價值低。”孫德偉認為,目前中國的有機農業體系還處在原始成長階段,從業人員魚龍混雜,似乎人人都覺得自己可以當好農民。而一些農場主也對消費者進行某種信息誤導或欺騙。長期下去,如沒有行業監督,“本來挺好的有機生態農業,漸漸也會成為新一輪食品安全問題的主角。”
“我不想毀了有機農業,打假只是希望這個行業更加透明一些。”孫德偉說,2010年冬天,翡翠灣出現了大批客戶退訂的現象,自己的打假行動,不想也對自己造成了負面影響。但是孫德偉仍然堅持,打假對于整個行業是有積極和正面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