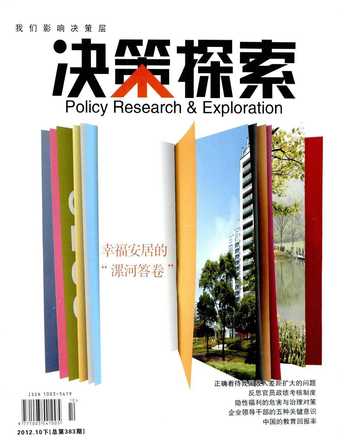論古文字教學(xué)中對(duì)原材料的篩選和使用
王建軍
古文字教學(xué)中所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指出土與傳世的古文字材料。如何正確而有效地使用這些材料,是教學(xué)過(guò)程中所要把握的關(guān)鍵問(wèn)題。目前,學(xué)術(shù)界對(duì)古文字的考釋水平已達(dá)到較高的層次,但古文字的教學(xué)內(nèi)容對(duì)原材料的使用似乎還嫌不夠,這就導(dǎo)致現(xiàn)今的古文字教學(xué)與原材料的實(shí)際研究水平之間還存在一定差距。作為一位專業(yè)教學(xué)工作者,筆者試就這些問(wèn)題談?wù)剛€(gè)人的看法。
第一,重視對(duì)字形的基礎(chǔ)整理,是有效使用古文字原材料的前提與條件。整理古文字字形,首先面對(duì)的是一大宗古文字原材料:既有殷墟出土的13萬(wàn)余片甲骨文 ,又有大量的青銅器銘文、陶文、玉石文、古璽文、古幣文等,還有傳世的漢魏石經(jīng)文字、汲冢竹書等。這些古文字原材料不僅數(shù)量豐富,而且門類齊全。
要想從中選擇較為重要的部分作為課堂教學(xué)的內(nèi)容,就必須加強(qiáng)基礎(chǔ)整理工作。這是提升教學(xué)質(zhì)量與教學(xué)效果的重要一步。分析整理古文字原材料,應(yīng)從單字的構(gòu)形入手。這就要求我們,首先必須搞清楚古老的文字并不是單純由圖畫演變而來(lái),其符號(hào)造型也不全是由意象成分所決定,而是早在殷商時(shí)代就已形成了一套高度發(fā)達(dá)的符號(hào)系統(tǒng) 。此系統(tǒng)存在著古文字具有規(guī)范意義的基本部件、基本筆畫、構(gòu)形方式及其誘發(fā)分化與演化的多種潛在規(guī)律。因此,熟悉、釋讀古文字的基本前提就要堅(jiān)持從嚴(yán)格的字形整理與分析做起。整理工作盡可能做到全面而系統(tǒng),分析與描述也不能生搬“六書”的條例和傳統(tǒng)字說(shuō)框框,而是要客觀、慎重地梳理每個(gè)字形,從而揭示出它們演化的信息以及所貯存的文化內(nèi)涵。以甲骨文為例,2003年,我們?cè)馕毡娂抑L(zhǎng),并以《甲骨文可釋字形》為題,整理并臨摹了1429個(gè)字頭,此表按音序排列,附以著錄號(hào)與分期信息等。2006年,《殷墟甲骨文的字形特征及類型劃分》一文,對(duì)以上字表收集的部分特征字,利用計(jì)算機(jī)進(jìn)行剪切、存儲(chǔ)原篆字形,又重新整理出一套《殷墟甲骨文各組類特征字形表》,而且對(duì)每個(gè)特征字的構(gòu)形都做了解析與描述,并附以學(xué)術(shù)上比較前沿的組類劃分信息。然而我們也看到,前者整理的單字屬摹釋字形,這就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誤摹、誤釋等一些不應(yīng)有的失誤,而后者整理的單字都是原篆字形。應(yīng)該說(shuō),這兩本小冊(cè)子,對(duì)此后的古文字教學(xué)確實(shí)起到了有效的改進(jìn)與提升作用 。
第二,加強(qiáng)對(duì)原材料及相關(guān)研究成果的總結(jié)歸納與充分吸收,這對(duì)古文字教學(xué)內(nèi)容的深化具有重要意義。強(qiáng)化對(duì)古文字原材料及相關(guān)研究成果的總結(jié)歸納與充分吸收,旨在深入探討辭例與文字之間的有機(jī)聯(lián)系,從而達(dá)到深化古文字教學(xué)內(nèi)容的目的。
選擇與使用古文字原材料,在這方面不是需要盲目的膽識(shí),而是需要有素養(yǎng)的訓(xùn)練。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深入到原材料及其相關(guān)的研究之中,絕不能淺嘗輒止。以整理柞伯簋銘文作為教學(xué)內(nèi)容為例,我們?cè)鴮?duì)這件青銅器的相關(guān)材料進(jìn)行了廣泛收集。此器1993年在平頂山市薛莊鄉(xiāng)(現(xiàn)名滍陽(yáng)鎮(zhèn))滍陽(yáng)嶺應(yīng)國(guó)墓地(M242)發(fā)掘出土。據(jù)發(fā)掘者考證,該器銘文中的“柞”應(yīng)指文獻(xiàn)中的胙國(guó),其地應(yīng)當(dāng)在今河南延津一帶。柞伯簋本屬胙國(guó)銅器,卻陪葬在應(yīng)國(guó)墓地。可見(jiàn),胙、應(yīng)兩國(guó)同為姬姓國(guó)。由此他們進(jìn)一步推論,西周初期兩國(guó)均擔(dān)負(fù)著屏周重任,故彼此關(guān)系親密,所以,此簋或許就是柞伯當(dāng)年饋贈(zèng)給該墓墓主的一件禮品 。這一結(jié)論富有啟發(fā)意義。此后,李學(xué)勤先生對(duì)該銘也做了考釋,并逐字逐句分析了銘文的內(nèi)容,還歸納了全銘大意:在八月庚申這一天,周王在都城宗周舉行大射典禮。王命南宮率領(lǐng)朝中各位卿大夫、士,命師魯父率領(lǐng)小臣仆人。王懸賞十塊餅金,對(duì)柞伯說(shuō):“小臣已經(jīng)準(zhǔn)備好扳指,你如能射中,就取走餅金。”柞伯十次舉弓,沒(méi)有一箭脫靶,于是,王把十塊餅金給了柞伯,另外又加賞一套柷吾樂(lè)器給他。柞伯因此鑄器祭祀其父周公。很顯然,李先生的考釋以及所得出的結(jié)論是正確的。1999年陳劍先生又發(fā)表了《柞伯簋銘文補(bǔ)釋》一文 ,至此銘文內(nèi)容已經(jīng)基本弄清。因此,系統(tǒng)整理此銘的原材料,并合理吸收相關(guān)的研究成果,從而有效地推動(dòng)了古文字教學(xué)質(zhì)量與教學(xué)效果的顯著提高。
第三,古文字學(xué)本身是一門交叉性很強(qiáng)的實(shí)用學(xué)科。由于它的邊緣性,這也使得該學(xué)科有著較大的教學(xué)難度,有時(shí)僅憑興趣和發(fā)憤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科學(xué)研討古文字教學(xué)內(nèi)容,離不開(kāi)對(duì)原材料的微觀考察與宏觀駕馭,至少要站在考古(出土情況)、歷史(含文獻(xiàn)典籍)和語(yǔ)言文字(形、音、義及其所在環(huán)境)三大學(xué)科板塊之間。
目前,古文字教學(xué)的改革與發(fā)展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考古學(xué),因?yàn)楣盼淖值陌l(fā)現(xiàn)與研究總是離不開(kāi)考古材料及其背景,這其中包括我們對(duì)文字探源的有關(guān)出土資料。早在20世紀(jì)20年代后期,田野考古就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遠(yuǎn)古陶器符號(hào),此后,在許多重要的考古學(xué)文化內(nèi)涵中均有重要的發(fā)現(xiàn),可以說(shuō)遠(yuǎn)古時(shí)代的刻畫符號(hào)遍布祖國(guó)各地,它們共同為漢字的探源提供了新的證據(jù)。此外,在判斷古文字材料的性質(zhì)和年代等問(wèn)題上,考古學(xué)的層位學(xué)、類型學(xué)等方法是很有力的手段。譬如,從20世紀(jì)40年代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熱烈討論的“文武丁卜辭”的時(shí)代問(wèn)題,其解決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出土坑位和地層的分析。
另外,語(yǔ)言學(xué)的研究對(duì)古文字原材料的解讀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近些年,學(xué)術(shù)界對(duì)語(yǔ)言學(xué)的研究已有較大的進(jìn)展,語(yǔ)言學(xué)的一些普遍原理,尤其是關(guān)于古代語(yǔ)言文字研究的成果,都可移用于古文字的研究與教學(xué)之中。仍以甲骨文為例,甲骨卜辭是殷商時(shí)期的書面語(yǔ)言,就其語(yǔ)法而言,它具有一定的民族特點(diǎn)和相對(duì)的穩(wěn)定性。研究表明,語(yǔ)詞的構(gòu)成與變化,直接影響著組成卜辭語(yǔ)言的詞匯或詞組的構(gòu)成與變化。大多數(shù)卜辭語(yǔ)序是比較規(guī)范的,這與后代的基本一致。但也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就是正常語(yǔ)序中有時(shí)出現(xiàn)“移位”或“割裂”的現(xiàn)象。除此之外,卜辭的詞性仍可分為實(shí)詞與虛詞兩部分,對(duì)于實(shí)詞,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較多,而在虛詞的整理與研究方面卻存在諸多薄弱環(huán)節(jié),這對(duì)古文字的教學(xué)非常不利。
2001年,我們對(duì)卜辭中所見(jiàn)的“以”字進(jìn)行了初步探討。認(rèn)為 “以”字本來(lái)就是一個(gè)動(dòng)詞,從早期的構(gòu)形特征來(lái)看,“以”字的主體結(jié)構(gòu)是一個(gè)側(cè)立的人形,在手臂下部勾勒有一個(gè)圓團(tuán),像手執(zhí)物狀,甲骨文中的“以”字表“貢納”,“進(jìn)獻(xiàn)”之意,也表較抽象的行為動(dòng)作,相當(dāng)于“用”“做”,后來(lái),“以”多充當(dāng)介詞或連詞使用 。之后,又撰文發(fā)表了對(duì)“于”字的看法。認(rèn)為古文“于”字產(chǎn)生的時(shí)代較早 ,而且其構(gòu)形發(fā)展演變的軌跡十分明晰。“于”字在商周秦漢時(shí)期出現(xiàn)了幾種較為典型的寫法,通過(guò)整理與比較 ,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卜辭中都使用了已經(jīng)省化的字形。到了周秦時(shí)期,為了美化字形 ,習(xí)慣于把省化的字形“于”字的下部豎畫寫得婉轉(zhuǎn)屈曲。不過(guò),這個(gè)字形,在經(jīng)過(guò)漢隸之后,沒(méi)有再發(fā)生大的變化。
總之,從以上 “以”、“于” 的構(gòu)形源流來(lái)看,在漢字的發(fā)展演變過(guò)程中,具有一定的規(guī)律性 。正是基于對(duì)這一規(guī)律的充分認(rèn)識(shí),才使得我們?cè)诮虒W(xué)過(guò)程中能夠認(rèn)真分析今天所使用的漢字,其中有不少是割裂、省變或改造早期的象形字而變化發(fā)展過(guò)來(lái)的。
在傳世文獻(xiàn)方面,漢初新發(fā)現(xiàn)的古文經(jīng)曾一度推進(jìn)了小學(xué)的發(fā)達(dá)和《說(shuō)文》的問(wèn)世,現(xiàn)代不斷增多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及其考古學(xué)成果也必將會(huì)促進(jìn)古文字學(xué)科體系的日臻成熟。如今全方位的科學(xué)研究手段(包括古漢字信息處理技術(shù)的利用和開(kāi)發(fā)),給古文字學(xué)者的素質(zhì)提出了更高的標(biāo)準(zhǔn),這當(dāng)然對(duì)我們今后的教學(xué)與研究工作,也設(shè)定了更高的境界。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