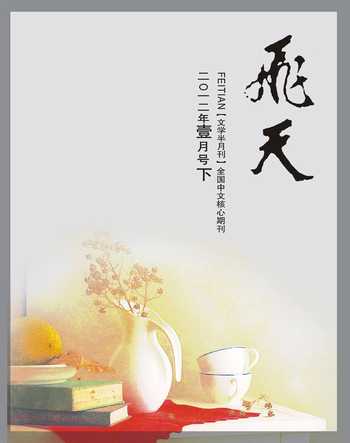新歷史主義視域下的《等待野蠻人》
南非小說家、散文家J.M.庫切自200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就備受學界關注。當前,國內外研究庫切,主要關注的還是他所創(chuàng)作的小說,視角涉及作品主題、敘事手法、文體風格、藝術風格及作品所體現(xiàn)出的存在主義思想、戀母情節(jié)、生態(tài)觀、作家的道德困境等。然而,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從新歷史主義視角出發(fā),將關注點放在庫切作為小說家其創(chuàng)作如何受到南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抑制,作家如何抗衡、甚至顛覆主流意識形態(tài)上的批評文章屈指可數(shù)。筆者選擇庫切創(chuàng)作的第三部、即讓他獲得1980年南非最高文學獎CNA獎的小說《等待野蠻人》,擬采用新歷史主義文論對該作品進行全方位透視,運用該文論的核心概念“顛覆”與“遏制”來分析庫切如何通過其獨特的再現(xiàn)酷刑手法來抗衡當時南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酷刑書寫的抑制。
在新歷史主義者看來,作家的個人意志與他所處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之間具有顛覆與遏制的關系。格林布拉特指出,“作家人格力量與意識形態(tài)權力之間的非一致傾向,即特定時代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都并非必然成為作家和人們實際生存方式中的主要形式”(王岳川,:1999:167)。在作家的人格力量與意識形態(tài)權力之間存在著非一致性傾向,即特定的時代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并非都必然成為作家和人們實際生存中的主要方式。盡管整個權力話語體現(xiàn)規(guī)定了個體權力的行為方向,但規(guī)約強制的話語與人們尤其是作家內在自我不會完全吻合,有時甚至會在統(tǒng)治權力話語規(guī)范與人們行為模式的縫隙中存在徹底的反叛和挑戰(zhàn)。格林布拉特將這種反叛和挑戰(zhàn)稱之為“顛覆”。與此同時,格林布拉特還指出,這種“顛覆”的力量被控制在許可的范圍之內,使之無法取得實質性效果,他將這種控制力量稱之為“抑制”(王岳川,:1999:388))。庫切的小說《等待野蠻人》通過對老行政長官受刑過程的獨特再現(xiàn)手法,打破了當時南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諸如酷刑書寫等邊緣話語的抑制,為被壓抑、被剝奪了的弱勢一方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在《等待野蠻人》這本小說中,庫切把自己關注的焦點轉向一直籠罩南非政治生活的議題,即酷刑問題。小說雖然以寓言的形式出現(xiàn),但它事實上是對當時南非現(xiàn)實情況的影射。自從1948年南非國大黨執(zhí)政以來,一直有關于政府對政治犯人實施暴行與酷刑的指控。1976年6月,南非“黑人意識”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史蒂夫·比科(Stephen Biko)被國大黨逮捕后不到一個月飽受酷刑死于獄中,由此引發(fā)了公眾抗議的疾呼。庫切在1986年的長篇評論《進入黑屋:小說家與南非》中指出,當時南非政府以法律明文禁止媒體以任何形式對監(jiān)獄進行刻畫,更是通過各種審查制度對各種出版物進行監(jiān)察,以抑制不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所接納的邊緣話語。然而,當局的高壓政策無法阻止作家們挑戰(zhàn)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嘗試,而監(jiān)獄、刑室作為禁區(qū)比起其他任何場景更能激發(fā)作家創(chuàng)作的欲望。“顯然因為他站在黑色的門外,想進入那黑屋卻不能,他是個小說家,他必須去想象在門的那一邊發(fā)生了什么……恰恰是他不能進入的那間黑屋所產生的張力令那屋子成了他所有想象的源泉──藝術的子宮。”(Coetzee,,1992: 363)因此,對酷刑問題的討論充斥著當時南非各種媒體話語,不少作家創(chuàng)作了關于酷刑的文本,其中較著名的有西弗·塞巴拉(Sipho Sepamla)的《乘風破浪》。然而,是否對書寫酷刑就達到挑戰(zhàn)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呢?庫切在《進入黑屋:小說家與南非》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那黑暗、禁忌的房間本身成了小說創(chuàng)作的想象力之源泉,政府通過制造這一污穢之地并使之神秘化,從而為再現(xiàn)監(jiān)獄及酷刑這類小說創(chuàng)作設定了先決條件……作家若將它描繪為充滿神秘、惹人遐想之地,則無疑成了政府的同謀。所以對作家而言,更深層的問題是如何不掉進政府設給作家的陷阱,用自己的方式再現(xiàn)酷刑。”(Coetzee,1992: 364)
小說發(fā)表時值輿論對南非政府對待犯人方式的巨大爭議時期,文本中不乏對當時南非新近發(fā)生事件的影射。例如在小說中當描敘國防部時,用的術語就和當時人們用來描述南非國防部警察的行話很相似:喬爾上校在“緊急戒備狀態(tài)下”被派來;他已經指定了“審判的程序”;犯人們必須被“隔離”起來。當?shù)谝粋€被喬爾上校關押并用刑的犯人神秘死亡時,喬爾對其死亡給老行政長官提供的報告讓人馬上聯(lián)想到了南非政府對南非“黑人意識”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史蒂夫·比科死亡原因的解釋,“在審訊的過程中,囚犯的供詞顯然漏洞百出。這些漏洞百出的供詞被揭穿后,囚犯變得狂怒起來并且攻擊進行案件調查的長官。接著在發(fā)生扭打的過程中,囚犯重重地撞在了墻上。經搶救無效死亡。”(J.M.庫切,2004:8)在上述虛飾的言辭中,“犯人”作為主動語態(tài)的主語,被描述為唯一主動的施動者,動作的實施人,從而掩飾了審訊者、施刑者的行為和動作,將其責任模糊化。而當老行政長官去檢查犯人的尸體時,他發(fā)現(xiàn)的犯人“壓迫的嘴唇癟了進去,牙齒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邊,另一只眼眶成了一只血洞。”(J.M.庫切,2004:9)身體的證詞駁倒了官方出示的證詞。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既沒有大力渲染黑色暴力,用浮華的辭藻刻畫用刑的場面及犯人受刑的痛不欲生;也沒有對暴力行徑視而不見,避免直接刻畫暴力和酷刑,而是采取了獨特的再現(xiàn)手法。對受刑過程冷峻、克制的描寫使庫切避免成為國家機器的同謀,粉碎了政府試圖通過將監(jiān)獄和刑室渲染成充滿暴力及血腥的神秘之地從而震懾人民的意圖。
除此之外,庫切還對作家進行酷刑書寫本身進行了批判性的思考,提出了作家的酷刑書寫能否真實再現(xiàn)施刑者和受刑者的心里及其體驗的問題,因為“事實是,刑室是人類極端經歷發(fā)生的場所,除了施刑者和受刑者之外,無人能夠體驗。”(Coetzee, 1992:363)對這一問題的思考表現(xiàn)在小說通過隱喻的手法對作家是能否完全獲得受害者受刑真相進行討論。老行政長官將受刑至殘的蠻族女孩帶回家后,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幾乎都圍繞著如何獲得女孩受刑的真相上。先是檢查女孩受刑至殘的腳,然后是被弄瞎的雙眼。在檢查的過程當中不斷詢問女孩受刑的過程。“他們干了什么?”(J.M.庫切,2004:39)“他們對你做了什么?……你為什么不告訴我?”(J.M.庫切,2004:42)而女孩對于他的詢問,不是搖頭就是沉默。無論他如何努力,老行政長官對酷刑真相的探索都以失敗告終。
從新歷史主義視角解讀庫切的小說《等待野蠻人》,我們可以看到在南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抑制作家話語權的情況下,庫切通過其獨特的酷刑書寫方式為受刑者等邊緣人發(fā)聲,在挑戰(zhàn)主流話語權的同時不淪為國家機器的同謀,在提醒讀者對任何形式的文本再現(xiàn)進行批判性思考的同時使官方所謂“受刑者死亡真相”的報告不攻自破。由此,我們可以重新對歷史、文本、作家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辨證思考。
注:本文為廣西師范大學2011年度校級青年科研基金項目“新歷史主義視域下庫切小說反歷史書寫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 Coetzee, J. M.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Weber, Samuel. Violence, Identi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J.M.庫切著,文敏譯:《等待野蠻人》,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
[4]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作者簡介:蔡云,廣西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