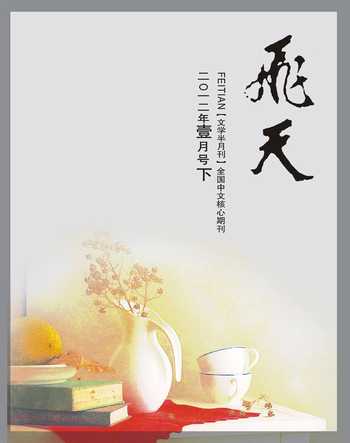試析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情節淡化特征
情節淡化是曼斯菲爾德作品中的一個重要現代主義特征。對于短篇小說的情節,傳統觀點認為短篇小說的情節由主人公行為構成,同時又認為人物同周圍的人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聯系與行為構成小說情節。在曼斯菲爾德的作品中,讀者看不到脫離日常生活的情節,相反,她的小說更像生活畫面,其小說中的情節不過是為了表現人物精神世界的依托。情節淡化使她的作品具有散文的隨意性,詩歌的空靈感和寓言的哲理性。
作品《在海灣》由12個部份組成,而其間的每一個部份都可以算得上是一個生活畫面,這12個部份組合在一起,看起來似乎是沒有什么組合原則,但卻表現出來的是真實的生活。
作品的結局部份也全然不再同于以往傳統短篇小說那樣,非得給讀者一個定論或一個說法不可,這樣的結局不像是一個“結局”,因為,生活根本就沒有結局,作者給予讀者的敘述已然結束,可是,作者所敘述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生活,還在其紙筆之外繼續著。
對于那些讀慣了傳統短篇小說的舊時代的讀者而言,在閱讀這部小說時,大概會因為找不到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應當出現其間的情節而感到“不知所云”。小說由12個部份組成,但這12個部份中的各個部份也無非是將生活的某一片斷或場景呈現出來而沒有傳統小說中所有的離奇事件:(1)海灣清晨的種種景象;(2)男主人斯坦利的晨泳;(3)全家人熱鬧吵嚷的早餐場景;(4)孩子們在海灣游戲;(5)人們在海灣的場景;(6)母親琳達在花園的浮想;(7)外祖母和小孫女的午休與對話;(8)女仆的下午茶;(9)下午茶后孩子們的游戲;(10)母親琳達在花園中同鄰人的對話;(11)斯坦利與琳達的黃昏;(12)小姨貝莉爾的夜晚。
這就是整個小說的12個部分,12個部份色彩各異,有時明快,充滿著天真的美與激情,如第4個部份;有的則緩和平淡,生活在如浮云般飄蕩無定的人的思緒面前停滯不前,如第6部份;有的呈現生活中的浪漫一刻,如第5部份;有的則呈現生活中平淡的一瞬,如第11部份;有的極力渲染親情的溫馨,如第7部份;有的則充滿著淡淡的化不開的憂傷,如第12部份。這色彩各異的12副畫面組成了這則意在表現生活本來面目的小說,展現了一個新西蘭中產階級一天中的生活,充滿著平實樸素的藝術美感。讀來如一則散文那般隨意、真實。
《在海灣》正表明了曼斯菲爾德的文學觀點:文學不是憑空捏造而是出自內心的真情實感,唯其如此,才能以平淡無常的生活場景與事件成就出優秀作品。情節淡化是20世紀文學一大特點,更注重情感情緒而不受理智支配是此時期作品共有特點。《在海灣》事件情節與行為情節淡化;人物心理流程得以強化,曼斯菲爾德從情節著手,體現20世紀小說重要傾向:作家由人物行為轉向人物心理,行為再也不是揭示人物心理與個性的唯一手段與途徑,行為是簡單的,一目了然的,是表象,不是本質。
曼斯菲爾德部分情節淡化小說類似20世紀前半葉出現在西方文壇上的“意圖小說”(planned stories),又稱為“意境小說”:情節淡化近無;作者無意刻劃人物,側重表現意念和境界;情節、人物退居次要地位,變成表現特定意念境界的“客觀對應物”。此類小說近于抒情詩或散文詩,有節奏旋律,有往復循環的意象,有多層次的意義比較隱晦的象征和隱喻。意識的頓悟(epiphany)取代情節發展的高潮,初似散亂的光點忽然聚集一處,意義豁然。喬伊斯,勞倫斯和伍爾芙的一些小說都具有意境小說的特點。當代美國小說家如凱瑟琳·安·波特等也寫過類似作品。曼斯菲爾德的作品同樣具有意境小說的特點,某些作品表現深遠復雜的意境,后期作品《蒂勒爾街的春天》由互不連貫的場景組成;這些場景周期性重復,于重復有變化,但主旋律不變,由此構成意境:碧空如洗的早晨,緊緊關閉的百葉窗,搖籃中熟睡的嬰兒,引吭高歌的金絲雀,招搖過市的馬拉貨車,進進出出的面包店小伙計,象個碩大貝殼一樣的面包筐,夜里下過雨的街,路面的積水,干燥的人行道。……這些場景周而復始,構成意境——生命的意義在于去生活,去盡心盡力地融入生活,最能體現生命激情的莫過于春天這樣一個美好的季節,整部小說沒有刻意而為的情節,但卻是對于春天的最為真實也最為樸實的一個呈現。
顯然,曼斯菲爾德放棄以往作家以厚重生活事件所支持的寫實小說表達方式,在輕淡哀婉而呈片斷狀的敘述中營造現實性與非現實性相混雜的境界。每一段寫作似乎都與主題無關,但若刪除則整部作品就沒有任何魅力可言,以《在海灣》中第6部分和第10部分來看,即少婦琳達獨自在花園里的片斷,以散文筆法來敘述琳達浮般的心緒。
這一完全散文化筆法與作品的情節淡化一致,風清云淡間是脫離塵世束縛的美。琳達獨自在園中的敘述構成意境,在整部作品中不處于陪襯地位,相反作品中人物活動與相互關系為琳達的這一段敘述起到陪襯作用。每一瓣花的開落都融入琳達的心緒,虛寫花園,實寫琳達內心與自我,人的精神世界與自然景物相互交融,自然流暢,其疏淡素雅的風格赫然紙上。樸素但不直白,清淡又別有深意,這恰是20世紀初知識分子渺茫但不絕望心態的另種詮釋。
曼斯菲爾德對小說文本的情節淡化處理受契訶夫影響,契訶夫對苦心孤旨經營離奇故事的做法十足反。
情節淡化使得人物心理和細節得以在整個作品中占據重大地位,曼斯菲爾德小處落筆,細處堆積,濃縮人生影像,從而構成自然隨意又不事雕琢的深刻精致的風格。諸如在《蒂勒爾街的春天》中就有這樣一筆點神的細節描寫:夜里下過雨。路面上還有一洼洼的積水,好似摔碎的星星。這樣一筆關于雨后積水的細節描述,即將春天那變化無常的氣候表現了出來,而將積水比喻作“摔碎的星星”則增加了作品的詩意。同時,也表現出春天的每一處細節都充滿著詩意之美、詩意之趣。
曼斯菲爾德反對那種只為了吸引讀者而故意安排不合乎生活真實的所謂的情節,她這樣說道:要推動情節的發展,讓它自然形成,而不是捏造出情節。她對作品的情節不做刻意安排,因此人們認為她是生活實情的講述者(truth-teller)。對情節的淡化處理使曼斯菲爾德的作品呈現出那種讓人耳目一新的清新自然的顛覆傳統情節處理手法的散文化筆法。
情節的淡化離不開作家高超的藝術表現力,只有具有高超藝術表現才能的作家,才膽敢脫離靠離奇荒唐事件吸引讀者的路數。納里曼·霍馬斯基談到曼斯菲爾德小說在認識生活的提示作用時說:“千家萬戶日復一日地過著這樣的生活……我們已司空見慣,不以為然。這些我們視而不見的事物,在我們的意識中就像浮塵在空氣中漂動。只當從縫隙中射進一線陽光,照亮那薄薄的一片,我們才意識到浮塵的存在。”曼斯菲爾德在作品中所展現的并不是個離奇的世界,同契訶夫一樣,她所在意于心中的,還是生活的本來面目,只是,經她一支妙筆之后的“生活”,呈現出另一種美。象曼斯菲爾德那樣敢用普通人家的普通一天作為小說素材,需要膽略,更需要高超的藝術表現能力。當代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在創作手法很多方面,與曼斯菲爾德一肪相承,可見曼斯菲爾德開拓了經久不衰的小說新局面”。
(作者簡介:徐晗,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