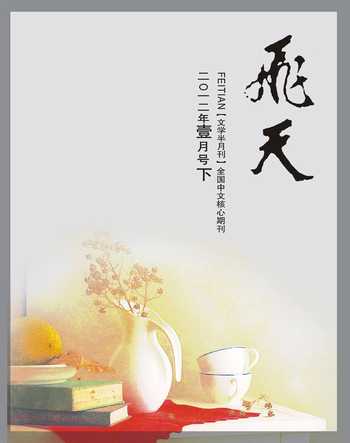梁楷《八高僧圖卷》藝術探究
公元六世紀初由南天竺僧人菩提達摩所創的禪宗,是佛教在中國“本土化”后形成的真正意義的中國佛教宗派,隨后的六祖慧能確立了南宗禪。南宋時期,江南一帶南宗禪宗興盛,使當時的道釋人物畫的內容與形式也受到了禪宗思想的影響,梁楷的《八高僧圖卷》就是在這樣的環境產生的。
禪畫大致分三類主題:一是禪宗高僧和祖師的描繪;住持、禪師和師尊的肖像;禪會畫。創作禪畫的藝術家們一般會根據所繪主題選擇最合適的技巧方法。梁楷的繪畫風格除對后世產生巨大影響的減筆體,還有一種雅致的“精妙之筆”宮廷畫繪制。在表現違拗舊習的人像常以“減筆”繪制,如《六祖截竹圖》。而禪師的肖像畫為表示敬重,不折不扣地再現師尊的真容,就會采用線條細膩而富于描摹性的繪法“工筆”,以用墨和用色精細為特點,《八高僧圖卷》就是他這種風格的代表作。
此長卷共有畫面八幅,其內容分別是《達摩面壁·神光參問》《弘忍童身·道逢杖史》《白居易拱渴·鳥窠指說》《智閑擁帚·回晚竹林》《李源、圓澤系舟·女子行汲》《灌溪索飲·童子方汲》《酒樓一角·樓子參拜》《孤蓬蘆岸·僧倚釣車》。以神光拜見達摩的著名故事為開始,描繪了禪宗所說的頓悟的瞬間以及祖師、高僧與弟子間的機緣,我們也可將《八高僧圖卷》視為一幅禪宗譜系畫。梁楷在這幅作品中沒以減筆作畫,而是追求一種天衣無縫的雅致,根據不同的內容和形象,運用不同筆法來表現各種不同的形態和生動的神情。謝稚柳先生曾評價該作品:“人物畫從粗細一致的線條,從直下而園轉的帶有釘頭的下筆到方折的,以及從粗壯的到纖秀的形體,在這卷中看到他從傳統而來的種種表現,以及面部描寫的深刻,無不洋溢著筆的善變多能和形象的特性所產生的奇妙骨氣。”同時畫家還緊緊抓住了人物表情與姿態的變化,營造出人與人間的相互呼應及畫面的戲劇感,充分配合了卷中敘事性的畫題,使觀者從中感悟到禪給予的生活啟示。
梁楷還將畫中人物安置在一種詩意的山水背景中,構圖延續了南宋院體山水畫“邊角”特點。畫中或布置小徑,或在一角營造樹干與河水,使人感覺畫中人物仿佛是被安排在舞臺般的空白平面上,畫面充斥著戲劇般效果。如《孤蓬蘆岸·僧倚釣車》,畫家就選擇描繪一個蘆舟中的人,以背側四分之三的視角,向近岸寬闊的寧靜水面探出身去,觀者僅見其后腦。梁楷并未太多著力于對遠景的描繪,僅以寥寥之筆墨暗示其存在。大多數細節聚于畫面左側一角,欣賞者通過玄沙備禪師的背影又將注意力折回畫卷。
此外,八幅畫的場景還重復使用了對角線構圖來分割又聚焦畫面空間,如《達摩面壁·神光參問》與《灌溪索飲·童子方汲》《弘忍童身·道逢杖史》與《白居易拱渴·鳥窠指說》等,它們的構圖形式大致相似,但空間上畫家的巧心經營又因人物間機緣相會的張力而顯得生動。
史料的記載,梁楷曾在他的藝術生涯前期作過畫院待招,受到宋代宮廷畫院“格律”的嚴格訓練。其老師賈師古宗法北宋大畫家李公麟的白描技法,所以在《八高僧圖卷》可以見到梁楷對北宋院體人物畫傳統技法上的學習與承傳,以及功底深厚的寫實技巧,展現出13世紀初禪宗思想與圖像傳統之成熟狀態。梁楷“減筆畫”的創造就是孕育于這傳統之中又超越傳統的作為;他的靈感源自對前人深厚繪畫藝術的積聚,以及自己的領悟力與實踐力。
梁楷是一位愛用筆墨表現自己個性的藝術家,在這幅作品中,畫家卻沒有用過于有表現力的繪法或故意出奇的圖像構思來展示自己的繪畫才能,但其大膽的創新在于通過其幽遠的環境、非常的人物,以及奇妙的對話表現出其淳樸的本質。畫面布局靈活,畫家通過將所繪人物視線集中到聚集點,無需通過對畫中人物臉部或眼部的注視就能把我們引入到禪的精神開悟中。這種獨特的視覺效果創造,讓畫面表現出與禪相同性格的東西,也體會了如不能體現禪家的清凈之心,則不能稱之為禪畫的意義。史料記載梁楷與佛門的往來密切,使我們不僅在宗教題材還是他的人物、花鳥、山水題材的作品中,都能體會到畫面中浸染著佛法的奧妙、禪宗的機鋒。
在世人眼里禪比佛更受人鐘愛,其原因在于它把極樂世界與世俗的距離最大可能地拉近了,使人感到不是飄渺,正所謂“郁郁黃花,皆有佛性”,花草樹木、人神動物無不可以入禪。梁楷在禪畫的創作也秉承著禪的這種世俗化表現,以佛教人物為題材的作品,會在其行為上、裝扮上盡量世俗化,摒棄傳統佛教繪畫將其高高在上的尊貴神秘感,除去了其他禪宗世系畫中的光暈和一些神話標志,而盡可能地將其轉化為世人的形象,比如《智閑擁帚·回晚竹林》,真正地表達出“運水搬柴,無非大道”,在日常生活事務中修得真知,所謂“道不可須臾離者”。
“以貌取神”、“以神取形”是中國古代人物畫創作的高超手法。《白居易拱渴·鳥窠指說》刻畫唐代詩人白居易在任縣官時入山訪禪宗大師鳥窠的故事。老人弓著背,伸出食指作教誨狀,反駁白居易稱其身處危樹之上,睿智的神情躍然畫中。
梁楷雖在畫院任過職,但他的作品中不具富貴之氣,反而充滿了文人氣息,這得力于北宋中后期,畫院長期對文化的重視,使畫院畫家的文化素質和審美趣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這種情況在南宋畫院一直延續著,并使南宋院體畫發展出與北宋不一樣的風格。
宮廷畫院的畫家們的創作必須符合統治者及其他皇室貴族們的審美趣味,北宋初期,入畫院者為皇室所服務都必須作“富貴”一路,連徐熙的孫子徐崇嗣都不得不改變繪畫風格。同時我們也看到,梁楷的繪畫中如此強調自我表現的藝術主張而不被處罰,在一定程度上歸于南宋宮廷畫院寬松的創作環境,畫家待遇提高并兼容了多種繪畫風格。北宋易元吉就由于風格與畫院的人不一樣,“畫院人妒其能,只令畫嶂猿,竟為人鳩”;崔白多次被“恩補畫院藝學”時也“固辭之”。統治者的兼容態度,使南宋畫院沒有兼守一家之風,為梁楷的創新提供了先決條件。另外梁楷不受金帶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畫院的管理寬松。將皇帝賜予的金帶掛于院內,可以說是對皇帝的大不敬,但史料中并沒有對梁楷的這種行為進行處罰,反而是院人“無不敬伏”,由此可見南北宋畫院風氣的巨大差異。
在南宋,一張卷軸上包含多幅禪畫的作品可能比現存圖像記載所提及的還要多,但現在梁楷八個場景連綴起來的卷軸是這類作品中惟一完整保存下來的個案。這幅作品讓我們知道了禪宗對中國古代繪畫的發展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僅影響了中國繪畫語言與繪畫形式,還對繪畫的內容和意境的表現產生影響。
禪宗是一種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在藝術上它的基本目的是以表現個體心靈的真實感受,極端重視個體審美心理的能動性。關注內心修煉上正好迎合了南宋社會中失意文人尋求精神寄托的心理。修禪者憑著自己的直覺和內省經驗,追求瞬間的“頓悟”,從而擺脫煩惱,超越煩惱,進入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梁楷后期從正統的人物畫風逐步地轉變為一種酣暢淋漓、瀟灑自如的大寫意畫風,只因為這種大寫意畫法更符合梁楷對禪宗美學意趣的追求。此外禪宗思想為文人畫風格體系和價值體系的形成也提供了觀念基礎,而且還直接提供了創作人才,將禪宗美學思想深深地滲透在他們的文藝作品當中。
(作者簡介:彭琛,湖北長江大學藝術學院講師,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