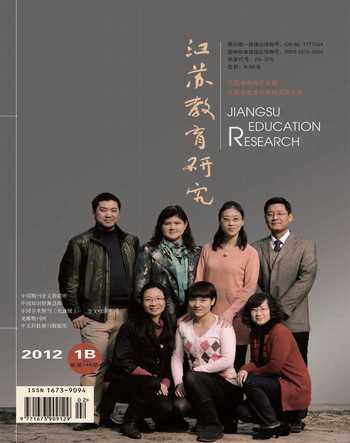從“無語”到“我語”
陳 芳
陳芳:傾聽兒童,讓語文課堂彌散詩意童年的情懷
2010年4月,那是一個春意盎然的時節,力學園中的迎春花開得格外旺盛,這兒一叢,那兒一簇,金黃的小花星星點點,就像孩子們那天真無邪、充滿希望的笑臉。力學園中的老師們也格外激動,因為研究了近五年的學校主課題“力學理念下的研究性課堂的實踐探索與理論建構”進入攻堅階段,我們將整理、撰寫、正式出版一本《研究性課堂實踐論》,寫作的重任和出書的喜悅就像鼓鼓的花苞,讓人緊張而又期待。書稿框架基本形成,我承擔了“研究性課堂中的兒童”這一章節的寫作。可一動筆,我才發現自己盡管熟悉兒童,但真要系統寫書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只能從自己的經驗入手,開始慢慢整理。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我寫出了一萬多字的初稿。當我拿出初稿,和專家第一次對話時,專家微微蹙眉,給我的評價是“視點比較散亂,研究性課堂中的兒童特點看起來很平常,并沒有體現你們學校獨有的兒童觀和課堂觀。還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上看兒童,要把日常的經驗提升至理性的思考。”看著被推翻的那一摞書稿,我“無語”了。
在接下來的兩三個月中,我和教育書店的老板成了好友,我購回了二十多本書,閱讀了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盧梭的《愛彌兒》,還包括劉曉東的《兒童教育新論》,朱自強的《兒童文學概論》等等書籍。從幾十萬字、幾百萬字的書籍中進行了廣泛的摘錄,并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去,當我將這樣寫成的二稿,小心翼翼地捧著與專家對話時,我開始能如數家珍地說出許許多多的名人以及他們關于兒童的認識和觀點。還記得成尚榮先生當時笑著表揚我說:“進步比較大,看來讀了一些書,但你心中的兒童觀是什么?研究性課堂中的兒童有什么特質?你們研究性課堂中的兒童是怎樣成長的?”這一連串的“什么”如醍醐灌頂,一語驚醒夢中人。名家、大家的觀點如此經典,如此精煉,但我囫圇吞棗,已經被他們淹沒了。這一次,我發現自己走向了“失語”。
時至深秋,窗外的梧桐葉已然在空中起舞,孩童們追逐著黃葉在嬉戲著,我在靜靜地凝望著他們,他們如何走進我的筆端,我陷入了又一次的沉思。漸漸地,我的腦海中浮現出那些課堂中喜愛插嘴的孩子;那些拿著調查問卷尋找采訪對象的孩子;那些能寫出“大小力學”般優秀文章的孩子,他們都是有屬于力學文化特質的孩子。我的目光變得清晰起來。我努力描述他們成長的狀態,根據平時對兒童的具體了解和感性認識,用我的語言,描述和提煉研究性課堂中兒童的特點,“兒童是天性自由的探究者,是一種無限的可能性,是豐富的課程資源,在研究性課堂中兒童的成長是一種快樂的狀態……”再次伏案,審視文稿、整理提綱,再到逐漸理性地分析,我終于從“無語”走向了“我語”,這是我寫書過程中最大的突破和超越。從這以后,我真正走上了“我的”研究之路。
如今,我校的“十一五”市級規劃課題《簡單語文 快樂語文 開放語文》和區級優秀課題《以品力研,童心品文——基于兒童立場的小學語文研究性課堂的研究》,都順利結題。這五年中,我們一步步攀登,經歷了畏怯課題研究、走近課題研究、相融課題研究的過程。如今課題研究已經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力學園中的教師研究熱情高漲,他們不再滿足于“守株待兔”式的研究,而是努力尋找“個人課題”。王黎老師研究《閱讀研究性課堂的建設與學生閱讀品質的培養》,沈琳老師研究《用變式教學建構小學生閱讀的一般能力》……全校49位語文老師人人有課題,我也用自己的研究方式不斷感染周圍的老師,消除他們的顧慮,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研究點和合適的研究方法,形成“我的”話語體系,寫出“我的”研究論文,走上自覺的“我的”研究之路。
(陳芳,南京市力學小學,21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