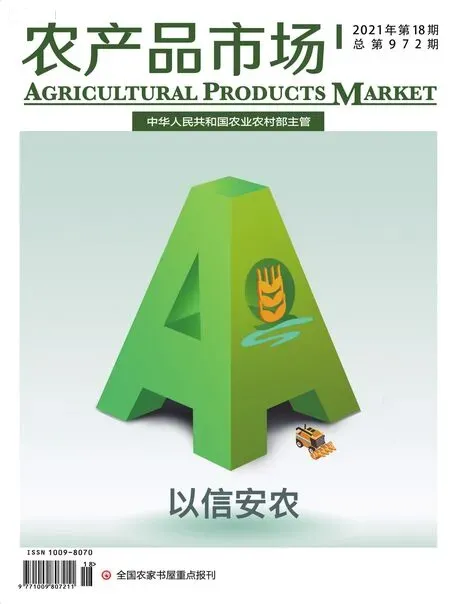5位清華學子的蔬菜供應鏈調研
章軻


“為什么‘菜貴傷民和‘菜賤傷民會同時出現?” “由于蔬菜價格上漲而導致的每月多花在蔬菜上的錢是有限的,但為什么城市消費者對蔬菜價格上漲反應如此激烈呢?”“如果菜販聯合起來打壓菜價是非法的,那么農戶聯合起來抬高菜價就是對的嗎?”
小農:真正的豪賭
5月4日,由社會資源研究所(SRI)提供研究支持的《小農的豪賭——定州—北京蔬菜供應鏈調研報告》對外公布。值得一提的是,這份調研報告是由張金野、汪翔、武通達、黃延、李一帆5位清華大學電子系無線電專業05班的大二學生歷時10個月的艱苦調研完成的。
學子們希望藉此報告,能夠推動社會公眾關注中國農業生產中的諸多現實困難。他們發現:農產品生產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由農戶來承擔。由于缺乏農業保險、組織化生產和分工協作,國內的農戶經營,更像是一場與市場和天氣的豪賭。
供應鏈出了問題
蔬菜滯銷事件發生在全國各地,蔬菜供應鏈的上游是菜賤傷農,在供應鏈的下游,則是諸多消費者驚訝于菜價依舊高企,對市場信號的反應嚴重滯后。那么,問題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憑著很膚淺的認識,我覺得是供應鏈的問題。”汪翔說。
學生們決定進行一次調研,選擇了從河北省定州市的菜地延伸至北京消費者餐桌的蔬菜供應鏈作為調研對象。因為這里是華北最大的蔬菜經銷集散地,以及北京地區批發和零售蔬菜的主要供給源。
2010年,定州蔬菜總產量229.5萬噸,總產值達到26.28億元,有500畝的馬鈴薯種植示范區,十大規模化種植區,包括了白菜、西紅柿、陽春白菜等數個品種。其中辛興無公害蔬菜生產基地有100畝土地,350個溫室大棚以及占地10畝的蔬菜批發市場。
考慮到定州的主產蔬菜種類,學生們選擇了土豆和西紅柿兩條產品供應鏈作為研究對象,以及定州和北京典型的村莊、批發市場、超市和農貿市場。走訪了5個村子,調查了市場上的60戶攤販,得到有效數據22份。還走訪了30多名普通市民和蔬菜協會的工作人員。
調研發現,菜農已經逐步由原子化的分散種植,向組織化生產和銷售過渡。在組織化生產的3個村莊中,農業協會的成員在種植季節會互相幫助管理,出現病蟲害之后也會一起處理,但不會統一銷售。采購商會自己通過菜站找到農戶。
辛興村的西紅柿種植基地則由大戶牽頭組織。據介紹,在種植環節,基地的帶頭農戶會聯系種子廠商,由于基地的需求比較大,廠商會到村里結合土壤條件,試驗不同的種子,此后農戶再選出自己滿意的種子。
此外,該基地也建設了溫室大棚,西紅柿能夠晚兩個月上市,畝產也達到了3-4萬斤,而一般村子的畝產只能達到1-2萬斤。在銷售環節上,因為品種和反季節的原因,客戶一般都會提前和基地的農戶簽下訂單。由于畝產量會根據當季的氣候條件而產生波動,如果合同訂購量小于產量,基地會統一聯系采購。
調研發現,在一年之中,菜農會根據前一年銷售的結果,選擇種2-3次不同品種的蔬菜。由于不擅長使用網絡工具,只能收看電視中的農業技術類節目,缺乏了解農產品價格或者整個市場情況的信息渠道,因此菜農對于市場價格的影響力有限。定州的菜農平均每年能獲得純收入5000元左右,這里面還包括農閑時打零工所獲得的收入。
價格波動三年一次
蔬菜從田里運出來,便進入到介于農戶和買主之間的菜站。
在定州,菜站大多是由2-3個人的家庭經營方式運作。通過幫助外地貨主聯系購買當地蔬菜,按照每斤提取2分錢的中介費用來盈利。中介費不會根據品種和市場行情的變化而改變,統一固定為2分錢。
菜站分別與當地農民以及外地的貨主達成口頭協議,之后貨主會提供車輛到菜站收菜,并在事后付貨款。在收購的時候,菜站還會對菜品進行一定的質量把關。
菜站的成本主要在于門面的租賃費用或者購買門面的一次性投資上,租賃價格每年3000到5000元不等。
據上述調研報告介紹,東關市場和西關市場是定州市的兩個主要農貿市場。作為農產品集散地,兩個市場各有特點:
東關市場離農村更近,也不對交易的農戶收費。許多農戶直接將收成的菜拉到市場中,與外地來的買主進行交易。這里也聚集了近20家菜站,他們租住的房子包圍了市場的三面,在這里菜站可以更方便地聯系到菜農,而且方便掌握市場信息。
西關市場則更加綜合,既有針對當地百姓的零售區,又有提供給大型采購商的批發區,批發區里的賣家一般也是外地經銷商。市場管理方會對賣方收取一定的費用。固定攤位按地方大小收費,單價一般在每月每平方米20元左右,車輛則是每天50元,較小的個體三輪,每天收費5元左右。
“定州蔬菜產量充足,均價較低,吸引了大量外地貨主。”報告稱,來自北京新發地農貿市場的貨主,平均2天完成一次收菜——賣菜周期。通常在凌晨1-2點就開始賣菜,作息極不規律。一輛大型卡車跑運輸,每月可以盈利5000至7000元。每輛車通常會有3-4個人輪替,人均月收入在1700元左右。
到了北京新發地農貿市場,管理方會統一規劃賣方的位置。分類標準不盡相同,有按地域分的,也有按品種分的。每車入場會收取入場費用,一般最小的三輪車,準載0.5噸,需要交50元左右;準載10噸的中型車,需要交150元左右;25噸的大型車在500元以上。
而遍布京城的超市、小型菜市場和個人商戶是蔬菜供應鏈的終端,直接面向個人消費者。他們一般從大型農貿市場如新發地收菜,其經營成本主要集中在場地租賃費用、水電以及人力成本上。
調研發現,就供應鏈不同環節的生產成本和銷售價格來看,流通領域中越接近消費者的市場主體,其增值幅度越大;在與消費者直接發生交易的市場主體中,小型超市的增值幅度最大。
以土豆為例,田頭收購價在0.4元/斤左右,到菜站和農貿市場價格為0.55元/斤,到北京新發地農貿市場為0.8元/斤,到大型超市為1.38元/斤、小型超市為2.25元/斤、個體經營者為1.7元/斤。
除此之外,蔬菜的價格波動幅度也過大。調研發現,東雙屯種植的大白菜,2008年每斤賣8毛,2009年則下跌到7分錢。而這樣的情況,在土豆、西紅柿等“大路菜”中非常多見。據農戶反映,類似的價格波動可以達到每三年一次。
農戶缺乏經營聯合
調研發現,當發生自然災害、種植面積過大等因素,導致發生價格波動時,各級經銷商通過自身對蔬菜定價的影響,可以把大部分風險轉嫁到了農戶身上。
具體做法是:菜站、貨主等通過壓價,控制產地蔬菜進入消費地的總量,以保持在消費地的供求關系不至于波動過大,確保自身的盈利水平。但無法進入市場的“過剩”蔬菜,小部分能被產地附近有限數量的居民低價消費掉,多數則不得不爛在地里。
報告稱,定州蔬菜的價格形成,主要在于外地貨主、菜站和菜農三者之間的博弈。貨主是主要的給價一方,而菜農是應價方,菜站起到的是一個經紀人和傳遞信息的作用。
由于菜農多數是分散銷售,外地貨主就獲得了較為有利的談判地位,其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買方市場,不用擔心收不到菜。而菜農之間有時還會因為賣菜發生沖突。
調研還發現,在農業產業化的政策背景下,政府對大規模的蔬菜生產基地給予了較多的扶持。但對于中小規模的蔬菜種植農戶而言,這些政策沒有起到實質上的惠農效果。此外,由于缺乏運作經費,科技服務站對于許多農戶而言,形同虛設。
“關鍵問題在于農戶缺乏生產經營聯合以及利益聯合。”報告認為,農戶應逐步實現統一銷售,向供應鏈下游兼并菜站。如農業協會能順利實現統一銷售,形成一定的供應規模,那么菜站這一經紀人環節可以被納入到協會或者說合作社的職能之中。在此基礎上,可以順利構建農村和超市對接的模式。
而對于菜農市場供求信息缺乏的問題,學生們也建議,與其由政府出面進行大規模一次性投入,建設功能完整的高端信息平臺,不如購買社會組織或商業主體的服務,分步實現以下目標:提升農村地區的網絡接入密度和帶寬,培訓農戶有針對性地使用和掌握相關網絡技術;完善現有的大型集散市場管理,配套建立市場信息采集平臺,農戶在家中便可以利用網絡跟蹤市場價格信息變動,并發布供應信息。
據記者了解,根據國家發改委、農業部今年1月頒布的《全國蔬菜產業發展規劃(2011-2020年)》,我國將在全國蔬菜優勢產區和大中城市郊區,建立由蔬菜生產信息監測重點縣、省級數據處理中心、部級數據處理中心組成的蔬菜生產信息監測體系,對全國大宗蔬菜的播種面積、產量、上市期和產地價格信息進行采集、分析、預測和發布,合理錯開播種期和收獲期,防止盲目生產。
與此同時,在全國蔬菜優勢產區和大中城市郊區,扶持一批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規模化生產主體,逐步解決一家一戶生產管理、技術推廣、產品銷售、質量監管難的問題。
“或許我們所做的對菜農沒有多少幫助,或者根本沒有任何幫助。但我們希望這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尤其是相關部門的專業人士,大家一起行動起來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我想,這就是我們這次實踐最大的意義。”汪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