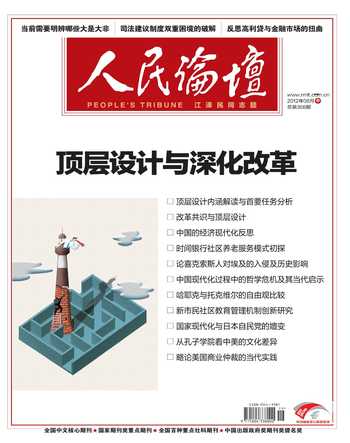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權之正當化功能分析
劉紹宇
【摘要】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是行政立法公眾參與的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是行政立法政治正當化的關鍵所在。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權,是民主行政和法治行政的必然要求,其主要功能,一言以蔽之,就是對行政立法的正當化,具體而言,主要有政治正當化功能、社會正當化功能和經濟正當化功能。
【關鍵詞】行政立法動議權政治正當化社會正當化經濟正當化
法學語境下的正當性,可視作一種批判性的分析工具,來對公共權力進行拷問,對一項制度進行反思,主要研究的是實定法的正當性,兼具形式和實質兩個維度,形式正當性指的是法律的效力位階問題,即下位階的法律必須服從上位階的法律,所有的法律必須服從最高位階的法,實質正當性是指法律必須符合一定時空下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政治理想和價值規范,從而達到被社會公眾所接受的目的。
在傳統的理論中,立法都是議會的專利,行政機關立法明顯屬于越俎代庖之舉,貽害無窮。但是隨著行政的疆域不斷擴大,國家從“守夜人式國家”轉向“行政國家”,行政立法也應運而生,而且愈來愈成為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實中的廣泛存在并不能為行政立法提供正當性基礎,諸多學者從必要性的角度來為行政立法的正當性進行辯護,但顯而易見的是,必要性并不能為其正當性提供一個完美的解釋。我們必須認識到,行政立法是一柄雙刃劍,必須揚其善抑其惡,在充分肯定其在現代社會的作用的同時,通過一系列的機制來對行政立法進行正當化。“現在的問題不是需要授權立法與否,而是采取何種控制和保障手段,以使所授之權不被濫用。”①而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機制正是行政立法正當化的手段之一,其主要功能,一言蔽之,就是行政立法的正當化,具體而言,有政治正當化、社會正當化和經濟正當化三個方面。
政治正當化功能:公眾參與
行政立法本身就備受爭議,因其與傳統的權力分立原則不同。按照傳統的權力三分法,立法權本應該由議會行使,議員經過全體人民的合法委托代表全體人民行使立法權,也因此使得議會立法獲得了無可爭議的正當性。現代社會,受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影響,社會公眾將自己的權利通過社會契約讓渡給國家,國家的一切行為必須符合公意,否則就會被視為背信棄義,政權的正當性基礎也就蕩然無存。符合公意,或者說經過人民同意,是現代法律的政治合法性基礎。而行政立法在政治合法性上顯然難以讓人信服,學者們一直尋找行政立法政治正當化的途經,目前來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立法機關的授權,另一個就是公眾參與。前者,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來看,是一種二次授權,人民將手中的權利讓渡給立法機關,而立法機關又將其授予行政機關,這時,代理人風險就會增高,換言之,立法機關授權在行政立法正當化中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后者,作為一種直接民主的模式,能夠有效地實現行政立法的正當化,化解行政立法的正當性難題,以至于有學者指出,公共參與是行政立法正當性的基礎。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是行政立法公眾參與的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公民的行政立法動議機制則是行政立法公眾參與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行政立法政治正當化的關鍵所在。
社會正當化功能:利益平衡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開始出現分化,社會階層開始復雜化。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各個階層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利益沖突也就在所難免。而在這種利益沖突之中,不同的階層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大相徑庭,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不公平現象,正如孫立平所說:“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可以將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作為一個分界,所劃分的兩個階段在改革的邏輯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概括地說,就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定型下來的社會結構,已經在強有力地影響著改革的方向和實際的進程。”②
利益平衡是法律的基本價值,行政立法由于數量最多、與公民生活密切程度最強,在社會利益平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賦予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權,建立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機制,能夠有效地起到利益平衡之功效,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平衡社會公眾弱勢社會階層與強勢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由于信息獲取、文化水平、經濟條件等因素,相對于強勢社會階層,弱勢社會階層往往對以行政立法為主要形式的公共政策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都甚微,且在制度層面,我國缺乏一個完善健全的利益訴求機制,這是導致我國上訪率居高不下,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擔當了一種利益訴求機制的功能,能夠有效地保障弱勢階層的參政權,讓行政機關能夠及時了解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第二,平衡行政機關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通過控制行政權力,防止行政機關為了自身的利益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國關于行政法理論模式的學說“控權—平衡論”認為,“控權是實現平衡的手段,控權是平衡指導下的控權;平衡是控權的目標,平衡只有通過控權才能實現。”③行政權力作為一種公權力,具有天然的擴張性,只有通過對其控制才能實現國家利益和公眾利益的平衡。“經濟人假設”告訴我們,每個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機。行政機關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實體人,但行政機關無疑也存在自身的利益追求,這種利益追求可能是基于行政職責對行政效益最大化的良性追求,也可能是非良性的出于維護本部門人員利益的追求,這兩者都有可能會損害社會公眾的利益。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法律供給主體的意愿取決于私人凈收益的大小,私人凈收益大,供給效率就高,反之,供給效率就低。在社會凈收益較大而供給主體的凈收益較小的時候,供給主體的供給意愿難以形成。”④將公民的行政立法動議權制度化,就會有效地克服法律供給主體,即行政立法機關的經濟偏好,使其更好地發揮利益平衡的功能。
經濟正當化功能:效益最大化
基于功利主義的哲學觀,經濟正當性是實質正當性的重要維度之一,反映在立法層面,就是立法要符合“成本—收益”的標準。行政立法效益是指行政立法收益與行政立法成本的差值,用公式表示就是:立法效益=立法收益-立法成本。從行政立法成本角度來看,賦予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權能夠有效地降低行政立法的信息搜集成本和執行成本。由于公民動議的行政立法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礎,在執行的過程中能夠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支持,從而減少了執行成本。同時,行政立法需要廣泛而真實的信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行政立法者由于種種原因往往無法接觸到最真實的信息,而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機制則使得公民能夠隨時向行政立法機關反映自己的利益訴求,如此,行政立法的信息搜集成本就會大大降低,搜集的信息質量也較高。
從行政立法收益的角度來看,公民立法動議機制能夠提高行政立法收益。如果將行政立法作為一種政府對社會公眾提供的公共物品,那么由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和社會現實的變動不居,法律供給與法律需求之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時滯”。這時,如果作為法律供給主體的行政機關能夠及時對社會公眾的法律需求作出回應的話,行政立法的收益就會比較高,反之則低。這是因為,當社會出現法律需求,而法律供給者沒有及時地作出回應,社會將會訴諸其他的方式來滿足這種需求,當需求非常迫切的時候,甚至會采取違法的方式。而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機制則能夠使行政機關及時對法律需求作出反應,使行政立法與法律需求之間的“時滯”大大縮短,從而提高行政立法的收益。
結語
隨著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立法模式也正在向開放型、回應型、自下而上型轉變,這從立法聽證、公開制度以及近年來流行的開門立法,公開征集意見等可見一斑。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司法解釋工作的規定》,史無前例地明確了任何公民和組織皆可推動司法解釋立項,就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難問題的司法解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的機制。由此可見,我國司法解釋的公民立法動議權的雛形已經形成。從行政立法的情況來看,雖然沒有一部全國性的法律來確立公民的行政立法動議權,但是很多地方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都賦予了公民這一權利。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我國行政法治和行政民主不斷推進的大背景下,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機制,在各個地方的實踐和經驗總結中,公民行政立法動議機制一定會被搬上立法議程,成為我國行政立法過程中的必經程序。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注釋
①曾祥華:《行政立法的正當性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6頁。
②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30頁。
③郭潤生,宋功德:“控權—平衡論—兼論現代行政法的歷史使命”,《中國法學》,1997年第6期。
④汪全勝:“論法律均衡—關于法律的制度經濟學分析”,《廣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