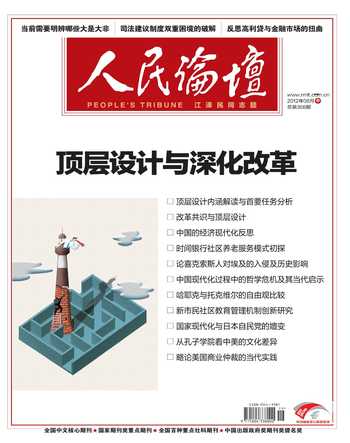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反思
尹保云
發展中國家有不少國際級別的富翁,但很少見到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因為私營企業的成長極其困難。它需要特殊的溫室環境。盲目追加投資、資源掠奪性開發等行為,都會帶來經濟數字的增長,但不會帶來現代化。我們的發展前景并非是已經確定了的,而是取決于進一步改革決心的大小。
評價經濟現代化的標準
這些年我們過多地追求經濟數字的增長,其實經濟數字盡管重要,卻不能說明經濟現代化的水平。中東一些石油國家的人均產值很高,但那里并沒有經濟現代化的發生。盲目追加投資、掠奪性開發資源等行為,都會帶來經濟數字的增長,但不會帶來現代化。
現代化是包含器物、制度、觀念等方面進步的綜合過程。人們一般習慣于把這三者分開,把經濟現代化看作器物的增加。其實,即便是經濟現代化,器物的增長也不是根本的,更加重要的是制度和觀念的變化。就制度而言,要建立起產權明晰的規范市場經濟;就觀念而言,要樹立權利意識、契約意識、法律意識等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觀念。
制度和觀念的變化好像說不清,因為每個國家都可以夸耀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其實不是這樣。因為制度和觀念要產生一個結晶即“企業組織”,而企業組織既可觀察又可量化統計。現代化理論的結構功能學派以及經濟學的制度學派都把企業組織強調到最突出的位置,把它的發展程度作為衡量經濟現代化的標志,而把器物和數字的增加僅僅看作是結果。他們所說的企業組織是指私營企業。私營企業的發展在邏輯上要經歷個體企業—私有小企業—私有中型企業—私有大企業(包括家族大企業和股份制大企業)這樣一個臺階。這個臺階標志出不同的發展程度。如果尚處在個體企業或小企業階段,那么經濟現代化就是初步的。如果出現了私營大企業群體,那么經濟現代化就進入高級階段。當然,還需要看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多少。私營企業的比重越大,經濟現代化的程度就越高。
私營企業的角色和重要性作為一種理性知識早已深深地滲透進美國的政治文化中。歷屆美國總統都把“企業家”作為國家信心的根據而掛在嘴邊,連小布什在“9·11恐怖襲擊”發生后的電視講話中也這樣說:“我們不怕,我們有企業家!”私營企業的重要性也得到世界歷史的反復證明。原蘇聯曾經風光一時,卻突然地崩潰了,因為它沒有企業家(私營組織),80多年間沒有發生經濟現代化;日本在二戰中幾乎把所有的經濟基礎打光,但卻在短短十多年就迅速恢復,因為它有企業家(私營組織),有經濟現代化。這樣正反兩方面的例子說明,把私營企業組織作為評判標準,我們就能更準確地預測一個國家的發展前景。
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比通常估計的大
我國大陸地區的私營企業通常被稱為“中小企業”,但從規模、技術、管理、適應性等方面看還遠不能與發達地區的中小企業相比。多數私營企業目前還處在粗糙的個體企業和家庭小企業階段。同時,私營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也很低。改革開放后,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指導下,私營企業從無到有并不斷壯大。根據工商聯2011年7月公布的數字,目前民營經濟占我國GDP總量“已超過50%”。這同改革初期相比的確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同經濟現代化的要求相比,這個數字就低得可憐了。就全國看,制造業領域的數字要高一些,超過了70%。但是制造業領域外資較多,凡是有較高技術的企業背后都是外國公司的背影。如果去掉外資成分,制造領域的私營企業的比重也同樣是很低的。
占產值總量“已超過50%”是什么概念呢?與韓國比較一下我們就清楚了。韓國在1945年后國有資產占總資產的90%以上,這些都是沒收的日本殖民者的財產。韓國在1950年代初搞了私有化,搞得迅速徹底,連幾家大銀行也私有化了,從此到1980年代國有企業占產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到8%之間。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向“東亞四小龍”主要學習了出口導向、引進外資、擴大投入等政策,但在制度層面上卻學習得不夠。從工業化整體水平及人均指標看,我們現在大致相當于韓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水平。如果比較私營企業的發展階段,那么我們目前也就是韓國1960年代初期的水平。
企業組織的差距是經濟現代化的深層差距,是制度和觀念的差距。這種差距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力量是強大的。多年來,從政府到社會各界都為一些現實問題所困擾,諸如居民收入增加緩慢甚至停滯、兩極分化、城鄉差距大、技術創新力低、內需不足等等,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技術”,一是“民生”。為什么總是得不到很好的解決?根源就在于私營企業成長緩慢。試想,國有企業效率低,而私有企業又沒有成長起來,靠什么來實現產業升級和生產方式轉變?同時,“民生”的目標只能靠民營來實現,因為民營就是民眾的參與。然而,生產50%的GDP的私營企業雇用80%以上的工人,而生產另一半GDP的國有企業卻雇用不到20%。一些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壟斷資源,盲目投資,綁架金融地產,在制造泡沫數字的同時不斷地進行私分、貪污、浪費、資產轉移的運動,80%的勞動者(還不包括農村)被排斥在這個運動場之外。在這樣的機制下,怎么可能解決好“民生”問題?
企業組織的落后對現代化的延誤往往是以百年為單位來計算的。拉丁美洲在17世紀早期城市、交通、文化等發展水平高于北美,但由于沒有私營企業組織的發展而很快被美國超過,從此就一直落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主要拉美國家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也經歷了幾個高增長階段,也出現過讓國際驚嘆的“奇跡”,現在它們的人均產值已接近1萬美元,城市化率也早已超過80%,然而,他們離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遠距離。技術創新力弱、教育落后、大面積貧困、農村落后等問題并沒有隨經濟增長而發生絲毫改變,而是被固定化、永恒化了。在體制上,這些國家長期保留一種“混合經濟”,私營部門、封建性大地產、龐大國企部門共存。私營企業始終處于受擠壓和被扭曲的不發達狀態。同拉美相比,我們目前“混合經濟”并無特殊之處,雖然我們沒有封建性大地產,但是我們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其封建性一點也不弱。而且,我們國有企業壟斷的局面要遠遠超過拉美。
前途取決于進一步改革的決心
發展中國家有不少國際級別的富翁,但很少見到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因為私營企業的成長極其困難。它需要特殊的溫室環境。
第一,政府的積極、大力扶植。西歐國家的私營企業當年并不是自然長大的。早期受到貴族和王室的支持,比如哥倫布的航海船;重商資本主義時期則受到國家的幫助和保護,比如各個東印度公司就是這個使命。后起的德國和日本,它們的私營企業的崛起主要靠政府的扶植。韓國是戰后世界上唯一在制造業領域培植出私營大企業的國家。這依賴于一種特殊的體制。樸正熙政府不僅為企業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而且通過免稅、獎勵、低息貸款等方式幫助那些業績優秀的企業加速資本積累。1962~1971年,僅給予企業的利息津貼就占國民產值的3%。1972~1979年,為了配合重化工業發展和產業升級,韓國政府給企業的貸款利率最高為3%,最低為 -14.9%。此時期約10%的國民產值補貼給了私營企業。三星、現代、SK等大財閥企業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長起來的。
第二,國有企業要迅速收縮從而為私營企業騰出空間。在現代化早期階段,政府投資一些國有企業以彌補私人投資不足是正常的,但是要盡快地退出。在此,總結一下臺灣地區的教訓很有必要。臺灣地區在1950年代的私有化沒有韓國那樣迅速、徹底,而是時間拖得很長。這使臺灣地區在1960、1970年代的高增長時期沒有成長出大的私營企業,直接影響到之后的產業升級。到了1980年代,臺灣地區在技術上比韓國低了一個臺階,一直遙遙領先的人均產值也在1990年代被韓國反超了。
盡管如此,臺灣地區還是提供了國有企業一路收縮的成功范例。而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情況則是國有企業膨脹容易而收縮困難。這不僅是因為受到認識或意識形態的阻礙,還有很多別的原因。1960年代中期巴西、阿根廷上臺的軍人政府信誓旦旦地要壓縮國有企業而發展私有企業,但在他們執政期間國有企業反而進一步膨脹了。因為官僚集團要通過國家投資來謀取利益,所以找各種冠冕堂皇的借口來擴大投資。無論原因如何,國有企業不能騰出足夠的地盤,私有企業就不可能有大的發展,這樣,無論經濟數字怎樣增長現代化總是空的。
第三,私營經濟的發展需要有民主制度的配合。馬克斯·韋伯曾經指出“理性的資本主義”需要“憲政體制”的支撐。如果不建立起民主制度,那么政治領域的封建權力結構和觀念因素就不會削弱,私有化也很難進展;并且,如果沒有民主制度,即便是搞了私有化,法律體系也難以有效運轉,企業的行為也得不到很好的規范,其性格會必然遭到扭曲而同樣成長不起來。此外,社會道德的提升、經濟透明度的增加、工人權利和消費者權益的保障等等,都需要民主的發展。一句話,政治變革與私營企業的發展是不可分開的。但近些年,國內學界在研究韓國時得出了“獨裁發展”的結論,認為韓國經驗是利用“獨裁”保持社會穩定從而獲得經濟增長。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導。樸正熙總統時期被韓國人認為是“最獨裁的”,但實際上樸正熙政府一直是在憲政體制下活動,更重要的,韓國的政府是“小政府”,不僅規模小而且遠離凱恩斯主義,與儒教傳統的官本位體制的性質完全不同。
除了上述三個方面的條件外,私營企業發展還會受到歷史、文化等其他因素的作用。對于很多國家來說這些條件的確很難達到。這也是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現代化步履維艱的原因。盡管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作為儒教文化圈的成功給我們展示了很大希望,但我們的發展前景并非是已經確定了的,而是取決于進一步改革決心的大小。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