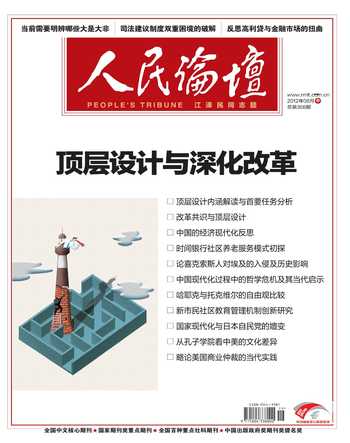民俗旅游文化社區參與的層次分析
劉文穎
【摘要】在大理白族民俗旅游中,喜洲鎮周城村民俗旅游的發展和社區參與模式較為典型,但同時它也還存在諸如村民利益分配不公,精神參與與實體參與不同步,旅行社參與力度弱等問題,需要從探索白族民俗文化資源進行資本轉化的有效途徑等措施入手,提升大理白族民俗社區參與層次,從而實現該社區對旅游的有效參與。
【關鍵詞】周城村白族民俗旅游社區參與利益相關者參與層次
引言
大理白族民俗資源豐富多樣,遺憾的是這些資源至今未能得到很好得開發。喜洲鎮周城村全村總人口10350人,白族占99%左右,被譽為“白族民俗活化石”,至今仍保留著洱海西岸最為完整的白族民俗。因此,周城民俗旅游社區具有發展白族民俗旅游的獨特優勢。經過近20年的民俗旅游開發,其“公司+經濟精英+農戶”的民俗旅游發展模式在大理地區已成為先進和典型。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層次決定了社區參與民俗旅游的深度和廣度。本文通過對周城各利益體在社區民俗旅游中的參與層次和行為意識進行剖析,以期能以點帶面,構建符合白族社區利益的民俗旅游參與項目、參與層次和利益分享體系,從而為其他白族社區對民俗旅游的有效參與提供借鑒。
民俗旅游社區參與的利益相關者及參與層次分析
民俗旅游的社區“參與”及“層次”是一種旅游經濟參與行為,是社區各利益相關者對民俗旅游資源的經濟敏感度和依賴度的強弱表現。“社區參與的層次區分了社區參與旅游的不同程度,相應地不同層次的社區參與將對旅游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力”。社區參與實際上是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在周城,利益相關者主要分為利益主體—文化持有者(社區居民)、外部利益相關者—旅游者、旅游中間商和當地政府幾類。其參與的層次與當地民俗產品的開發時間、知名度及其產生的經濟效益有密切聯系。
文化持有者的參與:自發與自覺。周城社區居民對于扎染產業的參與經歷了散戶自發、全民自覺、精英主導和不參與幾個階段。
20世紀80年代初,周城民俗旅游剛剛起步,當時以接待少量的外國散客為主,扎染處于散戶自發,保守經營狀態,當地居民參與較被動。1984到1995年的十二年間,隨著大理發展旅游力度的加大,周城的游客增多,扎染產業也獲得了跨越式發展。此階段,該村出現了“公司+農戶”的扎染經營模式,即村中成立了扎染廠,廠方負責設計圖樣、對外營銷和對村民進行培訓。扎花工序下放農戶,廠方按時按酬回收村民扎好的布料。村民農忙扎花兩不誤,酬勞穩定與其它產業又不沖突,所以在鼎盛時期,周城村同時有六七千村民參與扎染產業,占全村勞動力的78%。加上鄰村勞動力,每年以周城為中心的扎花勞動力保守統計超過三萬人,每年村民從扎染廠領回的扎花費用可達700多萬人民幣。村民由此致富,扎染產業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周城民俗文化旅游進入全民自覺參與的鼎盛時期。從1996年開始,該村扎染產業的參與層次出現分化。扎染廠部分技術骨干“跳出來”開起了前店后廠式的家庭扎染作坊接待旅游者。這種先參觀制作工藝后購買成品的“扎染民俗體驗游”很受游客歡迎。較好的經濟效益吸引了大量村民的加入。到目前為止,周城形成了以20多戶大型個體扎染戶,40多戶中小扎染戶為主的扎染中間商群體。這些人成為發展扎染產業和民俗旅游的“經濟精英”。“經濟精英+農戶”模式帶動下的全民參與成為這時期周城的主要發展模式。
在“經濟精英”的帶動下,從1997年開始,周城的其它文化旅游產業諸如白族服裝加工、刺繡業和白族餐飲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到2002年,周城人均收入達到3741元,GDP達二億四千多萬,其中扎染產業總收入占到50%左右。2005年以后,扎染廠停產,“公司+農戶”運營模式崩潰,扎染核心技術完全被“經濟精英”壟斷。為爭奪市場,個體經營戶開始惡性競爭,周城扎染質量下降,市場萎縮。此時,雖然周城扎染的“經濟精英+農戶”參與模式仍保持穩定上升狀態,但全民參與的積極性減弱。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扎染產業的經營使得周城白族居民的經濟意識和產業意識發生了質的轉變,部分退出扎染產業的村民轉向經濟作物種植、白族服裝加工、繡品加工、旅游餐飲、特色客棧等高收入旅游副業。2006到2007年,扎染制作工藝被納入到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產業規模及聯動效應進一步擴大,周城人均年收入達到4500元,其經濟效益在大理地區的行政村中位居前列。這是周城白族民俗旅游“精英”帶動,全民參與,轉換意識,實現產業聯動和增值的結果。
旅游者的參與:觀光和體驗。周城的游客以散客為主,團隊為輔。團隊主要是通過跟團游覽進行“觀光性參與”。 散客在周城則會通過更多的“感官”體驗進行社區參與,比如參與扎染工藝品制作,對白族民俗進行深度體驗等。旅游者對周城民俗旅游的主動參與,給當地居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同時也極大地激發了當地人“參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周城是“大理一日游”團隊游客的午餐用餐點,大量團隊的到來使得當地白族餐飲業發展迅猛。但是由于行程安排過緊,游客往往只有一個小時左右的用餐時間,游覽體驗時間很短,這種非正常參與在社區中引起了負面的連鎖反應,即眾多餐館和扎染作坊為搶客源低價競爭,導致旅游服務質量嚴重下降。作為社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旅游者和社區“俱損與共”,提升旅游服務質量,吸引旅游者的回歸成為當前周城民俗旅游社區良性參與必須解決的問題。
旅游中間商的參與:推介和營銷。目前,大理旅游業對旅游中間商—旅行社已形成完全依賴的態勢,旅游產品的設計權和營銷權多掌握在旅行社手中,景區景點難有話語權。據有關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大理旅行社對周城的認可度和參與度只有30%左右。除了一些國際社愿將其納入歐美和日本團隊游的線路外,國內旅行社基本對其不“感冒”。主要原因在于:從吸引力上看,周城的民俗旅游資源單一,市場吸引力小,旅行社不愿做;從線路設計上看,周城與喜洲空間距離過近,受白族名鎮—喜洲“屏蔽”效應的影響,周城的民俗魅力難以充分展現;從旅游項目類型上看,周城的民俗旅游屬于專項旅游,經營成本高,故參與興致低。旅行社是連接旅游者和社區最佳介質之一,如何提高旅行社對周城及其他白族旅游社區的關注和推介度值得思考。
當地政府的參與:引導和支持。政府是民俗文化旅游的引導者和支持者。周城以扎染、白族服裝加工業、旅游餐飲為主的民俗旅游項目示范帶動效應明顯,大理各級政府都表現出了積極的參與熱情。一方面,政府給以政策、資金、科研支持,幫助解決扎染的原料種植和污水處理問題,并給當地民俗旅游項目經營戶解決信貸問題;另一方面,政府從2007年開始派駐長期的民族文化產業觀察員,扶植旅游項目帶頭人,幫助成立旅游協會。村委會作為州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也在村中起到了積極的引導作用。隨著產業參與面的擴大,經濟效益的上升,政府財政稅收快速增長,對當地的“反哺”力度加強,周城旅游環境也獲得了顯著的改善,當地社區居民參與的自信心普遍增強。
綜上所述,周城民俗旅游的社區參與已經步入成熟參與層次,但也還存在諸如村民利益分配不公,精神參與與實體參與不同步,旅行社參與力度弱等問題,如果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周城對整個白族社區的示范帶動效用將會有所下降。
提升大理白族民俗社區參與層次的建議
首先,必須要有符合民情村情和各利益相關者利益的項目作支撐。項目必須具備參與面廣,參與成本低的特點,越是貼近社區居民傳統生活的資源越容易參與。大理白族民俗豐富,就環洱海區域來看,海邊地區可依托蒼洱美景結合“漁”文化項目,發展民俗生態博物館、特色客棧、民族餐飲,給與客人以獨特的體驗。同時,必須做好對民俗文化資源的保護。政府需要加大引導和支持的力度,擴大宣傳,幫助社區克服民俗旅游開發帶來的負面效應,提升各利益相關者對民族文化資源的認同和保護意識,加大對民俗傳承人的保護;打破“小富既安”的思想局限和扎染家族的技術壟斷,廣辦培訓班,真正實現資源項目化,擴大當地居民的參與基礎。
其次,必須找到白族民俗文化資源進行資本轉化的有效途徑。周城民俗旅游發展的經驗即“公司+精英+農戶”的途徑值得借鑒和推廣,在缺乏龍頭企業的時候,“經濟精英+農戶”或“協會+農戶”同樣可以發揮其強大的示范帶動作用。
再次,必須理清相關利益者的參與層次,明確他們在社區參與中的地位、權利和責任,構建“項目+層次+利益共享”的階段性參與體系,并對社區參與的不同層次和階段做出適實調整,以調動各方積極性,實現“利益共享”,真正擴大參與面和利益分享面。
最后,必須進行利益的合理分配。經濟效益的獲得是社區參與的首要動機,社區參與則是包括當地居民在內的各利益相關者參與社區旅游資源開發、管理和獲得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無論在哪個參與層次和發展階段,必須將文化持有者(社區居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確保參與主體的利益獲得,白族社區民俗旅游才能有發展的良好環境和資源,其他利益體的利益也才能得到保障。
(作者為大理學院政法與經濟管理學院講師;本文為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大理周城白族扎染的文化產業效應與調適研究”的成果之一,項目編號:09C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