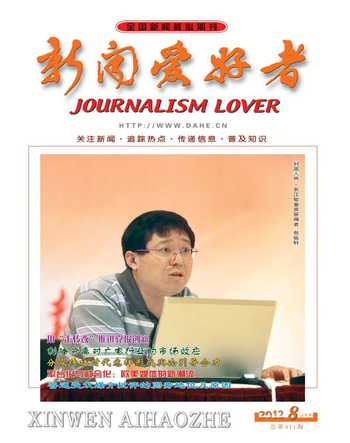長篇連播節(jié)目的廣播語言特征
馮杰
長期以來,在廣播電臺的文藝節(jié)目中,長篇連播的收聽率始終居高不下。究其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吸引力之外,廣播語言所特有的魅力也是不容置疑的。正是由于廣播語言與受眾心理期待的契合,才造就了各地廣播電臺長篇連播長盛不衰的繁華勝景。在慶祝建黨90周年之際,平頂山人民廣播電臺文藝廣播推出了長篇小說連播《龍嘯中原》,這部由本地作家創(chuàng)作、資深編輯改編、本臺播音員播講的純原創(chuàng)節(jié)目一經(jīng)播出,即以其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濃郁的地方特色和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jié)吸引了廣大聽眾,并贏得一片喝彩。在錄制過程中,筆者對長篇文學作品連播的廣播語言特征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理解,現(xiàn)在將個人觀點歸納整理出來,與同行商榷,請專家們指正。
長篇原著的文學屬性與廣播語言的口語特征
長篇小說屬于文學藝術(shù)范疇,它是通過人們的閱讀來傳遞所要表述的內(nèi)容的,具有平面信息傳播的基本表象。根據(jù)人們不同的閱讀習慣,可以瀏覽、翻閱,也可以慢讀、細品,一本書在手即擁有完整的信息,或一口氣讀完、或分章節(jié)閱讀均可。而廣播信息的傳播方式是即時性的,電臺即時傳遞、受眾即時接收,轉(zhuǎn)瞬即過,過時不候。與閱讀的視覺接收形式相比,廣播的聽覺傳遞方式似乎不占優(yōu)勢,然而聲音的魅力是誘人的,在通過聲波沖擊人們耳鼓的同時,也借助聲音所負載的信息內(nèi)容激活了人們疲憊的神經(jīng),喚起收聽的興趣和欲望。這種直接、簡單、快捷的傳遞模式,比起靜止的平面文字對人們的感官刺激要直接得多、迅速得多,從而形成了先聲奪人的優(yōu)勢。
廣播電臺連續(xù)播出長篇小說節(jié)目的生命力,正是基于從書面文學到廣播語言的成功移植和嫁接,它簡化了受眾閱讀的繁瑣程序,節(jié)省了受眾對文學作品的理解時間,無形中擴大著各個文化階層的受眾群體。在書面文學到廣播語言的轉(zhuǎn)化過程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就是口語的運用。口語即口頭語言,也是文學的一部分,只是相對于書面語言而言的。正像寫信與打電話一樣,一個是“寫字”,一個是“說話”。
剛接到《龍嘯中原》這部長篇小說的書稿時,看到作者楊曉宇在小說名字之前冠以“長篇驚險懸疑歷史小說”的字樣。顯然這是一部文史參半的作品,主人公也確有其人、有史可查。牛子龍是一位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1904年出生于平頂山市郟縣冢頭鎮(zhèn)拐河村。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他接受組織委派進入國民黨軍統(tǒng)豫站,屢立奇功,成為特別行動小組組長,成功組織了刺殺華北五省特務總機關(guān)機關(guān)長吉川貞佐及日本關(guān)東軍和日本皇室慰問團的全體成員行動,設(shè)計智除大漢奸劉興洲、徐立中,其英雄事跡震驚國內(nèi)外,受到國共兩黨高層的盛贊。后因軍統(tǒng)威脅,他果斷槍殺了軍統(tǒng)豫站站長崔方平。牛子龍被軍統(tǒng)逮捕后,又在西安成功越獄返回豫西,重新拉起抗日武裝。日本投降后,他在國民黨反動派發(fā)動內(nèi)戰(zhàn)之初,發(fā)動了新鄉(xiāng)山彪鎮(zhèn)起義,終于回到黨的懷抱。
本土的抗日英雄、傳奇的人生經(jīng)歷決定了作品的吸引力,而從文學作品到廣播口語的轉(zhuǎn)型是否順暢決定著小說的可聽性。根據(jù)小說紅色英雄題材的要求和其中很多諸如香山寺、滍陽街、娘娘山、開封、鄭州、禹州等不可割舍的珍貴歷史資料的限制,為避免講述時突兀、生硬、脫節(jié)等不協(xié)調(diào)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經(jīng)過統(tǒng)籌考慮,演播者通過反復推敲及大量的案頭備稿工作,采用了半說半讀的表述語態(tài),把廣播的口語特色發(fā)揮到了極致,使故事播講、史料陳述和場景描寫的轉(zhuǎn)折和過渡顯得平潤、自然,受眾聽起來入耳入心。比如,將原著中的“此人”改為“這個人”、“……的當兒”換為“……的時候”、給人名“鄭驢娃”加上兒化韻等,雖然只是小改動,但已把其“中看不中聽”的文學屬性削弱甚至革除,呈現(xiàn)出廣播語言的口語特征。
實踐證明,做到長篇原著的文學屬性與廣播語言的口語特征的兼容并蓄并不難,只要從作品的主題、內(nèi)容和風格出發(fā),讓廣播語言為文學作品服務,就一定會尋找到最佳的口語表述狀態(tài)。
口頭文學(曲藝)的敘述語境與廣播語言的播讀特征
筆者認為,播講長篇小說時所適用的廣播語言有兩大顯著特征,除了口語之外,就是播讀。廣播語言最初只有播讀一種,作為播音員、主持人的必修課和基本功,沿襲傳承下來。由于先入為主的緣故,所謂標準的“播音腔”成為電臺聲音的主流典范,雖然字正腔圓、擲地有聲,但莊重有余、活潑不足,其適應范圍僅限于新聞及評論的播報,在朗誦文學作品方面顯得難以駕馭,如果用“播音腔”播讀長篇小說就會不倫不類。如何使用廣播語言播讀長篇小說其實并不是一個難題。在長篇小說連播問世之前,已有長篇評書連播的成功范例,時至今日,評書依然是廣播電臺長篇聯(lián)播不可替代的絕對主角。不管是從借鑒的角度來講,還是從學習的態(tài)度來論,以說為主的口頭文學(如評書、相聲等曲藝品種)的語音、語氣、節(jié)奏、技巧等都是播講長篇小說的理想表述方式。
在錄制《龍嘯中原》時,播講者在保持小說原著特色的前提下,大膽地植入曲藝表演的故事敘述語境,用以彌補單純廣播播讀特征的先天不足,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故事情節(jié)更加生動。
先聲奪人,讓開頭不再難。長篇小說的開頭、每個章節(jié)的開篇,文字都十分講究,但唯美的詞句通過口語表述時會略顯“晦澀”。口頭文學(曲藝)的敘述語境的引入使小說播講輕而易舉地擺脫了“開頭難”的困擾,并且出現(xiàn)了一些可圈可點的“導語”。第20講原小說的開頭除了背景介紹外,緊接上章往下敘述。如果播講時按部就班、照本宣科,難免平淡如水、索然無味。為給這一精彩段落錦上添花,播講者設(shè)計了這樣一段開場白:“話說豫西五虎中的老大老君寨寨主孫夢飛、老二三界山寨主陳正卿、老三虎狼爬寨主梁萬生與老五娘娘山山寨女寨主秦椒紅齊聚香山寺,為在槍戰(zhàn)中死去的結(jié)拜老四、倉頭山寨主鄭二麻擺下道場,超度亡魂……”寥寥數(shù)語,把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承上啟下,使轉(zhuǎn)折很“圓潤”。長篇小說的場地轉(zhuǎn)換只需另起章節(jié)或空行留白即可,而廣播語言就要添加一些過渡性的“串詞”,這些“串詞”在曲藝節(jié)目中比比皆是。如常用的“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按下某某不表,再說某某某”等,完全照搬未嘗不可,照貓畫虎也不失為一條捷徑。播講《龍嘯中原》時有很多這樣的實例,如“按下德化街鋤奸不提,咱們再說山陜會館……”、“有人歡喜有人憂,有人歡樂有人愁。牛子龍凱旋而歸,這可氣壞了日本特務頭子吉川貞佐……”,雖說是添枝加葉,由于是在口語的敘事語境中,不僅沒有畫蛇添足之嫌,反而給人恰到好處之感。
巧設(shè)留懸,用“扣子”扣心弦。曲藝表演中的“扣子”就是設(shè)置懸念,在敘事過程中埋下伏筆,以引起受眾繼續(xù)關(guān)注的欲望。在播講長篇小說時巧設(shè)“扣子”,再慢慢解開,自然也會喚起聽眾的收聽興趣。其實設(shè)置懸念并不一定要長篇累牘,只要掌握其要領(lǐng),幾句話就是一個“扣子”,尤其在每集末尾處最為常用。引入曲藝口語后,《龍嘯中原》第17講結(jié)尾就有了這樣的“扣子”:“明知明天的道場暗藏殺機,香山寺危機四伏,那牛子龍匆匆拜完香山,馬上趕到滍陽街,他到底又有什么計劃呢?”第23講的結(jié)尾同樣巧設(shè)懸念:“對手隱蔽、任務艱巨,特別行動眼看要與日本特工展開一場斗智斗勇的生死較量,精彩的故事盡在下集……”
以上實例,既保留著廣播語言的播讀特征,又有清晰的曲藝敘述語境的痕跡,二者之間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只要運用得當,是會相得益彰的。
多元表述方式對廣播語言特征變異的滲透和影響
隨著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大眾的閱讀習慣也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有聲讀物大行其道,對于專攻聲音的廣播來說,可以說是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機遇是大眾對聲音載體的認知和對語言傳播的訴求之中,蘊藏著巨大的潛力和未知的空間;挑戰(zhàn)是被大眾推崇和接受的聲音表述方式并非完全符合廣播的語言特征。
相聲、評書、小品、百家講壇等口語表述方式的幽默、親切,在給廣播語言帶來沖擊的同時,也帶來了有益的啟示。語言表述方式的多元化提供了一個優(yōu)勝劣汰的生態(tài)圈,作為擁有深厚積淀的廣播語言面臨著“四面楚歌”的境遇,主動出擊,找準突破口,吸納多元表述方式,求變求異求新是唯一的可行之路。
廣播電臺的長篇連播要再現(xiàn)文學作品當家的昔日勝景,結(jié)束評書一統(tǒng)天下的尷尬局面,就必須像百家講壇那樣,走下三尺高臺,放下學術(shù)架子,博采眾多語言表述方式之長,充實、豐富、完善廣播語言。果能如此,受益的將不僅僅是小說、報告文學等長篇文學作品連播的播講方式,而是廣義、泛指的廣播語言的表述形式。
(作者單位:平頂山廣播中心)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