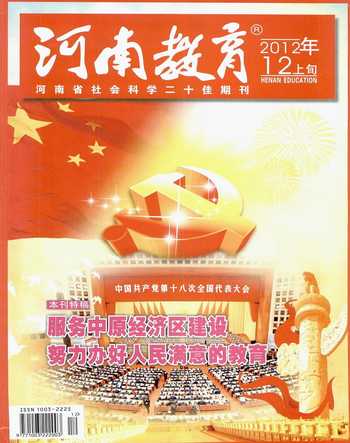校規執行:“一厘米主動權”的良知堅守
王立華
站在統計學的立場上分析,一厘米幾乎是一個可以被忽略的長度、距離,哪怕是違反一些原則,甚至是觸犯社會規則。
一厘米,實在是個能輕松跨越的尺寸。黃口孺子在不知不覺中就能多跑一厘米,賣繩子的小販可以毫不吝惜地向顧客贈送一厘米,處于生長期的孩子一年多長高一厘米也很正常……在負向上逾越一厘米,似乎也不一定會出大問題。栽植冬青,株與株之間多一厘米不會影響綠化效果;學校的自動伸縮門可以少開一厘米,也不影響師生出入;大街上醒目的廣告牌長度減少一厘米,照樣能引起路人的關注……
能輕松跨越的一厘米,真的是個永遠安全的距離嗎?
一
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我,一厘米,放到學生管理中來看,并不永遠是個安全距離。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一厘米的安全性是有很大差別的。
宿舍管理、日記批閱要求等制度再向前“一厘米”,就有可能侵犯學生的隱私;設計校徽時某個構圖元素再增大一厘米,整個圖案比例失調后就不美觀了;教學樓頂懸掛的巨型宣傳標語,再寬一厘米,就可能因招風面過大導致標語牌被吹落;教室的黑板偏左一厘米,右邊的同學看著就不舒服;教室內的多媒體展示屏幕安裝時高一厘米,學生們抬頭看久了就會覺得累……
凡事都有兩面性,一厘米的關照與對待也是這樣。一個學生管理者應該始終清醒地讓一厘米在安全區內伸縮、變動。
二
學校管理者在應對一厘米的安全變動時,存在什么問題呢?
2010年10月9日,在山東省臨沂市六中(現為臨沂十五中)就讀的七年級女生張悅因為發型不符合學校的要求(其實學校也沒有具體的界定標準),在三次被趕出校門后,在家喝下殺蟲劑自殺身亡。
就是因為頭發長了一點(我們姑且計算為一厘米),學生管理者“逼死”了一個鮮活的生命。那么因為發型不合格引發的悲劇或沖突就這一例嗎?不是的。深圳坪山高級中學的蔡勝慧,因頭發過長,被老師批評后跳樓死亡;長沙市九中學生蔡佳因老師剪掉其頭發鬢角,深感氣憤,從二樓縱身跳下受傷;山東省東營市勝利一中的李欣 ,因頭發過長,被老師反復催促剪發后,從五樓跳下身亡……
以上這些關于發型問題的令人觸目驚心的案例,反映出目前一些政教管理制度制定和執行的不合理,其中有些制度的制定和執行連教育的基本良知都沒能堅守住。
三
一位學校管理者對班主任、學生的早晨到校時間做了這樣的規定:“我們要大力推行素質教育,學生早晨7點半前不能進校,但考慮到學生的實際,學校大門是開的,部分學生真來早了可以提前進校。學校不限制班主任的到校時間,但是為了安全起見,教室里有學生了,班主任原則上就要到位。”
這一看似規范的規定從出臺那一刻起就存在不合理性。這是因為學生有從眾心理,有學生來得早,其他學生就會擔心自己落后,也可能會逐漸地早到校。于是,學生們仍舊是早到校,教育主管部門來檢查,政教處是無責的——我們已經限制了學生的到校時間,符合國家的規定,但是個別學生情況特殊,應允許他們進校,要不然會有安全隱患。另外,學校確實沒有規定班主任的到校時間,但是,學生來得早,班主任擔心學生安全出問題,仍然要早來。無形中,等于設定了班主任必須早到校。
類似的規定還有許多:班主任批改學生周記的規定,管理人員隨意出入學生宿舍的檢查規定,強迫學生穿他們不喜歡的校服的規定,以加強校紀為名趕學生回家受教育的規定等。
這些不合理的規定,以愛學生的名義制定,盡管只向前超越了“一厘米”,但也是有危害性的。
四
在執行學校的規章制度時,學校管理者有沒有超越安全線“一厘米”的?有!
對前文中提到的山東省臨沂六中的案例,我們做個假設:假設學生張悅接受了批評,已經理發三次,離學校規定的頭發長短只有一點兒差距,出于對學生尊嚴的維護,教師不再趕學生出校門,而是把張悅留在學校慢慢引導,我想張悅的發型最終會達到學校要求的。因為在接到班主任和政教處的通知后,張悅已經三次理發,說明盡管她不情愿,也還是盡量按照班主任和政教處的要求去做了。
一厘米的頭發長度,與一個鮮活的生命孰輕孰重?學校的學生管理規定是靜止性的、冰冷無情的,大家要遵守,但執行的時候得有“弱者思維”,執行行為應該是溫柔的、有暖意的。因為我們的執行對象是學生,對他們不能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無論怎么說,學生們留不合格發型也不違法,更不是不道德,最多是有不良行為習慣而已。
當一些政教管理規定只是出于學校的一廂情愿,并沒有和學生達成約定時,這算不算是一種教育冷暴力?我認為,一個學校管理者在執行這些規定的時候,應該堅守教育良知,掌握好“一厘米主動權”,既保持校規校紀的嚴肅性,又維護學生的權益。
五
學校管理者不光自己要把握好“一厘米主動權”,還要引導班主任把握好“一厘米主動權”,畢竟班主任是學校政教管理制度的落實者。換言之,學校的政教管理是個什么形象,學生是通過班主任感知的。
一個學校管理者,應該經常沉到班級中,向學生了解班主任的政教管理規定的執行情況。在調研后,整合各種信息,有效調控各位班主任政教管理規定的執行情況。
六
在柏林墻被推倒前的兩年,東德一個名叫亨里奇的守墻衛兵,開槍射殺了攀爬柏林墻逃向西德的克里斯·格夫洛伊。柏林墻被推倒、德國統一后的1992年2月,柏林法庭審判了此案。亨里奇的律師辯稱,亨里奇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因此,亨里奇是無罪的。但是,法官西奧多·賽德爾不這么認為,他當庭指出: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沖突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原則。最終,衛兵亨里奇被判處三年半的徒刑,且不能假釋。
西奧多·賽德爾站在人性高度的審判既合法亦合情,堪稱經典。
面對復雜的社會環境,任何人都不能以“服從命令”“嚴格執行制度”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倫理底線。以此類推,作為一個學校管理者,應該在特殊的一剎那堅守教育良知,不能以任何借口超越人性善良的底線,不能用過于細致甚至嚴苛的制度及執行去限制學生本應擁有的生命自由。
執行正確、科學的校規需要把握好“一厘米主動權”,執行不合理的校規更要靈活把握。在那些不合情且侵犯學生權益的校規校紀還沒有被廢除、還需要執行時,學校管理者應該堅守教育良知,運用自己手中掌握的“一厘米主動權”,盡最大可能保護學生,不讓他們受到校規校紀的傷害。
(本欄責編 盧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