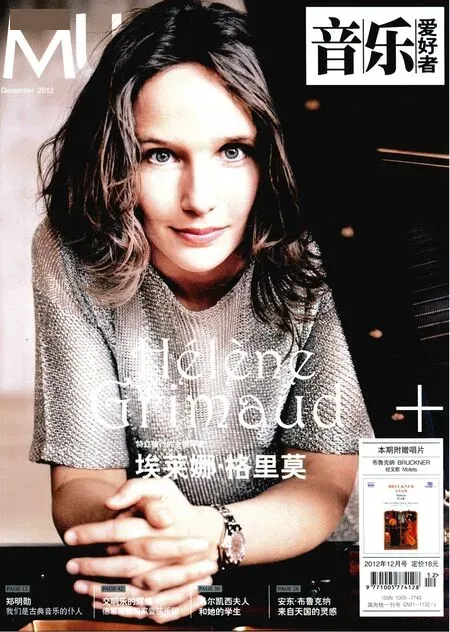鄭明勛:我們是古典音樂的仆人



那一晚在上海,指揮家鄭明勛燃起的激情,在音樂會結束后仍在持續燃燒。
近午夜十二點了,酒精使他的臉色微微泛紅,一向寡言的鄭明勛,亢奮之情全寫在了臉上。他的太太在一旁感到甚奇,似乎他要把幾年中沒說的話說完。“有時候演出順利或者很棒,我就感覺自己像在飛一樣。”顯然,此時他在“飛”。
2012年,鄭明勛執棒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在上海東藝連演兩場音樂會。見多識廣的上海樂迷,以理性的音樂熱情和良好的音樂素養,擁抱了他們喜愛的指揮家,以及有著一百二十四年歷史的國際樂壇的老牌勁旅。
韓裔指揮家鄭明勛為上海之行感動了。感動他的,不僅僅是璀璨靈動的上海的夜晚,還有鐘情于“世界語言”的中國聽眾。十五年前,當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的“敲門聲”在他棒下剛響起,觀眾席上立即爆發出不合時宜的掌聲。“現在的中國,與我十五年前感覺中的中國不一樣了,它發展得非常快。這種發展包含著觀眾對音樂的理解、音樂的氛圍等等。”指揮家舉著酒杯對東藝總經理林宏鳴說:“這是我幾十年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場音樂會。”
繼小澤征爾、祖賓·梅塔后,鄭明勛是當今國際樂壇又一位聲譽顯赫的亞裔指揮家。他謙卑的個性以及凌厲與細膩的雙重指揮風格,令世界上許多樂迷著迷。在上海凱越酒店,鄭明勛接受了我的采訪。
“明年,我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指揮家”
身著休閑裝的鄭明勛,上午準時出現在暖氣十足的咖啡廳里。盡管少小離開韓國,長期生活在美國與歐洲,鄭明勛的血管里依然流淌著韓國人的文化血液。從八十五層高樓往下望去,一覽眾山小,恢宏景觀盡收眼底。他收回凝視的目光,一臉輕松愜意。
個子不高的鄭明勛,或許因為長期腦體結合,始終保持著勻稱身材,相比之下,腦袋顯得有點大。臉上常帶有些許威嚴,不經意間流露出一種內在的控制力。正是這種控制力,能將世界上各種百十號人的樂團“焊接”在一起,在瞬間爆發出同一種音響。
“我們是同齡人,相信會有不少共同語言。”
他微微一笑,友好地向我伸出手。那一瞬間,我感覺到了他的謙卑。在國際樂壇,鄭明勛的謙卑出了名。他不像一些被寵壞了的大牌,自以為是,凌駕于音樂之上,更多時候,他將自己看作是音樂的仆人與傳遞者。在采訪進行時,有人很不知趣地走過來打斷采訪,要求與他合影,他竟欣然說了一聲“OK”!
●-施雪鈞○-鄭明勛
● “印象中,你來中國很多次了。”
○ “哦,我記不清了,可能有十來次吧。可到上海次數并不多,主要是去北京。”
● “你和你姐鄭京和在中國很出名,樂迷人人皆知。你有一張唱片人們很感興趣,是德國DG公司錄制的《卡門》,我就非常喜歡。你幾乎指揮過世界上所有的一流樂團,與哪些樂團合作,你覺得很順手?
鄭明勛眼睛一亮。也許提問中某些恭維的成分起了作用,他不茍言笑的臉上,浮現出微微的笑容。一開口,便不加停頓地將所問問題說完。
○ “我比較喜歡法國的樂團,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我指揮最多的是意大利斯卡拉樂團,還有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樂團形式。”
● “幾年前在上海,我聽過你指揮法國廣播交響樂團的一場音樂會,演出的是柏遼茲作品。而今這兩場音樂會,你卻帶來了大量德奧作品,這是為何?另外我還聽說你與荷蘭皇家愛樂的合作,能產生出某種‘化學反應?”
○ “對我來說,我所學最基礎的,是德奧風格的東西。此外,德國作品更能表現出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的實力與風格,他們樂團演奏德奧作品更好。我們合作由來已久,自從二十五年前開始第一次合作后,我對這個樂團的了解變得越來越深刻。
“美國一些交響樂團,雖然技術很出色,但是他們缺少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溝通,或者說是情感的交流,這就是為什么我與美國樂團合作較少的原因,他們給我印象只是純專業上的東西。而美國與歐洲樂團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歐洲樂團直指音樂的本質——人性。
“對音樂來說,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它是人類情感的一種表達。所以,我特別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與溝通。指揮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指揮,應更多地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之上。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們的音樂,不只是炫耀自己有多么的出色,而是體現出一種人文的關懷與人文的溫暖。”
● “人們很欣賞你的指揮風格,氣勢凌厲,明快細膩,毫不拖泥帶水,與歐洲一些指揮大師很相像。你是否意識到,你年輕時的風格與現在有變化?”
○ “你說我的風格,事實上我自己并不知道。但是,一定會有差別。年輕的時候,我注重的是肢體語言,而現在卻更注重簡單,藝術越趨向高級,就越簡單。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指揮,我可以教你,一分鐘就教會。”鄭明勛幽了一默,“我覺得,指揮非常簡單,每個人都可以很快學會,但要指揮得好,卻不是件容易的事。”
鄭明勛太太曾調侃地說,他的指揮,有四種手勢:舉棒不動、兩拍子左右晃、三拍子畫三角和四拍子畫方塊。可鄭明勛指了指胸口,對我比劃了一個圓圈。他說,這是他長期職業生涯中悟到的第五個手勢——畫圓。“畫好這個圓,是我一輩子追求的目標。事實上我學指揮時,整整三十年時間里,學的只是指揮的基本技術,直到現在,我才有了圓的概念。”
他說的這個“圓”,就是指音樂的本質。而本質的東西很不容易得到。
“我致力于指揮風格回歸簡單與原始。我還沒有到達那種境界,真的沒有!但是我很努力,我只是開始。”鄭明勛謙遜地說,“再過一年,我就可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指揮家了,因為國際樂壇有明確劃定,六十歲前,人們通常稱之為年輕指揮家,到了六十歲,才能成為真正的指揮家。”
“我只是音樂的仆人和傳遞者”
在外人看來,指揮在神圣籠罩下工作。他必須是個強勢人物,他越強悍,就越容易被下屬稱為專制。他只有伸出手,才能讓人聽話。他不能容忍任何異議,他的意愿,他的話語,他的每一次掃視,就是法則。
鄭明勛則不然。他威而不怒,充滿著東方人情味。他以出色的掌控力以及與樂團合作“融洽到可以產生化學反應”的能力,贏得了國際樂壇的親睞。
三十三歲那年,鄭明勛就擔任了法國巴士底歌劇院藝術總監的顯赫職位,五年后離任時,他的身價已高達九百萬法郎。之后,他擔任法國廣播交響樂團音樂總監長達十年。盡管藝術無國界,可鄭明勛卻以一個東方人的身份,牢牢立足于西方音樂界并贏得尊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0年,他開始在美國、歐洲各大知名樂團擔任音樂總監兼指揮,他一個接一個地面對嚴峻挑戰直至成功。面對一個新指揮,一個樂隊只要花上十五分鐘時間,便可得知他是個例行公事的排練廳里的說教哲學家呢,還是一個優秀的指揮家。而今,鄭明勛已經成為柏林愛樂樂團、倫敦交響樂團、倫敦愛樂樂團等世界一流樂團的座上客。
鄭明勛把這一切歸功于音樂的本質。
“現在我做音樂,更多地是表達一種禪意,即靈魂的釋放,境界的提升。音樂就是讓人們釋放自由的靈魂。所以到后來,指揮時就不會有那么多肢體動作。我很幸運,我有音樂這樣一個載體。所以,我覺得演出順利或者很棒的時候,我就感覺自己像在飛一樣。”他接著又說,“對于音樂家來說,終其一生,都在挖掘聲音。就像鋼琴家,不僅僅是敲擊出聲音,而是把內心的聲音挖掘出來,挖掘得越來越深,然后將其釋放,這就是音樂家的工作。
○ “所以我覺得,在亞洲,特別是在中國,普及古典音樂非常必要,因為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富有、快樂,人們做的所有事情,都與快樂有關,而音樂可以釋放他們自由的靈魂。”
● “你性格內向,沉默寡言,你是用什么方式與不同國家的樂團合作的?聽說早年歐洲有些樂手用各種方式考驗你,你與柏林愛樂合作時,還曾有過不愉快的經歷?”
○ “雖然我的性格孤僻寡言,但在指揮臺上,你可以認為我是法國人,或是意大利人和美國人。因為我在指揮不同樂團的時候,我不知不覺就擁有了那個國家人民的性格。無論是演奏家還是指揮家,我們只是個傳遞者,傳遞那些偉大作曲家的聲音。所以不管你是德國人還是美國人,我們在演釋時沒什么區別。這一點,很多人還沒明白。在韓國,有許多人說,你是個韓國人,為什么演釋這樣的音樂?為何音樂可以放在民族之前?我對他們說,我相信音樂的偉大,在作為韓國人之前,我覺得有更偉大的事情要做;比如我們在奧運會上,人們想到的是為國家而贏,競爭尤為激烈,但音樂更多是使世界變得和諧,生活變得美好,因此,音樂比民族更重要。去年我指揮朝鮮樂團時,因南北韓長期存在著政治沖突而有些尷尬,但令我欣喜的是,當第一個音符奏響時,所有的沖突及戰爭的陰影似乎都不存在了,這就是音樂的魅力所在。于是我給自己定位,首先我是個人,我們都是平等的;其次我是音樂家;再次我是個韓國人。
“我們必須認識到,偉大的藝術家將人類音樂遺產一代代傳承下來,我們所做的,只是在傳遞他們的音樂;我們的工作,只是服務于偉大的作曲家、藝術家。對他們來說,我們只是傳遞者、服務者。我之所以會來這里,是因為我在傳遞這些音樂。”
● “非常好,很多年來,我第一次聽到你這么理解音樂。現在有一些演奏家,凌駕于音樂之上,覺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而你把自己看作一個世界公民,音樂從不帶有政治因素,它沒有國界,音樂與哲學至高無上。”
○ “是啊,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不一樣,你看麥當娜,人們不可能從她音樂中得到些什么,她只是在展現她自己。古典音樂就不同了,它展現的是音樂,是偉大作曲家的思想。所以,無論是中國、韓國還是荷蘭音樂家都一樣,他們都是仆人和傳遞者。這就是我為何鐘情于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的原因,因為他們是一個非常好的‘仆人,他們謙卑地將自己放在了偉大音樂家之下。這猶如交朋友,有些人一看就很耀眼,系一根漂亮的領帶,各方面都很體面;有些人長相很一般,但是你與他交流,覺得他的心、他的靈魂,有非常豐富的內涵,我們愿意與這樣的人交朋友,目的是想成為這樣的人。
“所以我以為,柏林愛樂與維也納愛樂的不同之處在于:柏林愛樂非常宏大,有著威嚴嘹亮的聲音,像一個強壯的男人;維也納愛樂像個美麗的女人,有非常嬌美的面容;而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愛樂就是你越聽越想聽的一支樂團。這是我能說的最好的贊美了。”
“我在尋找一種合適的方式回饋社會”
“總有記者問我的夢想是什么?通常我都不愿回答。我從小成長到現在,就一直生活在我的夢想中。但有一件事我一直在做準備。在我生命最后的一段時間里,我要做的,就是幫助別人。而我最能做的,就是幫助年輕的音樂家。當然我希望能幫助更多的人。”
鄭明勛有著東方人虛懷若谷的胸懷與智慧,盡管他不太認同他有“東方人的智慧”一說。無可否認的是,他對藝術觀的闡述更直接,更現實,頗有中國的老莊之風。在我以往的采訪中,似乎沒有哪位中外音樂家說得如此透徹。
有評論認為,“如果說,指揮大師阿巴多組建的琉森節日管弦樂團是歐洲的全明星隊的話,那么,鄭明勛在1997年創建的亞洲愛樂樂團,則是亞洲音樂的‘夢之隊。當中國觀眾看到一支由黃皮膚音樂家組成的交響樂團表現出完全不遜于歐美一流樂團的水準時,便產生了無法抗拒的親近與自豪感。”
● “你在1997年創立了亞洲愛樂樂團并多次來中國演出。創建這個樂團有什么寓意嗎?是否想提高亞洲交響樂團的總體水平?
○ “我的初衷很簡單,就是想把亞洲的音樂家整合在一起。因為有一些國家之間關系很緊張,去年我們在北京演出時,這支樂團中有三分之一是日本人,三分之一是韓國人,三分之一是中國人。他們都來自芝加哥交響樂團、費城交響樂團、紐約愛樂樂團、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等歐美知名交響樂團。當音樂響起后,你已經無法分辨這是哪國人,看上去就是一家人,這很棒!接下來,我希望朝鮮音樂家也能加入進來,也像一家人那樣其樂融融,因為我們都是古典音樂的仆人。”
● “在亞洲,像小澤征爾這樣的指揮家太少了。”
○ “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好指揮確實越來越少了。你看世界上優秀交響樂團越來越多,可指揮界卻出現了斷層,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一個樂手不稱職,影響的只是一個聲部,但如果一個指揮不稱職,能夠使整個樂團垮掉。指揮的工作就是這么危險。
“過了六十歲,我可能會降低演出頻率,因為我有更多的事要做,那就是發掘更多的年輕藝術家并培養他們。”
“鄭門三杰”出了一個“專業廚師”
鄭明勛出生在韓國首爾,父親是一個律師,還是一個十足的音樂發燒友。正是由于父親的愛好與影響,他的家庭中彌漫著濃郁的音樂氛圍,兄弟姐妹七人中,后來竟然有六人成為職業音樂家。
鄭明勛的大姐鄭京和,是二十世紀中后期世界上最優秀的小提琴演奏大師之一;二姐鄭明和,成為大提琴演奏家;哥哥是單簧管演奏家。因此將他的家庭稱作“音樂家的搖籃”毫不過分。
為了孩子們的成長,鄭明勛的父親毅然放棄了律師職業,在他八歲時,舉家移民至美國西雅圖。十六歲前,鄭明勛是自家韓國料理店的業余“小伙計”“小廚師”。十六歲后,他被意大利美食所吸引,選擇去意大利求學。
鄭明勛常常念及家庭對他的影響。“有人問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學習音樂的,我告訴他:始于胎教。我未出生時,就在娘胎里天天聽姐姐們演奏音樂了。在家做料理時,我是廚師;做音樂時,我是一個服務生,把別人做好的音樂‘端出來。”
鄭明勛姐弟們的健康成長,得益于父母的開明教育。放棄律師執業后,從不下廚的父親竟然學成了個好廚師。他的父母從小讓孩子們學習音樂,卻從來不強迫他們練習,在音樂上也不替他們做決定,任其自然成長。所以當大女兒鄭京和放棄鋼琴選擇小提琴、二女兒鄭明和選擇大提琴時,父母都是竭力地支持,而鄭明勛選擇了鋼琴,之后又轉行學指揮。他們姐弟的成功,證明了父母在教育上的明智。
有趣的是,在開始職業音樂生涯之前,鄭明勛更鐘情的“職業”竟然是廚師。這個美食家,幾年前還親自撰寫了一本有關韓國家庭料理的菜譜。時至今日,只要他在家里,廚房基本上就是他一個人的天下。他說,“在烹飪上,我有‘神童般的天賦。除了指揮臺,廚房是讓我感到最愜意的地方。無論什么原料,到我手里很快就能做出來。”
這樣的家庭經歷,像個美麗的傳說,令人羨慕。
● “一個家庭出了三個音樂大家,被稱為‘鄭門三杰,令人仰慕。我聽說你們姐弟的三重奏聞名于國際樂壇,將來有機會來中國演出嗎?那一定會很轟動!”
○ “不太可能,去年,我們姐弟搞過一場三重奏,那是為逝去的母親舉行的一場追悼音樂會。我們三人都很忙,聚會都很難,我則更多地將精力放在指揮上。當然,這不是不可能,只是幾率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