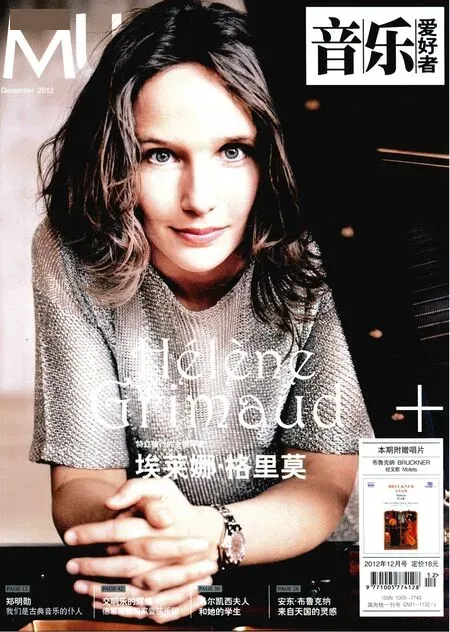安東·布魯克納和他的經文歌
徐樂娜
1824年,安東·布魯克納出生在奧地利林茨附近安斯菲爾登村莊的一個教師家庭。父親過世后,布魯克納進入圣弗洛里安修道院,成為一名唱詩班歌手。三年后的1840年,他前往林茨接受教師培訓,并先后到遙遠的溫特哈格(Windhaag)及科隆施托夫(Kronstorf)當老師。1845年,布魯克納終于成為圣弗洛里安的一名教師,并于六年后受聘為管風琴師。
自兒童時期開始,布魯克納便對各類音樂有所接觸和了解,圣弗洛里安為他提供了更多聆聽偉大宗教作品的機會,而他自己的早期作品也絕大多數為教堂而作。在朋友的建議下,布魯克納前往維也納向西蒙·塞西特(Simon Sechter)拜師學藝,并接受其建議辭去了圣弗洛里安的職務。1855年,布魯克納終于成為林茨大教堂的管風琴師。與先前相比,這里的宗教及世俗音樂曲庫可謂“豐盈富足”,讓他受益匪淺。
1861年,布魯克納完成了對位法的學習,跟隨林茨大提琴家、指揮家基茨勒(Otto Kitzler)學習管弦樂配器及曲式等作曲法。不久,瓦格納的《湯豪塞》在林茨上演,這對布魯克納而言無疑是一次強烈的沖擊。他對交響樂的創作熱情高漲,并于1864年譜寫出《D小調交響曲》。然而,這首作品并沒有得到認同,甚至被評價為“言之無物、微不足道”,它的“零”編號便是個饒有意味的佐證。此后,布魯克納開始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彌撒的創作中,并譜出了三套大型彌撒作品。直到1868年,由于收入等多方面的原因,他轉到維也納音樂學院任教。
來到維也納之后,布魯克納過得并不順心,甚至是麻煩不斷,而起因皆源自他對瓦格納的崇拜。樂評家漢斯立克對他的敵意更是不加掩飾,即便勃拉姆斯本人在聽過布魯克納的作品后表示認同,這位勃拉姆斯的捍衛者依然一度設置障礙,不讓布魯克納來維也納音樂學院任教。此外,維也納愛樂樂團也一度拒絕演奏他的交響樂作品。種種挫折讓布魯克納自信不滿,常常修訂自己的作品,以至于今天我們會看到他的交響樂存在好幾個版本。布魯克納的余生幾乎都在維也納度過,而他也最終未能沖破“九”的魔咒。1896年,在完成了《第九交響樂》的最后樂章后,布魯克納離開了人世。
自始至終,謙遜的性格伴隨著布魯克納的一生,而這應該歸因于他對宗教信仰的堅定與虔誠。盡管對即興創作的擅長讓他的交響樂創作受益匪淺,但宗教作品更是顯現其音樂天賦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從1842年在溫特哈格創作的彌撒套曲,到1884年輝煌宏大的《感恩贊》(Te Deum),布魯克納投入其中的心血幾近一生。
為配合禮拜儀式的需要,布魯克納寫過很多短小的作品。1879年,為醫生教會而作的《公正的話》(Os justi)正是其中之一。這是一首利底亞調式的升階經,以“哈利路亞”結束,當時被題獻給伊格納茨·特勞米勒(Ignaz Traumihler),圣弗洛里安的唱詩班指揮,亦是倡導教會音樂改革的塞西利運動的擁護者。正如布魯克納給特勞米勒的信中所說,遵循教會音樂改革的要求,《公正的話》中沒有使用變化音,沒有使用七和弦、六四和弦等等。
1869年,在南希(Nancy)的一場小型音樂會讓布魯克納有了國際知名度。巴赫作品的演奏及現場的即興表演不僅為他贏得滿堂喝彩,更使他得到了來自巴黎圣母院的盛情邀請。亦是因為這次機會,布魯克納開始被弗朗克(Cesar Franck)、圣-桑等著名音樂家關注。題獻給奧托·勞伊多爾(Otto Loidol)神父的升階經《此乃神的殿堂》(Locus iste)正是在這一年完成,其中的模仿式復調段落尤其出彩。
圣佛洛里安的副院長阿爾內特神父(Michael Arneth)應該算是布魯克納的貴人。正是他在布魯克納父親去世后,將之收入修道院成為一名唱詩班歌手,亦是他將身處溫特哈格郁郁寡歡的布魯克納安排到科隆施托夫,繼而回到圣弗洛里安。可以說,阿爾內特是布魯克納音樂人生的引路人。1854年,阿爾內特與世長辭,葬禮上的音樂正是布魯克納為他譜寫的《拯救我》(Libera me)和《在阿爾內特的墳前》(An Arneths Grab)。這兩首經文歌皆為男聲合唱和為三把長號而作,亦可由長號和管風琴等莊重肅穆的樂器來演奏。
七部無伴奏合唱《圣母頌》(Ave Maria)創作于1861年,5月12日首演于林茨,當時的布魯克納正是大教堂的管風琴師。音樂的第一樂句首先由女聲引入,第二樂句由男聲對答。隨著力度的漸強,“耶穌”被一聲聲呼喚,緊跟其后的是聲部間的模仿對位。全曲樸實清新,充滿著虔誠圣潔的氣氛,其中的對位技巧更是精妙高超。
創作于1885年的《第九號前奏曲》(Ecce sacerdos)是林茨教區千年紀念的獻禮之作。這首圣歌在合唱之外特別設計了長號和管風琴的加入,各聲部間和諧融洽。全曲的結尾同樣采用了半音式進行,與樂曲的開頭交相輝映。可以想象,在教區的千年慶典上,如此豐滿恢弘的音響震撼到多少人的靈魂。
為耶穌受難日而作的《王的旗幟》(Vexilla regis)完成于1892年,是布魯克納的最后一首經文歌。這首贊美詩平和舒緩、引人沉思,結束的一句“阿門”氣若吐絲,神安氣定。
1884年可謂布魯克納的豐收年。首先是《第七交響曲》在萊比錫首演獲得巨大成功,指揮尼基什(Nikisch)和布商大廈管弦樂團是這個重要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感恩贊》亦在這一年完成,而《拯救你的人民》(Salvum fac populum tuurn)再次袒露出他對音樂的摯愛和對信仰的虔誠。這一年,布魯克納六十歲。
奉獻經《心中之王》(Afferentur regi)創作于1861年。此時的布魯克納還未跟隨塞西特學習,其對位法的寫作技藝自然也略顯生澀。這部作品包含四個聲部,在將樂曲推向高潮的部分,布魯克納特別安排了三個長號聲部作為補充,以此讓全曲進入頂點之際錦上添花。
完成于1868年的《贊美的語言》(Pange lingua)采用弗里幾亞調式,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賽西利運動對教會音樂提出的一些約束和限制。十年之后,為慶祝林茨大主教魯迪杰爾(Bishop Rudigier)上任二十五周年,布魯克納譜寫了圣歌《瑪利亞,你為美麗無瑕》(Tota pulchra es Maria),題獻給這位生命中的又一位貴人。音樂在男高音獨唱與合唱的對話間進行,管風琴嚴謹而精準的持續音莊重沉穩,給樂曲不斷注入生機與動力。
《枝頭花朵凋零》(Virga Jesse)作于1885年,亦是題獻給特勞米勒的作品。這首升階經和《第九號前奏曲》完成于同一年,樂曲中強烈的對比、急促的停頓等極具戲劇性的手法,讓人感受到無窮的力量。結尾部分,樂曲趨于平和,管風琴的低音E在人聲之下構成堅厚踏實的基石。
奉獻經《大衛王降臨》(lnveni David)與《贊美的語言》創作于同一年,為男聲和四把長號而作。樂曲由F小調開始,在“哈利路亞”中以凱旋的F大調結束。贊美詩《黑夜隱去,白晝已到來》(Iam lucis orto sidere)則再次采用了弗里幾亞調式。
《皇皇圣體》(The tantum ergo)用于祈求上帝的賜福儀式,歌詞選自《贊美的語言》。這首包含五個聲部的D大調合唱曲的誕生并不順利,從1846年至1888年,四十多年間被布魯克納多次擱置一邊。
升階經《主耶穌的順服》(Christus lactus est)完成于1884年,同樣題獻給勞伊多爾神父。布魯克納在譜上標記的是“神秘的中速”。四聲部由同音齊唱引入之后,立刻以對位進行推動音樂發展。隨著聲部間的張力蓄積,樂曲在一層層聲浪中被推向頂點,而低聲耳語的結束句,與高潮段落形成極大的反差,更帶來強烈的戲劇化的聽覺感受。
圣布萊德教堂合唱團
Choir of St. Bride's Church
作為新聞工作者們的教堂,圣布萊德教堂一直為人熟知,而它所處的位置正是以前的新聞界中心、倫敦有名的艦隊街(Fleet Street)。圣布萊德教堂合唱團經常得到新聞界的捐贈,盡管倫敦的新聞產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媒體人依然把教堂視為他們的精神家園,也一如既往地給予教堂支持。
1958年,因戰亂而中止的圣布萊德教堂合唱團重振旗鼓,由戈頓·雷諾茲(Gordon Reynolds)擔任指揮。合唱團組建之初的編制一直維持至今,目前他們擁有十二位成年的專業歌唱家。除為新人提供婚禮音樂、紀念儀式等現場服務之外,每周日教堂的雙合唱團唱詩是他們最為重要的工作內容。
羅伯特·瓊斯
Robert Jones
1988年至今,瓊斯一直擔任圣布萊德教堂合唱團的指揮。他早年在牛津基督教堂學院跟隨大衛·約翰斯頓(David Johnston)學習聲樂,跟隨尼古拉斯·丹比(Nicholas Danby)學習管風琴,并獲得音樂獎學金。在校期間,他還是西蒙·普雷斯頓(Simon Preston)麾下的教堂唱詩班中的一名合唱歌手。十六歲時,他便得到了第一份職業——管風琴師。畢業后,瓊斯在溫莎公園內的圣喬治禮拜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擔任唱詩班的領唱。與此同時,他亦十分喜愛合唱團歌手的角色,與塔利斯學者合唱團(Tallis Scholars)、奧蘭多合唱團(Orlando Consort)、加布里耶利合唱團(Gabrieli Consort)的合作尤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