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競業限制”風險提示
李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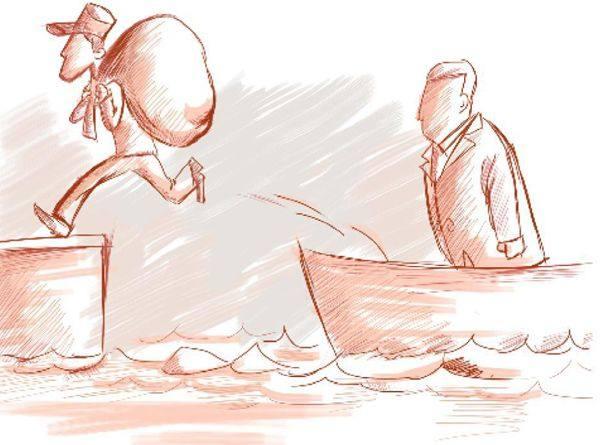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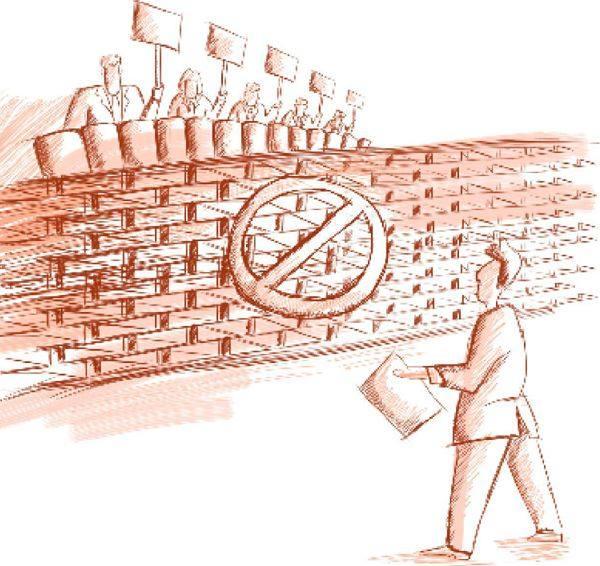
競業限制,對于企業以及人力資源管理者來講,早已不是陌生詞。自《勞動合同法》實施以來,競業限制已經揭去了它朦朧的面紗,對其相關的規定在法律層面上也有了較為清晰的指引。但是,現行的法律法規只在整體上對競業限制進行了把握與限定,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有很多細節需要通過勞資雙方自由協商來實現。
一個完善的競業限制管理制度,一份高質量的競業限制協議,不僅能夠為建立規范、和諧的用工機制提供有力支撐,還能有效降低勞動爭議頻發的風險。如何設置行之有效的制度體系,維護企業和員工的合法權益,避免重點人才、關鍵崗位員工流失后給企業帶來的經濟損失和風險,是每一個企業都應當關注的關鍵問題。
【案例】
2007年7月1日,A公司與張某簽訂了《競業禁止協議書》,約定張某在職期間及離職后24個月的競業禁止事項,公司每年補償張某5000元,補償金的支付方式為競業禁止期滿后一次性發放。如張某違反競業禁止協議書,則應支付公司違約金10000元。張某在職期間月工資為20000元。
2009年12月1日,張某離職后第二天就注冊了與A公司有業務競爭的公司,2010年2月被A公司發現并提起勞動仲裁,要求張某賠償經濟損失100萬元,但至提起仲裁時,A公司也未向張某支付競業禁止經濟補償。
【案件點評】
本案涉及三個問題:第一,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支付方式。第二,競業限制補償金的支付標準。第三,若用人單位未支付補償金,競業限制協議是否有效。
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支付方式
《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三條明確規定了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支付期限,具有強行法的性質。出于對保護勞動者權益的考慮,用人單位應依法在解除勞動合同后、競業限制期滿前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否則視為約定無效。本案中,A公司在與張某簽訂的《競業禁止協議書》中,約定經濟補償金的支付期限為“競業禁止期滿后”,該約定顯然不符合《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故此,該約定應為無效,A公司依然應依法在競業限制期內支付經濟補償金。
競業限制經濟補償的支付標準
有關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標準,《勞動合同法》并沒有明確規定統一的標準。盡管某些省市通過地方性法規對其進行了一定規定,但規定各有不同:
《北京市高院關于勞動爭議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紀要》第三十九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的,經濟補償可按照雙方勞動關系終止前最后一個年度勞動者工資的20%-60%支付補償費。《中關村科技園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向負有競業限制義務的員工按年度支付一定的補償費,補償數額不得少于該員工在企業最后一年年收入的二分之一。
《上海高院關于適用<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三條規定,勞資雙方就補償金數額約定不明的,雙方可以繼續就補償金的標準進行協商;協商不能達成一致的,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勞動者此前正常工資的20%-50%支付。
《江蘇省勞動合同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用人單位支付勞動者的競業限制年經濟補償額不得低于該勞動者離開用人單位前十二個月從該用人單位獲得的報酬總額的三分之一。
《浙江省技術秘密保護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競業限制年度補償費按合同終止前最后一個年度該相關人員從權利人處所獲得報酬總額的三分之二計算。
《深圳經濟特區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競業限制協議約定的補償費,按月計算不得少于該員工離開企業前最后十二個月月平均工資的二分之一。
雖然上述地方法規為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標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但是由于地方法規的空間效力,使其只適用于轄區范圍內,對于轄區以外的省市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而實際中,大部分省市因為沒有經濟補償方面的立法規定,勞資雙方更多依賴的是自由約定,這也為司法實踐中的具體操作造成了很大障礙。而前不久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勞動合同法司法解釋(四)》的第十二條對競業限制補償底線做出了明確規定,要求經濟補償數額不得低于勞動合同履行地上年度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用人單位未支付補償金,競業限制協議是否有效
用人單位不按約定支付經濟補償,自然屬于違約行為。但是,用人單位的違約行為是否導致競業限制協議的無效呢?勞動者是否還需要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呢?
首先,從基本法律理念上來說,經濟補償是勞動者履行競業限制義務的等價補償,是用人單位履行其合同義務的一種表現形式,任何時候權利和義務都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用人單位未支付經濟補償而要求勞動者履行競業限制義務必然得不到法律支持的,因此,如果用人單位不支付或者沒有正當理由拖欠經濟補償,應當認定競業限制對于勞動者的約束是無效的,勞動者就不再承擔相應的義務了。
其次,從法律規定上說,《勞動合同法》并沒有對此種情況進行明確的規定,只有一些地方法規、規范性文件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做出了一些規定:
《上海高院關于適用<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三規定,勞動合同當事人僅約定勞動者應當履行競業限制義務,但未約定是否向勞動者支付補償金,或者雖然約定向勞動者支付補償金但未明確約定具體支付標準的,基于當事人就競業限制有一致的意思表示,可以認為競業限制條款對雙方仍有約束力。
《江蘇省勞動合同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用人單位未按照約定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的,約定的競業限制條款對勞動者不具有約束力。
《寧波市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和《珠海市企業技術秘密保護條例》規定,企業違反競業限制協議,不支付或者無正當理由拖欠補償費的,競業限制協議自行終止。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關于適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二十六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的,應當在競業限制期限內依法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用人單位未按約定支付經濟補償的,勞動者可要求用人單位履行競業限制協議。至工作交接完成時,用人單位尚未承諾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的,競業限制條款對勞動者不具有約束力。
在國家法律層面沒有統一的規定時,各地區仍要依據各地已出臺的規定進行具體操作。
【案例】
2005年3月,李某入職某自動化公司并擔任該公司銷售部經理,2010年與公司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并簽訂競業限制協議作為勞動合同附件。協議約定:合同解除或者終止后2年內,李某不得到與本公司生產或者經營同類產品、從事同類業務的有競爭關系的其他用人單位任職,或者自己生產經營同類產品、從事同類業務。單位將自李某離職之日起每月支付競業限制補償金3000元。
2011年11月,因公司對李某的處罰導致雙方產生沖突,雙方于2012年1月解除了勞動合同,公司按協商額度支付了經濟補償。2012年6月,李某發現工資卡里面已經有2個月沒有收到補償金,隨即打電話催要,但仍然沒有收到補償金,公司也沒有給出任何說明。李某于7月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申請,要求公司補發拖欠的2個月競業限制補償金,并按照競業限制協議的約定繼續履行義務。
【案件點評】
用人單位是否可以單方解除競業限制協議
根據《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用人單位按照競業限制約定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后,支付勞動者經濟補償。勞動者違反競業限制約定的,應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由此可見,法律上規定了勞動者的違約責任,卻沒有規定用人單位的違約責任。因此,實踐中勞動者在用人單位違約的時候只有解除競業限制協議的權利,而沒有向用人單位追償損失的權利。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等三部門《印發關于適用〈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勞動合同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用人單位未按照約定支付經濟補償的,勞動者可以要求用人單位履行競業限制協議,支付經濟補償。自工作交接完成后滿1個月,用人單位尚未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的,勞動者可以不受競業限制協議的約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指導意見》第十三條規定,企業在競業限制屆滿前已通知員工解除競業限制條款,員工請求企業繼續履行競業限制條款并支付經濟補償的,不予支持。
基于上述表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企業具有單方解除權。如企業行使單方解除權,勞動者則無需承擔競業限制的義務。
【案例】
王某于2006年9月入職A保險公司,擔任華南地區銷售經理,勞動合同期限為兩年,入職時公司在與王某簽訂勞動合同的同時,要求與王某簽訂一份《競業限制協議》,協議中約定王某在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后兩年內不得加入與A公司存在業務競爭關系的其他公司。王某的月收入為10000元,其中1000元為競業限制補償金,按月與工資同時發放,如果王某違反了競業限制義務,將要按年薪的10倍向A公司支付違約金。后王某因工作上失誤主動提出辭職,并在離職后不久進入B保險公司。A公司因此訴至法院要求王某支付違約金120萬元,并要求B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案件點評】
競業限制的經濟補償包含在工資中進行支付的行為是否合法有效
《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對負有保密義務的勞動者,用人單位可以在勞動合同或者保密協議中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條款,并約定在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后,在競業限制期限內按月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根據該條款,競業限制經濟補償的支付應當在競業限制期限內即勞動者離職之后。對于上述案例中,A公司與王某約定在薪酬結構中包含1000元的競業限制補償金,并且在職期間發放。這種做法是否有效呢?
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法及實施條例解讀》一書中,對于《勞動合同法》第二十三條的解讀是:“競業限制補償金不能包含在工資中,只能在勞動關系結束后,在競業限制期限內按月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按此理解,A公司在支付工資同時支付競業限制經濟補償的做法是得不到法律認可的。
對此,《勞動合同法》規定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的用人單位“在競業限制期限內按月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應當是一種指導性規定,并不是強制性的。勞資雙方可以在自由、平等協商的前提下對競業限制經濟補償金的支付形式進行約定,且用人單位按此約定進行給付義務。當然,立法的意圖中也包含了防止“用人單位利用工資來代替補償費”的做法。但是,判斷用人單位的做法是否合法有效,應當以用人單位實質上是否對勞動者履行競業限制義務支付的對等的經濟補償,以及用人單位的行為是否損害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為評判標準。案例中,A公司與王某入職時即約定了王某的薪酬結構,明確10000元的收入中包括了1000元的競業限制補償金,即說明其實1000元的性質并不是勞動報酬而是競業限制補償金,這是雙方真實意思的體現,并不違法。而且A公司將本應離職后發放的經濟補償金提前發放,并沒有損害王某的權利。因此不能得出該行為無效的結論。但對于公司另一種做法應給予違法的認定,即:用人單位將原本屬于勞動報酬的一部分工資命名為競業限制補償金,或者競業限制協議中約定工資中已包含了競業限制補償金,而要求勞動者承擔競業限制義務的情形。
B公司是否要對A公司主張的違約金承擔連帶責任
對于勞動者后入職的企業是否對前企業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勞動合同法》第九十一條已做了規定,用人單位招用與其他用人單位尚未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勞動者,給其他用人單位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違反<勞動法>有關勞動合同規定的賠償辦法》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尚未解除勞動關系的勞動者,對原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除該勞動者承擔直接賠償責任外,該用人單位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其連帶賠償的份額應不低于對原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總額的70%。但是,通過上述條文不難發現,法律只針對用人單位招用未解除、未終止勞動關系的勞動者給原用人單位造成經濟損失的情形要求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而未對是否與勞動者連帶承擔的競業限制違約金做出明確規定。筆者認為,《勞動合同法》沒有做出此規定反而對勞動者個人起到了一定的震懾效果,勞動者自身去承擔違約金,要比與之后入職的企業連帶承擔更有心理上的壓力,也間接減少了勞動者抱有僥幸心理的違約行為,但是仍無法有效的杜絕“惡意挖墻腳”的行為發生。
因此,用人單位在招用新員工,特別是從事技術崗位的員工時,如果該員工向用人單位提供有關技術信息,應掌握其信息來源,審查該技術是否涉及原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進而保證依據該技術信息所取得的經濟利益并不是基于侵權行為而獲得,不存在被訴侵權的風險。除了設置相應的審查程序外,建議再與員工簽訂相關協議,協議中明確約定:員工在今后的工作中所提供的技術信息并不侵犯其他企業的經濟利益,或者明確員工在原單位已經度過離職前的脫密期。如因上述行為發生權利人對此的追訴,則由員工個人承擔民事責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