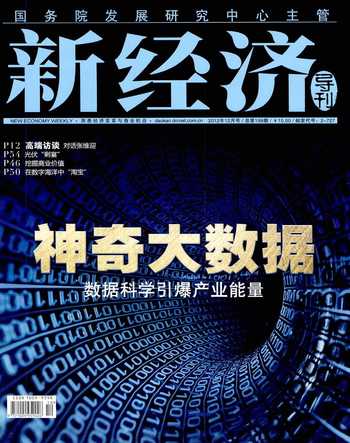中國改革“三步走”
吳敬璉
十八大以后,改革似乎在整個社會升溫。從領導到大眾對于今后的改革推進,都有很強的期待。但是我們現在第一步走出去之后,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就變成一個很迫切的問題。光是提出目標或者提出推進改革的口號,甚至下了這樣的決心,還是不夠的。我比照上一次大的轉折,就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的改革大推進,大概整體配套改革要走三步,我們現在僅僅走了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所謂目標模式的確定。現在說法叫“頂層設計”。
第二步是制定各方面改革的方案設計。根據各方面改革把它們之間的配套互動關系做出一個總體規劃,或者叫做行動的綱領。
第三步就是實施這個行動綱領。打破阻力把各項改革落到實處。
選擇目標
從上一次90年代初期一直延續到90年代末期,甚至到21世紀初期的這一次大推進來看,前面兩步都是做了相當深入的扎實的準備,所以,從1994年開始,這個改革從20世紀末期把市場經濟的框架初步建立了起來。
那一次改革大推進的發起人是鄧小平。在1990年12月在中央全會開會以前,他和主要領導人談話里面提到了我們應該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91年2月,在和朱镕基的談話里面再一次提出。在他兩次提醒以后,并沒有馬上就形成共識,而是出現了大家所知道的“皇甫平”事件,就是上海周瑞金和其他幾位同志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寫了四篇文章,提出要推進改革,但是馬上受到另外一種力量的反擊,于是展開了一場到底是計劃經濟為主、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場大爭論。
這個爭論中主流的媒體當時表現的是一種保守的傾向,但是支持改革的領導人和學術界、企業界、政界的許多支持改革的人們,就潛心進行研究:到底我們要一個什么樣的目標?這個研究和討論到了高潮就是1991年10月到12月,江澤民總書記召集了11次討論會,著重討論怎么搞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參加這個討論會的經濟學家里面,幾乎一致認為要建立市場經濟。這次討論會后,中央領導又征求了其他一些主要領導人的意見。到1992年6月9日準備十四大時,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的一次講話里面就說,現在對于我們要“選擇一個什么樣的目標”有幾種不同的意見,他自己傾向于把目標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且對市場經濟的特性做了解釋。大致上是講了兩點,一個就是市場經濟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另外一點市場經濟這個制度能夠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
這個講話以后,黨的高層沒有反對意見。在向鄧小平報告之后,決定在10月召開的十四次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定為我們改革的目標。這樣就把目標模式確定下來了。現在我們把它叫做“頂層設計”了。
重啟議程
在十四大確定了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并沒有停留在這個口號上,又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工作,參加這個研究的人數更多了,才在1993年11月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制定了一個當時叫做總體規劃,或者也叫做行動綱領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一共50條。
這個“50條”其實是一個總體的規劃。比如說財稅、金融,當時主要是銀行、國企、社會保障體系、外匯管理體制等重點方面的改革,而且規定了它們之間的配套,以及時間順序和配套關系。從1994年開始就執行這個總體規劃,執行過程中也有一些小的調整。后來就是在1997年十五大上又提出怎么改造,叫做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應該做什么樣的改革,特別是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
由于在該總體規劃下執行了這些改革的方案,我們就能在20世紀末期宣布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體制正是我們中國經濟能夠崛起的制度基礎。和這個相對比來說,看來我們現在就是需要進行第二步了。現在我們正在討論,十八大做出非常重要的決定,符合十八大前大眾的期望。
那么大眾對十八大的期望是什么?就是重啟改革議程,啟動我們改革的再出發。所以這個應該說是第一步,就是確定頂層設計的目標。既然1992年十四大已經確定了這個目標模式,也就是說確定了頂層設計,為什么又會提出要重啟改革議程,又要來討論頂層設計呢?這個原因是,大致上在21世紀以后,出現了新的爭論、新的不同意見,我把它叫做有另外一種頂層設計出現了。我們20世紀建立起來這個體制,它一方面打開了市場經濟、市場制度起作用的空間;它另外一方面又存在很多舊體制,就是命令經濟或者是統制經濟的遺傳。
做出決斷
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認識到了我們的體制還很不完善,還存在很多舊體制的遺傳,所以在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這個決議來看,我們生產力發展仍然存在很多體制性的障礙,所以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過,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執行,現在看起來不盡如人意。雙重體制的存在,使得有些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矛盾日益尖銳。
而怎么解決這個矛盾,就出現了認知問題。有的認為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對,它造成了腐敗兩極分化云云。按照這種意見的支持者,他們的想法就是應該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要強化政府,強化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這種趨勢顯得愈演愈烈,以至于一年以前可能到了最嚴重的地步。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傾向?有不同的說法,有人把它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有人按照我們東亞國家轉型的討論提出來,叫做威權主義的發展模式;或者有的人說得更嚴重一些,說這種趨勢是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趨勢。于是就出現了兩個頂層設計之間的爭論。
所以人們期盼十八大能對這個爭論做一個決斷,明確我們到底向哪個方向走。現在看來,十八大明確了我們到底應該選擇一個什么樣的方向。十八大重申我們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這樣就把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到執政黨的議事日程上來了,所以說第一步已經走出去了。
(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歡迎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