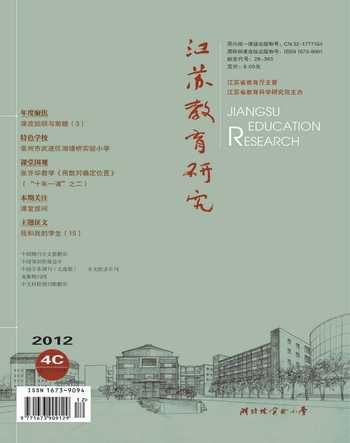小溪泛盡卻山行
有幸得以細品張齊華老師的兩節《用數對確定位置》,先是嘆服于第1版本中孩子們驚人的創造力,繼而又被課例2當中孩子們對規則的精準把握和精彩外延所吸引。再三把摩、沉思兩課細微之處,則不禁敬佩張齊華老師在這一異構過程中所傳達出的對學生的人本關懷以及對教學的不懈追求。躬逢美課,恰如游走于色彩斑斕之山溪美景,不免要生出色授魂與之感。乃強為置喙,恭疏短見于下。
一、改課,不改以學生為主體的目標
兩個版本課堂的最大不同,無疑在于:課例1當中的數學規則是在學生自己提出各種表達方式的基礎上總結得來的,是一種能被觀察者明確看到的建構;課例2則是由教師給出表示位置的數對,然后由學生統一內部的爭論,達到建立和掌握規則的目標,形式上似乎傾向于老的“教師主導型”課堂。
《增廣》云:“世事如棋局局新”,我們若將這句話中的“世事”換做“課堂”二字,想來也沒什么不貼切的。就這節教學內容而言,孩子的頭腦里必定都具有比新規則層次低的相關內容,但若說每一群、每一個孩子都可以自我建構起新的規則,恐怕不好定論。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會看到這形式上教師主導的第2課例。然而我最大的觸動卻正來源于第2課例。
布魯納指出:“兒童都有他自己的觀察世界和解釋世界的獨特方式。”實際上,就像課例1里面我們看到學生呈現的各式不同的數對(也許有孩子沒有呈現什么)一樣,不同的學生對新知識的建構在程度上是有差異的。但是我們可以設想,哪怕再不濟的孩子,他也總是知道“4和3是缺一不可的”,并非沒有絲毫的自我建構,只是不曾意識到他的“自我建構”,或是缺少這方面的經驗而已。而一個真正關注人的發展的教學設計,會為每個學生提供主動積極活動的保證。如何“讓課堂煥發出生命活力”?如何改變部分學生只是不起眼的“群眾演員”(葉瀾)?回答這兩個問題,需要將“人”作為教育中最重要的目標來考慮,因為,人,才是生命的主體。
因此我貿然猜測,試圖幫助每一個學生都能意識到他的“自我建構”,是張齊華老師作出改變的目的之一。只是,要將這樣的目標納進教學視野,就必須要對自主創造的課堂與教師主導的課堂這兩極完成某種超越,就意味著教師將自己拋擲在了一個更加為難的境地。因為,錦上添花很容易贏來喝彩,雪中送炭卻未必能得到理解和鼓舞。如此思量,也許能對我們理解所謂“課堂教學對教師和學生都具有個體生命意義”這句話有些許幫助。大文學家歐陽修說:“教學之法,本于人性。”“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明。”從為學生而思變這個意義上看,張老師這番改課比之于以往的同課異構,可能是更需要一點勇氣的吧。
二、改課,不改主動建構之本意
如果將知識看作是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那么學習活動的重要特點就在于其主要是一個主動順應的過程,即是認知框架的不斷擴張和重組,后者是新的學習活動與認知結構相作用的結果。這是建構主義學習觀對學習的一種認識。那么,將一節自主探究的課改成由教師告知結論的課,究竟有沒有達到前文所述“雪中送炭”的目的呢?表面上看,課例2這么一“告知”,就不能為學生的主動探索留下更大的空間。從建構的角度來看,它有沒有違反認知的規律呢?
兒童發展心理學家皮亞杰關于數學學習的一個基本觀點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啟示:“全部數學都可以按照結構的建構來考慮,而這種建構始終是完全開放的……這種結構或者正在形成更強的結構,或者正在由更強的結構來予以結構化。”由此來反觀兩個課例,我們可以發現:課例1當中,兒童對于各種表示方法進行了豐富的思辨和抽象后再建立起的規則自然是建構的結果;課例2中,兒童由教師提供的數對出發去分析和重構,“告知”的形式似乎缺乏開放的意識,但是其內在的思維上的開放,使學生的認識過程清楚地呈現為一種主動的態勢。
美國學者伊弗斯的《數學圈》里有段對話很有意思。有人問證明某個命題是什么感覺,數學家回答:證明一個定理就如看見一座感興趣的山峰。為了到達頂點,我們搭起大本營,然后沿陡峭的山路攀登,掙扎著邁出腳步,一寸寸的延伸旅程。最后我們登上山頂,俯瞰四方——發現山的另一邊有條大馬路!然而,在簡單的結論和愉悅的思辨之間,讓孩子們自己去做選擇,他們會去走那條大馬路嗎?
我們可以看到,當教師告訴學生“用(4,2)表示”之后,學生們便有了自發的爭論,有爭論就必然需要對話。張齊華老師恰恰是一位營造“公共話語空間”的高手,他引領但卻又不占領舞臺,生生之間通過“自我協商”與“相互協商”的方式來解決自我產生的疑惑。課堂便如供人自由呼吸的山林,“游人去而禽鳥樂也。”如此,思維對話的價值得以凸現,富有活力和創見的想法不斷得到激發。規則,在充滿張力的數學思考中逐步清晰;理性,在智慧的不斷碰撞中漸漸沉淀。
三、改課,不改以問題引領學習的意識
哈爾莫斯有句話得到了我們普遍的贊同:“問題是數學的心臟。”也有人說:“最精湛的教育藝術,遵循的最高準則,就是讓學生自己提出問題。”
2007年課例中學生提出的問題是:比“第3排第4個、第4組第3個”更簡潔、準確的方法是什么?由此才引發了學生創造的熱情,而學生也不負所望,在各種自圓其說的方案中逐漸逼近了實際的規則。2011年課例則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教師已經給出數對了。但學生還是說:“有問題!我們組的答案不統一。”
我們對一定世界的無知還構不成問題,只有當它被主體自我發覺,使其進入思維活動,也就是意識到了無知并以思維的方式主動反映時,“問題”才會形成。所以才“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此處老師的告訴,目的是喚醒學生的經驗,啟發學生比較鑒別、質疑批判,使學生得以保持思維的敏銳。且看學生們的表現:得到數對之后,學生顯然是有交流的,答案的不統一,促使他們分析問題并找到原因:原來是老師的表達有漏洞。對教師的質疑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否定。皮亞杰認為,通過這種否定的行動,解決矛盾、消除差異、排除障礙或填補間隙,正是一種有意義的學習。
這一設計在我看來就如中國女性穿著之旗袍,看似保守,實則性感十足。旗袍之美,在于貼合了中國女性溫婉豐潤之身材而掩其不足也;而課例中的“告訴”,正是教師對部分學生初嘗新知時候的無助體驗的理解與幫扶。幫助學生是教師的天職,但真正的幫助是讓學生“擺脫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依附”,倘若一告到底,則又失去數學課堂的魅力了。再看學生得出兩個關鍵詞“順序、方向”之后,教師又是如何“告訴”學生規則的:“不過很遺憾,這兩個問題,我都不想直接告訴你們。不過,我可以透露一下,我孩子最要好的朋友小鄧,他所在的位置如果也用這樣的數對來表示的話,應該是(2,1)……”
學生再也按捺不住了!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表面上看是“老師告訴”,實際上則意味著“先讓學生產生困惑”。由此看來,“解惑”的潛臺詞是“先主動學習,再自己求解”。可以說,問題的指向性和延展性在張老師的課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曾有人以“精細的教學架構、精練的板塊推進、精致的教學演繹”來描述蘇派數學教學。以此觀之,誠不欺也。
四、改課,不改通過數學學會思維的主張
建構性的學習旨在使學習者形成對知識的深刻理解,然而我說數學課堂的目標不止于此。香港大學蕭文強先生論及數學教育目標的時候,曾借用清代文學家袁枚關于學、才、識的論述:“學、才、識正好可用以概括數學教育的目標,即思維訓練,實用知識,文化素養。”
縱觀張老師的課堂,可以發現,他所追求的恰恰是我們數學課堂需要去做的事情。我們可以看到:從座位排列到數據表格再到棋盤等等,除了暗合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的思維過程,更將數學活動和學生個體經驗發生意義上的關系;由書上的規定與生活中實例的比較,從組成以及方向順序之不同再到其中的內在統一性及其辯證關系,完成了學生規則意識的第二次認識上的飛躍;從二維的平面空間到三維的立體空間,乃至多維的無限空間進行大膽而理性的推想,激發了孩子無限的研究欲望……
正是在這樣的開放意識下,2011年課例得以和張齊華老師以往的課一樣,課堂的終極追求超越了確定可靠的結論,而是指向了種種從原有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一個個新的更高的數學課堂追求。這份追求的心境,恰如詩人在山水中跋涉徜徉后所得到的回報。正是“綠陰不減來時路,添得黃鸝四五聲”,能夠在課上聽到學生“鳴聲上下”,學生何其爽也,教師何其幸也。上得一節如此有意義的數學課,夫復何求?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課堂變革的東風正是方興未艾。張老師“一個人的同課異構”,給我們留下的遠非僅僅是兩節課那么簡單。在理念層次上,如何以兒童發展為出發點來思考教師自身的發展已經引發了我們的關注;從課堂實施的技術層面看,這兩節案例本身亦不失為一種可供借鑒的范本。實在應感謝張齊華老師的辛勤耕耘和默默堅守,給我們展現出教育的生動圖景。不有佳作,何申雅懷?向著共同的目標,無論是泛溪還是山行,無論是愉悅還是艱辛,相信我們一定能看到更多的精彩課堂和更好的學生發展。
(劉志強,無錫市揚名中心小學,214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