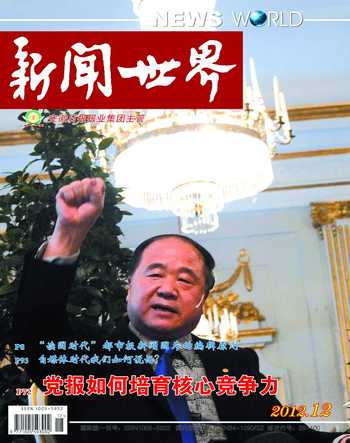淺談微博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李曉軍
【摘要】本文從Twitter談起,深入分析了微博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關鍵詞】微博傳播力影響力
“在Twitter中,即便只有一個人關注你,僅僅通過若干分隔空間,你便可以同全世界數百萬正在使用Twitter的人產生聯系。”①其實,微博帶來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以溝通渠道為核心的互聯網信息傳播革命——對字符的限制無疑使其互動性增強,僅僅140個字,就能引來一連串的交流,不是因為這些文字有多么風趣或是精辟,而是人們更愿意通過微博這種進入門檻較低的媒介作為載體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與他人分享關注的話題。Mary Ann Bell在其文章《What's all the noise of about Twitter》中評論道:“Twitter網站的最大吸引力之一就在于這種交流感。”
一、Twitter使信息從“推”開始
首先,Twitter作為一個網絡媒介,與傳統紙質媒介傳播交流方式是不同的,因為人們看到的是光束而不是紙張,網絡交流是一種非線性傳播交流模式,“當你為網上的讀者寫材料的時候,你必須保證讀者會從你的網頁上‘帶走他們想要的信息”②。電腦屏幕上顯示的信息是二維的、互動的、具有多媒體效果的,而人們在電腦屏幕上瀏覽信息,卻并不仔細閱讀,太陽微系統公司的調查發現:人們在電腦屏幕上的閱讀速度要比平常閱讀報刊等的速度慢25%。在這種情況下,僅140字的字符限制是微博的強大優勢。
第二,Twitter不同于電話——雖然兩者都是一種私人交流工具——電話中談話內容具有私人性質(Twitter也可通過“私信(DM)”功能私下交流),而Twitter公開談話內容,并與陌生人溝通。簡言之,在Twitter中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交流,而主題是由推客(Tweeter)確定。
第三,Twitter不同于博客。Twitter的微小性使得更多的留言更頻繁地涌現出來,它的訊息直截了當且速度迅捷,這樣在交流過程中傳者受者的位置在不斷轉換之中,這種交流觀是一種類似詹姆斯·凱瑞所言的“儀式觀”,強調“言說”與“交流”,這不僅因為從文化傳承與價值持守的維度來看,在傳播中“言說”勝過“所察”,“交流”重于“拍照”,而且蘊含著在一定程度上回歸口語傳統的潛臺詞。而Twitter因其媒介屬性使得地理位置正在變得無關緊要,字符限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交流共享,因其交流速度消除了人與人溝通障礙。因此,與博客相比,Twitter上的交流運轉得更快,往往也更加深入。梅特卡夫法則(Metcalfe's law)告訴我們:網絡價值隨著網絡節點數量的增加而呈指數增加。在Twitter城,我們都成為一個網絡節點。分享某個既定話題的消息和想法的人越多,我們這個整體的能量就越大。
二、微博的傳播力
從傳播時代進入交流時代的一項基本變化在于,決策的流動方向從由上至下轉入由下往上。在公司決策層面,企業利用微博進行博客監測的一個手段:通過140個字符嘗試開導不可知論者信奉企業的價值理念。統計顯示,潛伏在博客、Facebook和Twitter上的人,遠遠超過參與交流的人。即便如此,潛伏本身也是一種精明的開始方式,而企業團隊也清楚地知道:Twitter的價值不僅僅在于追蹤人們對于你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一種不間斷的反饋循環。在Twitter中最大的優勢在于,服務是公開的,所以,當一位顧客得到企業Twitter團隊中某位成員的幫助時,數千人都能看到這一切,是一場真實的“秀”。《赫芬頓郵報》專欄作家艾琳·懷斯特描述她購買新電腦的經歷:“我們一直談論的是別的事情,政治、會議以及養育子女什么的,聊了好一陣子后,才提到我需要臺電腦這檔事。他們已經是我的社區的一部分了。人們支持他們的朋友、他們的社區,不管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當我最終掏銀子的時候,你肯定猜到了,我買了一臺戴爾電腦。”③這反映出微博在人際交往中的特點和作用,它將人際交流變為一種關系的發展,一種管理自我信息的過程。
社會穿透就是關系當中增進親密感和信息透露的理論,而創造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厄文·艾爾特曼和達爾馬斯·泰勒(Dalmas Taylor)認為,一個人可以用一個由不同層次組成的球體來代表。如果關系相對而言具有回報性,那么就能維持下去;反之,如果關系的代價過于高昂,那么就會冷淡下去,這一過程稱之為“社會交換”,可見,交流雙方不僅會在各個特定的時間點上評估關系的回報和代價,同時也會利用他們所搜集到的相關信息來預測未來關系的回報和代價。而微博這一媒介,使得人與人之間存在著開放性的循環圈,由此逐漸形成情感交流,進而到達穩定交流階段,在交流過程中雙方對環境、小企業、社會性媒體的熱情和共同經驗范圍使得交流溝通得以持續和深入,企業公司的微博不再是“托兒”,而是形成一個社區和小團體。
三、微博的影響力
微博放大優勢的同時,也帶來另外一面,那就是它會使得企業在微博中的任何微小動作放大。如德國負責代理百事可樂公司的廣告代理商——BBDO廣告集團杜塞爾多夫分公司,其創意團隊設計了一個嬌小可愛的藍色卡通形象,它代表著每瓶百事極度可樂中“僅有的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孤獨的卡路里”。這三則廣告描述的是卡路里企圖自殺的情形。它采取的五花八門的自殺方式包括有上吊、中毒、割腕、槍擊等。一系列廣告中,人們可以看到子彈從卡路里頭部的另一端呼嘯而出,鮮血四濺。而當這一精彩的廣告投放不到24小時,關于對這些廣告的評價信息就已經蔓延至目標受眾之外。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留言出現在百事可樂的官方微博之中:“人們不愿意談論與自殺有關的事,對經歷過這樣的事情的人來說,這是一個痛苦且帶有私密性質的話題。”④隨即,這些廣告被撤換,與BBDO的合作也終止。
這樣的負面危機事件至少說明了兩點:第一是用戶獲得了掌控權,在社會性媒體出現之前,此種類似事件根本不可能發生,而在Twitter之下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但這至少說明百事可樂公司是一個受人關注的企業。其次,同理心和移情也在此次百事可樂公司危機事件中凸顯,Twitter放大了人們的反應,當然在這個事件中是負面的反應。品牌賬號已不再是單向的交流模式,它甚至會影響企業重大決策和品牌形象。正如星巴克咖啡的理念:星巴克關注更多的是人,而不是咖啡。事實上,品牌并不是代表人,但可以讓人在Twitter上用自己的聲音代表這些品牌,并顯示自己的真實面容,以這種方式加強品牌的影響力。Twitter也為公司的品牌和形象增添了一絲人情味。
在辮子新聞中,其中一條組成部分就是“公民新聞”,“重要之處在于,這些免費報道新聞的業余愛好者相信,其他人應該知道這些事情。”微博給予了人們一臺印刷機,給予了每個人一家自費出版社。這不由得讓人想到了自然災害中公民記者運用社會性媒體,地震、海嘯、颶風襲擊時,總有些普通公民及時發布消息,有圖片、視頻、音頻等形式來向人們講述他見到的景象,讓讀者切實了解正在發生的事件。互聯的黏性也體現其中。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真實性和客觀性又該如何保證?簡單依賴于推客和銳推互動方式顯然不能完全避免虛假信息和新聞。史蒂芬·列維特就曾在《魔鬼經濟學》中談到:“在微博中,有價值的信息占到的比例僅為4%左右。”
從尼古拉斯·內格羅蓬特和道格拉斯·拉舍克夫到喬治·吉爾德(Geogre Gilder)甚至紐特·金里奇,每個人都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社會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時期,它就像過去千年盛世那樣,人類的社會生活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或許,這個變化就從Twitter開始。□
參考文獻
①③④[美]謝爾·以色列 著,任文科 譯:《微博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②[美}謝爾·霍茲,吳白雪、楊楠譯:《網上公共關系》,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作者單位:浙江農林大學后勤產業集團辦公室)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