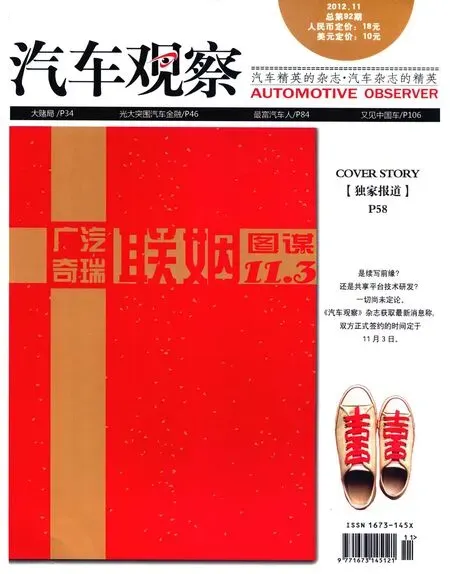被綁架的產能沖動
黃蓓蕾
這個賭桌的兩邊,一邊是企業,一邊是政府,它們都有著自己的籌碼,而這卻是一場輸不起的賭局。
這場新能源的豪賭至少給一汽轎車換來的是126萬平方米的土地,在車市持續減速,庫存也在不斷增加,像一汽轎車這樣的車企建新廠的步伐并未因此而減緩,反而有加速之勢。
就在今年上半年,福特、大眾現代、寶馬等的新廠猶如雨后春筍,這場押寶中國市場的行為對于企業之間更像是一場賭博——競爭對手都在下注,如果跟風,則有可能亂中取勝;如果不跟,鐵定成為輸家。也因此有人說:“在國內各個行業庫存加大的大背景下,汽車產業產能過剩的禍根再次被埋下。”
而這又是一場賭局,賭桌的兩邊,一邊是企業,一邊是政府,它們都有著自己的籌碼,而這場賭局對于雙方來說都輸不起。
“萬俱樂部”誘惑
從1800萬輛到2000萬輛的產銷,再到限購令政策實施等因素的影響下,車市增長大幅回落,這些年,似乎沒有力量可以阻擋車企擴產的決心和步伐,甚至連一些“保守”
的車企也開始跑馬圈地。
《汽車觀察》雜志細數了一下今年上半年宣布了未來有擴產計劃的企業,達到10余家,掀起新一輪的擴產熱潮。
長安福特馬自達重慶二工廠正式投產后,隨即公告了其在杭州的整車廠投資項目,5月,上海大眾新疆工廠正式奠基,這是上海大眾的第七工廠,6月伊始,華晨寶馬第二工廠鐵西工廠正式開工,上海通用武漢工廠就報道出正式奠基的消息,這是上海通用的第四工廠,隨后,6月25日,東風日產第四工廠在大連奠基,此后三天,廣汽菲亞特工廠竣工,東風悅達起亞第三工廠此后一天在江蘇鹽城奠基,還有東風本田第二工廠,北京現代第三工廠、廣汽本田第三工廠……隨著越來越多的車企加入“萬俱樂部”,可這個市場真能容納這么多車嗎?
一種樂觀的情緒是:目前車市的低迷只是暫時的,而車企擴張卻是為了仍然有光明前景的未來。國家信息中心信息開發部主任徐長明認為,從中長期來看,中國車市將進入第二個高速發展期,預計到2020年前仍將快速發展,年平均增長率約為20%。
福特中國董事長蕭達偉也積極地表示,中國車市2020年的產銷量將達到3000萬輛。而另一種悲觀的情緒是,從產銷情況來分析,今年中國車市結束了長達10年的高速增長,國內汽車產銷長期在10%以下徘徊增長或將成為常態。
不過,根據車企擴產的數量來看,市場必須要以20%的增速前行,才有可能消化如此大的產能。
從品牌情況來分析,《汽車觀察》雜志也曾報道過J.D.Power對未來三年的中國汽車市場做出預測:到2015年,中國乘用車市場將有90多個汽車品牌,其中自主品牌占據一半以上。
中國的汽車品牌是全球所有汽車市場最多的,相當于美國市場品牌數量的兩倍以上。如此眾多的汽車品牌面臨的市場競爭將會更為激烈。
產能過剩或者不剩的爭論,《汽車觀察》認為,未來一定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時代,優勝劣汰將更為明顯,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建新廠的都是近年來發展較快較好的車企,未來中國車市產業集聚將更加明顯。
誰是背后推手?
從年中上交的“成績單”來看,多數汽車企業難以完成既定的銷售目標,但即使形勢不樂觀,車企仍樂此不疲的跑馬圈地,將觸角深入此前未涉及的區域,完成全國產能布局。
“對于各個汽車企業這樣去做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錢不是它的,另一方面投資的地方政府還可以獲得很多的補貼,所以說跑馬圈地即便是利潤率很低的情況下,也要去搶占市場份額。”銀河期貨首席宏觀經濟顧問付鵬認為。
實際上,由于2008年、2009年購置稅的大幅下調以后,汽車消費有所透支,因此導致現階段汽車的消費增量開始放緩。
同時,交通壓力導致各個城市限購力度和范圍越來越大,這都直接影響到將來中國汽車消費的增速可能不會像以前一樣是高增長的年代。
在付鵬看來,汽車工業跟其他工業類似,在高速發展中主要依賴于銀行信貸。
地方政府考慮到GDP因素也大量支持此類項目上馬,最終導致這個行業會走向產能過剩。
“汽車工業具有產業鏈長,帶動性強的特點,大規模發展汽車工業成為地方政府全力推動經濟發展的重點,在利益的驅動下,產能規劃容易被盲目抬高。”國家發改委產業協調司司長陳斌和付鵬有著相同的觀點,并一針見血地指出跑馬圈地的幕后者。
各地方政府相繼出臺地方版的汽車振興規劃和戰略布局,提出了新的產能擴張目標。例如,安徽計劃2 0 1 1年全省汽車產量達到100萬輛,重慶計劃2012年汽車產銷量達到200萬輛,吉林預計2011年汽車產量超過180萬輛,山東計劃2011年汽車產量達到國內的10%等等。據悉,目前已有20多個省市制定了新能源汽車發展規劃,有過半數的省市把汽車業作為戰略性主導產業來抓。
與此對應,各地扶持汽車業的相關政策頻出,給出了不少優惠條件吸引汽車廠家入駐。例如,北京市統籌安排50億元資金,用于汽車等六大重點行業發展;杭州對獲得轎車生產牌照資質的企業,一次性最高獎勵300萬元,對通過兼并重組以及年產銷規模首次超過20萬輛的汽車生產企業,一次性獎勵200萬元;鄂爾多斯汽車招商項目可配煤礦資源等等。
以鄂爾多斯為例,《汽車觀察》曾做過相關報道,其汽車裝備基地接連引入華泰汽車、奇瑞汽車、東風汽車、中興汽車和眾寶汽車等新設工廠,總投資超過500億元。華泰汽車在鄂爾多斯圈地6000多畝,不僅享受西部大開發的相關稅收優惠、全國最便宜的企業用電價、長期減免企業在當地的多種行政事業性收費,而且,還配置了兩座煤炭資源。據有關媒體報道,2008年,僅靠出售一座煤礦的開采權,華泰就獲得了7億元。
“零地價的誘惑,這是各地政府在引進投資時慣用的手法,除此之外,很多優惠政策的出臺,都是為引進汽車項目大開綠燈。”一位業界汽車專家對《汽車觀察》說。
對于車企來說拿到零地價的同時,它形成了產能并解決了當地的就業,對于政府雖然出手了土地,但是卻換來了稅收,雙方都有著自己的籌碼,卻充滿了風險。
風險一旦顯現,這筆巨額賭資也就隨之“泡湯”。如何能把控這一風險?其主動權還在政府手中。一位資深業內人士對《汽車觀察》說,政府不能只想著未來的稅收,更應該在此前對企業進行深入地調研,最終只有企業發展了,“這才是筆好買賣。”
而按照慣例,一個新工廠投資建設動輒至少幾十億元人民幣,通常需要至少實現80%的產能利用率才能抵消高額的固定成本。業內人士認為,如果企業面臨產能過剩,通常會通過增加出口或者采用更加高效的柔性生產模式來減輕虧損運營的風險。
相關專家認為,在中央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汽車整體產業應加大自主創新和品牌提升力度,同時在協調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情況下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扶強補弱提高競爭力,將產業做大做強,使我國從汽車大國轉變為汽車強國,這才是產能爭論的最終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