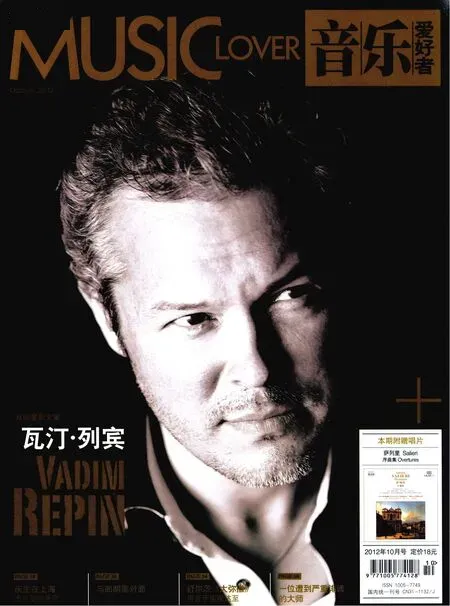舒爾茨《大彌撒》用音樂實現達至
梁晴



大彌撒
這是一部舞蹈作品,由二十世紀卓越舞蹈家舒爾茨(Uwe Scholz,1958-2004)創作于1998年,因為用了莫扎特被稱為“大彌撒”的《C小調彌撒》(K.427),所以名《大彌撒》。
舒爾茨出生在德國朱恩海姆(Jugenheim),從小天資聰穎喜歡舞蹈和音樂,孩童時就到附近的達姆斯塔特國家音樂藝術學院學習鋼琴、小提琴和古典吉他,十幾歲時曾立志成為一位音樂廳的售票員或指揮家,后來他成為了舞蹈家。1985年至1991年二十六歲的舒爾茨已經擔任蘇黎世歌劇院舞蹈總監,從1991年后一直是萊比錫歌劇院的編舞。舒爾茨喜歡莫扎特,早就不是個秘密。在他百來部作品中,多次運用莫扎特的音樂,如《小夜曲》(1977)、《年輕人》(1982,用鋼琴協奏曲K.271)、《魔笛》(1997)。
《C小調彌撒》是莫扎特的一部未完之作。寫于1782年,為兩個女高音、男高音、男低音和雙合唱隊及大樂隊而作,那時莫扎特剛進入維也納,當時正逢他大婚之喜,與別的彌撒不同,由于它不是奉命之作,所以有發自內心的直率和歡愉,又因為獻給新娘康斯坦策,特別安排大段的女高音,音樂莊重華美。與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曲》一樣,它因殘缺而更添美感,盡管缺了《信經》和《羔羊經》部分,有人仍將它與巴赫的《B小調彌撒》、貝多芬的《莊嚴彌撒》并列為世界最偉大的“三大彌撒曲”。《大彌撒》還包括莫扎特的另兩部作品:器樂曲《慢板與賦格》(K.546,1788)和合唱《圣體頌》(K.618,1791)以及更多內容,形成跨時空多作品重組,同時也解構了莫扎特,分以下十七段:
1. 格里高利圣詠:諸圣瞻禮主日彌
撒進臺經(中世紀)
2. 莫扎特:《C小調彌撒》慈悲經(1782)
3. 莫扎特:《C小調彌撒》榮耀經(1782)
4. 托馬斯·楊:《時空》(1991)
5. 庫塔克:《游戲》(選段)和巴赫
作品改編曲(1970-80)
6. 策蘭的詩《柱頭》(1960)
7. 莫扎特:《慢板與賦格》K.546(1788)
8. 策蘭的詩《穿成線的太陽》(1968)
9. 格里高利圣詠:信經(中世紀)
10. 莫扎特:《C小調彌撒》的信經(1782)
11. 阿沃·帕特:《信經》(1965)
12. 莫扎特:《圣體頌》K.618(1791)
13. 策蘭的詩《詩篇》(1963)
14. 莫扎特:《C小調彌撒》圣哉經(1782)
15. 莫扎特:《C小調彌撒》降福經(1782)
16. 托馬斯·楊:《時空》(1991)
17. 莫扎特:《C小調彌撒》羔羊經(由于這部分未創作,這里安排用莫扎特《C小調彌撒》慈悲經的音樂填補)
《大彌撒》是二十世紀末的佳作之一,是繼伊麗莎白·普拉特(Elisabeth Platel)《圣母晚禱》(Magnificat)后的宗教舞蹈作品,并與貝嘉(Maurice Béjart)的《生命之歌》(1997)有異曲同工之妙,相比之下,《大彌撒》“話題”更嚴肅。它一經上演就反響熱烈,被褒揚是一部“登峰造極之作”“今生看到最好的舞蹈作品”“一次可一不可再的盛會!”
史詩與游戲
人們說,貝嘉的舞蹈是哲理舞蹈,舒爾茨的舞蹈是交響舞蹈。舒爾茨一人承擔《大彌撒》的編舞、音樂設計、服裝、舞臺等創作,令人感慨。其舞蹈顯然是度音定造,根據音樂的樂句、聲部關系及配器等特征,創編動作,舞臺上有變化萬般的幾何圖形,既精確又流動。時常,音樂與舞蹈之間平行同步,如:四部合唱與四組人群、女高音與女子獨舞、三重唱與三人舞、合唱與群舞十字架等,再加上燈光配合,足夠炫目。對這樣的作品,需要眼睛聽耳朵看。舒爾茨把舞蹈視為另一件樂器,舞蹈巧妙地融入音樂,強化音樂的詮釋。
《大彌撒》全長共一百三十分鐘。“話題”有一白一黑兩個世界,音樂則一古一今。莫扎特音樂處,燈光溫暖,舞者們身著素潔白色長裙或褲子,表情端莊,體現神圣的恩典與力量。而在庫塔克、帕特和托馬斯·楊的音樂及策蘭的詩處,舞臺轉黑暗,舞者換上黑衣。分割與對峙,投射出樂觀與悲觀、崇高與世俗、理想與現實的區別。
在榮耀經之后,有一個獨立部分,“話題”看似很輕松,大約十三分半鐘(第五段),與前后形成較大反差:一兩位舞者、身著黑衣、舞臺被縮小、鋼琴獨奏、寥寥數音、說一些個人“俗”事。音樂采用匈牙利作曲家庫塔克(Gyorgy Kurtag,1926- )的鋼琴套曲《游戲》,寫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每段僅有幾行譜或幾個音,好像隨手速寫,了了幾筆,自言自語。生活中的庫塔克也是少言寡語,藝術上追求一種超越聲音的直接感知,他曾說過“有時候一個音就足夠了”,“對我來說,音樂不是使命,不是藝術,而是一種生命狀態”。《游戲》選段中,另加兩首庫塔克改編的巴赫作品,分別是:1)花是我們,我們是花(101);2)巴赫/庫塔克:我從深淵向你呼告(BWV687/523);3)弦外之音(050);4)花是我們(040);5)敲打-糾結(104);6)巴赫/庫塔克:上帝的時間是最好的時間(BWV106/220);7)激越的眾贊歌(050);8)一筆畫(032);9)自遠方(212)。音少了,舞者的肢體及表情要求更細膩,舞臺后方用了鏡子,反射前臺的一舉一動,有時,無聲中,在演釋一個很復雜的故事;一個和弦下,是無聲的嘶聲裂肺吶喊;在“上帝時間”的樂聲中,是男女花前月下的美好愛。
《大彌撒》有一種大型史詩的厚重感。看似輕松的《游戲》,埋下了諸多疑惑:為什么有人在抽搐?為什么嵌入巴赫?為什么用鏡子?為什么要游戲?舒爾茨認為現代藝術應該有能力抓住現代人的眼球和內心,有責任直接面對當下問題。在偏離錯位中,“話題”幻出幻入,線性敘事不斷改變著方向。如此做法沒有讓人渙散,反而迫使人卷入。
信—信—信
布局是“話題”成為一個令人信服整體的有序步驟及控制。
經過曲折跨越,《大彌撒》開闊的“話題”也逐漸明確起來。當莫扎特《慢板與賦格》響起,原本散開的趨向歸攏,厚重的低音弦樂及嚴密的復調將“話題”引入核心,帶著莫扎特音樂中較少見的德國式遺風。莫扎特是定居維也納之后才開始接觸巴赫的復調技術,因此,《慢板與賦格》與《C小調彌撒》有相近的風格,還有居然同是C小調,應該不是巧合。由這些細節可見,舒爾茨關照著“話題”的上下文并熟悉作品。之后,在黃金分割點上,連續出現跨時空的三曲《信經》(第九、十和十一段):一是中世紀格里高利圣詠《信經》;二是莫扎特《C小調彌撒·信經》;三是愛沙尼亞作曲家阿沃·帕特(Arvo PORT,1935- )寫于1968年的《信經》。三部作品經文未變,風格不同,信念態度迥異,音樂語氣大致是:中古時期是純凈的合唱,人們仰視上帝,信念虔誠而堅定“上帝,我信!”中世紀過后,人性開始復蘇,十七八世紀時,人與神平等共處,器樂與合唱和諧交響,道出“嗯,我們信上帝,當然也信自己”。再往后,時過境遷,二十世紀的現代人已經很難相信上帝的存在,音樂充斥著不和諧的聲音,許多人七嘴八舌:“信什么?……不,不信!”好在嘈雜中,有幾個人低聲堅持說:“上帝,您仍在,我們信。”
藝術貴在立意新奇,奪人耳目。與其說舒爾茨在“創新”,還不如說他敢于“守舊”,能在別人嚼爛的主題和事件中進一步再言說才算本事,因為,那些永恒的“話題”往往是有價值的。在常規彌撒中,《信經》原本就處于中心,戲劇性最突出。《大彌撒》中《信經》連續遞進,形成一股強有力的向心力,重申和證實“信”之重要及堅實。
帕特的《信經》將《大彌撒》推上高潮。這部作品完成于1968年,編制有獨奏鋼琴、合唱及樂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文化藝術正處于極其動蕩的時段,許多現代音樂只能取某一端,也能俘獲部分人,帕特的做法不同,他屬少數折中派,盡管寫這部作品時他還默默無聞,帕特在這部《信經》集中體現出他成熟的想法,音樂在秩序與混亂、有神論與無神論、失望與希望、和諧與噪音、有調性與無調性音樂中質疑、思考與選擇。舒爾茨的舞蹈將深奧的道理變得簡明易懂,整個舞臺講述的是一個生動的故事:開始嚴肅而崇高,音樂將巴赫《平均律》第一冊第一首前奏曲的著名曲調和聲化,舞臺很暗,有一位舞者獨自走在前面,后面是一排影子人,他們在黑暗中隱隱抽搐(《游戲》中已經埋下伏筆),色調是神秘黑與血腥紅的并存。然后,巴赫的主題正式由鋼琴奏出,代表著真理和正義,在定音鼓之后是樂隊與合唱進入,樂隊與合唱不斷打斷鋼琴,經過展開,二者成為正與邪的對峙與較量,鋼琴不斷被削弱,層層推進。這個地方,舞蹈上眾人爭搶凳子,而凳子逐一減少,最后當男主角坐上唯一的凳子時,被千夫所指,不奇怪,高處往往不勝寒。聲音越來越粗放,銅管的咆哮聲、鋼琴的擊打聲、人群的喊叫聲匯在一起,多媒體加入,人在打滾掙扎,推向高潮。在復雜的亂象中,好在有一絲信念尚存。接著,低音提琴C持續音也低聲響起,情緒慢慢地在轉向平靜,當唱到“圣靈感孕”(‘Et incarnatus est)時,一個燭光從天而降,伴隨著巴赫曲調被召回,黑暗中顯得特別明亮,這是希望之光,男舞者手捧光明環繞舞臺奔跑,當合唱肯定地唱出巴赫旋律時,那束光被投向空中,神奇地升騰。
這里,音樂、舞蹈、燈光等不同因素相互補充、映襯、放大與提升。《大彌撒》之《信經》三聯組聚集起一股能量,成就了一個感人入心的不凡瞬間。
線,各自反向延伸
《大彌撒》十七段音樂不是零散的點,內在有串起來的線:一、前景,莫扎特的音樂,貫穿整體;二、中景是兩個亮點,即庫塔克《游戲》和阿沃·帕特《信經》兩部現代作品;三、背景有數個小段,作為引入、轉折或連接作用,如格里高利圣詠、德國作曲家托馬斯·楊(Thomas Jahn,1940– )的《時空》及德系猶太詩人保羅·策蘭(Paul Celan,1920-1970)的詩歌。
從楊的《時空》和策蘭的詩歌中,可以揣摩到舒爾茨的意圖。第四和十六段是楊的作品《時空》(Orte und Zeiten/Tempi e Luoghi)。楊出生在柏林,現在活躍于漢堡,曾在柏林、漢堡音樂學院學習鋼琴、長號和作曲,1969年到美國洛杉磯學習流行音樂。他的創作范圍很廣,有劇場音樂、電視劇配樂、歌劇、舞蹈以及室內器樂等。《時空》可比作現代意義上的舒伯特藝術歌套曲《流浪者之歌》,寫于1991到1993年,基于德國與意大利詩人的詩作,如朱塞培·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1888-1970)、英博柯·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她曾與策蘭有過一段復雜的感情)、彼得·赫爾特林(Peter Hartling,1933- )等,內容涉及反戰、反暴力、反陌生化問題。第四段選自《時空》套曲的第二曲,詩歌正是勞克斯(Bernhard Laux,1955- )的詩《時空》,暗淡的舞臺上傳來先鋒性聲響,約兩分鐘,異質的長笛聲,氣聲、花舌及唇齒摩擦聲,由女聲念出傷感的詩句:“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時刻/平行線的兩端/反向延伸/難以相交/然而一旦它們交匯/道即彰顯/那一刻/是難得一見的。”
策蘭的詩出現在《大彌撒》第六、八和十三段,舞臺上只剩下一人,他神情凝重,自舞自吟。天才的詩句充滿樂感,具有啟示性意義,不過即便被這些文字迷住也并不證明你能進入這些文字。《穿成線的太陽》寫于六十年代,是策蘭一首重要的詩,形象抽象“穿成線的太陽/在灰黑的荒野上/一棵樹/彈著光調:還有/歌在人類以外/吟唱”。情景并不是“話題”本身,費解的字詞背后交織著多向度張力。同樣,《大彌撒》有詩一般的結構,舒爾茨用離奇的疊置和穿插的線條創造著新的關系及思想。
實現達至……
不必回避,缺失與遺憾也是完美的一部分。2004年11月,年僅四十六歲的舒爾茨由于健康原因離世,另一種犧牲。次年在他周年祭活動上,作為儀式,再次上演《大彌撒》。
進入第十六段,楊的音樂第二次粗暴地打斷“話題”,令人意外的是,舞臺上演員們一一當眾卸去裝束,夢被打破。臨近尾聲,“話題”在飛速轉換。
帕特曾說,“在我創作過程中,有很多復雜的和多元的東西纏繞我,于是,逼迫著我必須尋找統一。而這統一又是什么?我如何能夠找到它的途徑?有時,追求完美會滋生很多虛偽,于是,缺失也并不是那么可怕。”應該承認,很少有人能超越舒爾茨,他擁有如此豐富的古典舞語匯,對音樂的認識力非同尋常,總是在有限的空間中放飛無限的想象。一直以來,處理莫扎特《C小調彌撒》的這個部分是個難題,版本各式各樣,有一張卡拉揚的DG錄音(編號DGCD4775754),結尾用莫扎特《慢板與賦格》為《C小調彌撒》補缺。舒爾茨的音樂設計可以納入現代音樂文獻之列,音在獨立言說,走過萬水千山后,將開頭慈悲經音樂配上羔羊經文,《大彌撒》這樣收束。
最后一刻,舞者們都席地而坐,整個場子被懸置。據演員們回憶,舒爾茨讓他們安靜地坐在舞臺上,與觀眾一樣,聆聽音樂。之前是做加法,將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過去與未來、嚴肅與詼諧,整體與碎片,等等。然后做減法,策蘭《詩篇》充滿了否定,“無人再次用土與泥捏出我們/無人說起我們的粉塵/無人/你是應該稱頌的,無人/為了你我們/愿/綻放/對/你/一個無/我們恒古是,我們今時是,我們/永遠是,綻放著/無之玫瑰/無人之玫瑰”。無,非無,無,恢復整全。誰是無人?誰是演員?誰在表演?誰做主宰?當教條不再成為參照物,我們憑借什么判斷?以為有了結論,其實“話題”還在繼續。
舒爾茨曾說:“我并沒有創造什么,有音樂就足矣。”
完美不重要,實質重要;
宗教不重要,信念重要;
怎么說或說什么不重要,實現達至則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