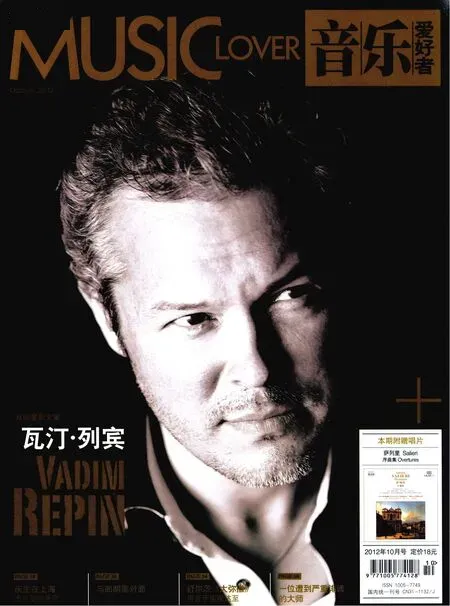騰飛之前的孕育與積淀
景作人



第一屆李德倫全國指揮比賽于2012年6月18日至6月23日在美麗的青島舉行。這次比賽是對我國年輕一代指揮人才的一次檢閱,來自國內各音樂院校以及在國外音樂院校中留學深造的十二名選手參加了比賽。
比賽的結果是第一名空缺,來自美國耶魯大學音樂學院的焦陽獲得第二名,來自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的景煥獲得第三名,來自德國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的李昊冉進入決賽。
本屆李德倫全國指揮比賽由文化部主辦,文化部藝術司、山東省文化廳、青島市人民政府、中國交響樂發(fā)展基金會承辦,青島國信發(fā)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協(xié)辦。比賽的藝術顧問是吳祖強和黃飛立,評委主席是俄羅斯指揮大師根納季·羅日杰斯特文斯基,評委會成員是:李心草、張國勇、鄭小瑛、俞峰、梁大南、譚利華(以姓氏筆劃排序)。
舉辦第一屆李德倫全國指揮比賽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情。李德倫是中國老一輩指揮大師,中國交響樂事業(yè)和交響樂指揮事業(yè)的開拓者之一。他的豐功偉績人所共知,現(xiàn)已成為中國音樂史上重要的一部分。以李德倫的名字命名指揮比賽,既是對這位偉大指揮家的緬懷和紀念,又是對參賽青年指揮家的鞭策和鼓勵,這是一個帶有“雙贏”色彩的創(chuàng)意。
本屆比賽我作為嘉賓來到現(xiàn)場,觀看了決賽階段的賽況。下面將我所看到和感覺到的情況羅列如下,以饗讀者。
成熟與細膩是取勝的關鍵
本屆比賽的最高獎(第二名)獲得者焦陽,是一位帶有“思想條理性”和穩(wěn)重氣質的指揮新秀。他當年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時師從于胡詠言教授,后赴美國耶魯大學音樂學院深造,在咸信益(Shinik Hahm)和鮑頓(William Boughton)的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焦陽在2006年于深圳舉行的第二屆全國指揮比賽中獲得第三名,當年他參加決賽時我也在現(xiàn)場,對其表現(xiàn)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
說實在的,當年的焦陽頗有一副指揮才子的“架勢”,指揮技巧已經很嫻熟。但他的弱點也很明顯,就是缺乏穩(wěn)重的成熟感,面對樂團,他常帶有不必要的情感外露和過于夸張的動作。記得賽后我與他接觸過一次,當時我就直言不諱地向他提出了這些看法。可貴的是,焦陽聽得非常認真,他一點都沒有找借口反駁我并為自己開脫,而是默默地記下了我的每一句話。看到他真誠的態(tài)度,我心中產生了一個念頭,這個年輕人不簡單,他日后一定會在藝術上取得成功,因為他的內心有著容納百川的氣度。
果不其然,焦陽在本屆李德倫全國指揮比賽中一路“過關斬將”殺到決賽,他的實力在比賽中展露無遺。搶眼之下,人們開始格外關注這個清秀而帥氣的小伙子。
進入決賽后,焦陽第一個出場,他選擇的曲目是勃拉姆斯《F大調第三交響曲》第一樂章(必選曲目)和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那天下午兩點,焦陽充滿自信地登上舞臺,面對著青島交響樂團的數十位演奏家,沉著地抬起了他的雙手。
本屆比賽有一個特點:選手們參賽時并不是從頭至尾將作品“順”完,而是邊演奏便排練,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完成對作品的音樂處理。焦陽上場后先排演規(guī)定曲目,“勃三”第一樂章很不容易,音樂結構嚴謹卻很有浪漫情調,對于指揮來講,如何處理好樂句的走向,繼而烘托出主題的特征,是一個“適度把握”上的難題。而樂章開始時銅管聲部的和聲效果亦是關鍵,這兩個和弦若處理得不好,接下來的第一主題就無法顯露出個性。焦陽面對總譜鎮(zhèn)定自若,語言和手勢都很簡潔,但排練的效果卻很明顯。我在下面隨著排練的進程聆聽,感覺樂團演奏的音樂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順暢。接下來的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焦陽強調了音樂的色彩延續(xù)性,對木管聲部的要求很細致。他的分拍打得精確,作品的整體性和樂風上的朦朧感都得到了盡情的體現(xiàn)。胸有成竹,成熟沉穩(wěn),焦陽靠此表現(xiàn)贏得了比賽。
比賽第三名獲得者景煥是一個性格開朗、心態(tài)平和的姑娘,其父是我國作曲家景建樹。當年就讀于中央音樂學院時,景煥是徐新教授的學生,后來赴美留學,在辛辛那提大學師從于指揮家吉布森(Mark Gibson),現(xiàn)正在該校攻讀指揮博士學位。
景煥有著很好的專業(yè)基本功,她對音樂的感覺十分敏銳,指揮動作清晰準確,富有一定的感召力。當天決賽時,她選擇的曲目與焦陽一樣,上場后先排演“勃三”第一樂章。她十分強調音樂的緊湊性,對于奏鳴曲式結構有著細致的處理,在呈示部兩個主題出現(xiàn)前,她做了相當充分的鋪墊,起到了有效的“啟示”作用。《牧神午后》她指揮得比“勃三”第一樂章好,對于這首印象派作品,她能夠以女性特殊的細膩來挖掘其中的色彩變化。我在下面觀察到,在將樂曲的整體結構調整順暢后,景煥重點排練了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演奏的內聲部音型,將音量、音色都作了“繪畫”般的處理,這樣便使得樂曲朦朧混沌的效果得到了更好的體現(xiàn)。
景煥是一位心理狀態(tài)和綜合素質都較優(yōu)秀的指揮新秀,比較參賽的其他選手而言,她的成熟穩(wěn)重感也是略強的。此外,她還有著男性般的大氣作風,排練時干凈利索,沒有過多的無意“糾纏”,這些都取決于她在音樂理解方面的自信心。
感性與理性結合才能成功
本屆比賽最令人遺憾的就是進入決賽的李昊冉未能獲獎。李昊冉是一個很有才能的指揮苗子,他的可貴之處就是具有無限的音樂激情,技巧也很不錯。李昊冉目前就學于德國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是德國指揮家埃赫瓦德(Christian Ehwald)的學生,此次參賽,他在前兩輪成績很好,是包括羅日杰斯特文斯基在內的全體評委一致看好的選手。
決賽那天,李昊冉第二個登場,他排演的“勃三”第一樂章尤其強調了音響的厚度,其他方面的處理算是中規(guī)中矩。自選曲目他沒有像焦陽和景煥那樣選擇《牧神午后》,而是挑戰(zhàn)性地選擇了肖斯塔科維奇《第十交響曲》第四樂章。說實在的,那天李昊冉真的很有氣魄,從曲目的選擇上,我就看出了他勢在必得的決心。果然,重新上場后的李昊冉使足了力氣,他將“肖十”第四樂章?lián)]得幾乎頂破了天,自己也開始渾身上下“拼搏”不止,形體動作一個接一個,而他手下的樂團則將音樂的速度推向了頂點。李昊冉的“激情”迸發(fā)到一瀉千里的程度,面對著像脫韁的野馬一般的樂團,他可能已經感覺到自己不是在掌控音樂,而是在隨著音樂奔騰不息。一曲奏完,旁觀者歡聲雷動,李昊冉本人或許也覺得自己很有希望。但是,他忘記了自己是處在比賽現(xiàn)場而不是音樂會現(xiàn)場,臺下端坐的是由數位頂尖級指揮專家組成的評委,而這些評委是不會輕易被他所表現(xiàn)出的激情感動的,他們需要看到的是感性與理想相結合的、符合作曲家作品風格的、正確而又適度的演釋。
果然,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后,決賽結果出來了,李昊冉沒能獲獎,連在獲獎音樂會上執(zhí)棒的機會都沒有。很多人為此而深深不解,而我卻在遺憾中接受了這個結果。李昊冉確實是一名出色的選手,他本來是有能力摘取獎牌的,但由于自己缺乏冷靜,在指揮時未能將感性與理想結合到均衡的程度,以致達到了對作品失控的地步。鑒于此,評委們給他打低分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通過李昊冉比賽失利這件事,我想很多年輕指揮都應該從中接受教訓。指揮到底是一項什么樣的藝術,每個人的心中都應該徹底搞清楚。一個指揮家,特別是年輕指揮家,一定要在自己的頭腦中樹立起音樂第一的概念,到什么時候都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要忘記你手下還有百十人的樂團,你的每一個擊拍、每一個舉動,都要對樂團負責,對音樂負責。不要總想著杜達梅爾有多帥,迭戈·馬修斯有多酷,繼而養(yǎng)成了一大堆輕浮外在的毛病,卻忽視了指揮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掌控能力,這是一個得不償失的誤區(qū)。
公正的評委是比賽成功的保障
本屆比賽的評委都是目前我國最活躍、最有威望的指揮家,他們基本代表了我國指揮藝術和指揮教學的最高水平。在這些評委中,鄭小瑛是廈門愛樂樂團藝術總監(jiān),是我國老一輩指揮家的楷模;俞峰是中央歌劇院院長、藝術總監(jiān),中國指揮協(xié)會會長;張國勇是上海歌劇院藝術總監(jiān),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譚利華是北京交響樂團團長、音樂總監(jiān);李心草是中國交響樂團首席指揮,韓國釜山交響樂團音樂總監(jiān)兼首席指揮,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教授。唯一不是指揮家的梁大南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北京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中央音樂學院小提琴教授。
本屆比賽評委會中的最佳亮點是俄羅斯指揮大師羅日杰斯特文斯基。他是當年李德倫的好友,李德倫留蘇時的老師阿諾索夫的兒子,也是鄭小瑛留蘇時的授課老師。羅日杰斯特文斯基具有極高的國際威望,是世界上現(xiàn)存的、為數不多的老一輩指揮大師中的杰出代表。此次出任比賽的評委會主席,他不顧八十一歲的高齡,每日坐在評委席上認真觀看選手們的比賽,還抽空舉辦了一次公開大師課。羅日杰斯特文斯出席本屆李德倫指揮比賽并擔任評委會主席,不僅是對他逝去老友的極大緬懷,也是對這次比賽的充分肯定與莫大支持。
本屆比賽的評委是公正的,他們的工作是嚴肅認真的。對待每一位選手的表現(xiàn),評委們都仔細地觀察,認真地評議,力爭做到嚴格把關、客觀公正。對于本屆比賽的最終結果,人們普遍認為是謹慎而負責任的,比賽第一名的空缺,正是秉承了嚴肅公正,寧缺勿濫的原則,這樣的結果,對于每一位參賽選手來說,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事實。對于李昊冉的評議,評委們的意見高度的統(tǒng)一,雖然每個人都感到很遺憾,但卻仍然以實事求是為準,沒有任何“網開一面”的表示,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騰飛之前的孕育與積淀
本屆比賽除決賽的三名選手外,還有三人進入復賽,他們是來自中央音樂學院的賴嘉靜,來自美國科蒂斯音樂學院的錢駿平和來自中央音樂學院的丁毅。這三位選手也都有著扎實的專業(yè)基本功和不同程度的指揮才能。
然而,本屆比賽并不是一屆明星閃耀的比賽。綜觀比賽的全過程,沒有出現(xiàn)令人驚訝的天才火花,這也許就是指揮藝術的特殊規(guī)律,或許是中國指揮藝術后備力量真實現(xiàn)狀的體現(xiàn)。盡管焦陽、景煥、李昊冉等人在比賽中表現(xiàn)出了令人欣喜的專業(yè)能力,但他們的身上仍有許多缺點和不盡完善的地方。比如焦陽,他的表現(xiàn)雖成熟穩(wěn)健,但缺乏鋒芒畢露的果斷感和敏銳的“霸氣”;景煥雖然很細膩,指揮作品時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動作有些程式化,音樂表現(xiàn)幅度不夠,整體上還有較強的“學生味兒”;李昊冉前面已經說得很多了,此處不再贅述。總之,選手們的表現(xiàn)給人們的感覺是基本功好,排演規(guī)格高,但沒有超強的駕馭力,也沒有令人為之驚嘆的感召力,距離真正的指揮家標準還有不小的差距。
此外,本屆比賽參賽人數太少,且選手多為在校就讀的學生(少數人曾在國外一些樂團中兼職),這樣的比賽多少給人們帶來了學生比賽的印象。真希望以后這個比賽能夠成為國際比賽,使一些在樂團中任職的青年職業(yè)指揮家來到參賽的陣容中,這樣不僅提高了比賽的專業(yè)規(guī)格,也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出年輕指揮家的真實水平。
萬事開頭難,這是李德倫大師的女兒、本屆比賽的重要籌劃者之一、大提琴演奏家李鹿老師的話。我很理解和贊成這句話,第一屆李德倫全國指揮比賽盡管還有諸多需要改進之處,但它畢竟成功地舉辦了,而且還在我國音樂界和指揮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已經是一件值得夸耀的盛事了。今后,相信在文化部相關領導的關懷下,在指揮界乃至音樂界諸多同仁的努力下,這個以李德倫大師的名字命名的指揮比賽,一定會越辦越好,最終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國際指揮大賽。
騰飛之前的孕育與積淀,這是我對本屆比賽印象的一個形容。盡管比賽中沒有出現(xiàn)人們所希望看到的“天才之星”,但選手普遍基本功好,技術全面,對樂團的掌控力提高,這些都是很好的“預兆”,也是一個量變的過程。而一旦量變發(fā)展到質變的程度,那就是騰飛的開始。到那時,我國的指揮“天才之星”一定會橫空出世,成為國際樂壇上的真正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