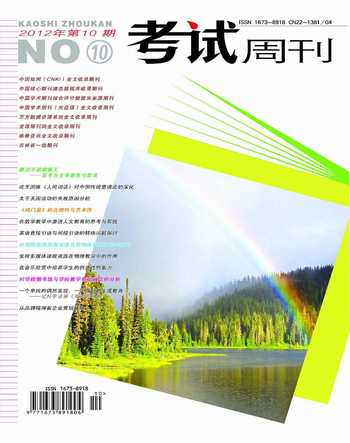論王國維《人間詞話》對中國傳統意境論的深化
李姍姍
摘要: 意境論發端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至唐代正式形成,經過司空圖、嚴羽、王夫之、王士禛等人的推動,含義日益豐富,適用范圍也更加擴大。近代以來,王國維集其大成,開拓了意境論的新領域。本文從“境界說”、“造境”與“寫境”、“有我之境,無我之境”三個方面論述王國維如何發展、深化中國的傳統意境論這一問題。
關鍵詞: 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國傳統意境論深化
意境是中國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藝美學范疇,意境論發端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至唐代正式形成,經過司空圖、嚴羽、王夫之、王士禛等人的推動,含義日益豐富,適用范圍也更加擴大,到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它標志著意境論發展的新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征是傳統意境論的深化、系統化,同時又融進了歐洲的近代哲學、美學、詩學成分,具有中西會合的特征,反映出中國現代美學所有的品格。
王國維一生著述頗多,其中《人間詞話》以論詞為主,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王國維的文學理論思想,繼承了中國古代文論傳統,又吸取了西方美學成果而自成體系。
一、“境界說”
王國維文學理論的核心是“境界說”,他在《人間詞話》開篇就旗幟鮮明地提出:“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覺者在此。”他對此也頗為自負地說:“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到其面目,不若鄙人捻出‘境界二字,為探其本也。”使得眾說紛紜的“意境”探討根植于“本”的求索上而不是“末”的玩味上,王國維的“境界”使人注重于美的本質屬性,使人從觀賞而深入到追究本質,使空靈蘊藉的回味找到具體可感的形象實體。
王國維所標舉的“境界”有特殊的含義,《人間詞話》第六、七兩則作了如下說明:“境非獨為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分析這兩則話,有三層意思:第一,“境界”是情與景的統一;第二,情景需真;第三,“真景物,真感情”得以鮮明真切地表達。因此“境界”乃是指真切鮮明地表達出來的情景交融的藝術形象,這主要是側重于作者的感受和作品的表現兩個方面。
在《詞話》第三十六則后,王國維又連續使用了“隔”與“不隔”的概念,對“境界說”又偏重于從讀者審美的角度加以補充。不論是“寫情”還是“寫景”,凡是直接能給人以一種鮮明、生動、真切感的,皆為“不隔”;反之,在創作時感情虛浮矯飾,遣詞過于造作,破壞了作品的意象的真切性,這就難免使讀者欣賞時猶如霧里觀花,產生了“隔”或“稍隔”的感覺。“隔”與“不隔”的關鍵還是在于作品本身是否真切地表達了“真感情、真景物”,使其內涵覆蓋到作者、作品、讀者三個方面,更加完善。
他對“意境”之“本”——“情”、“景”作了新的明確界定。他指出:“景”、“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是“客觀的”、“知識的”;“情”為“吾人對此種事實之精神之態度”,是“主觀的”、“感情的”。這一解釋吸取了西方的美學觀念,既強調了“意境”之“本”,又包容了“意境”之“末”,照顧到了作者的體驗、作品的表現、讀者的感受等方方面面,所以比之“興趣”、“神韻”諸說更為切實,更為全面。
二、“造境”與“寫境”
王國維《人間詞話》說:“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自然中之物,互相關系,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系,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王國維把境界區分為“造境”和“寫境”兩種不同的形態,“造境”即虛構之境,“寫境”即寫實之境,然而“大詩人所造之境”仍然深深地植根于自然人生的土壤之中,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寫實之境也不能照搬照抄自然人生,而必須用先驗的審美理想去揚棄生活中“關系限制之處”,加以提煉、改造,要用詩人的審美理想來補充和改造自然人生,王國維對這兩種不同創作方法的特點、區別和聯系作了精辟的論述,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作出了新的貢獻。
三、“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
王國維意境論中最具特色的是他對“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闡揚,它的價值絕不在于對意境的分類,而是對主體性的縱深的探析,它與民族美學的根本特色是相貫通的。
“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不是指在詩中是否直接出現“我”,也不是指詩中直接抒發詩人的思想感情,或隱蔽婉曲地抒情,而是從詩歌創作中主體與客體的兩種不同的關系上來劃分的。“有我之境”是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著對立的關系,而“無我之境”則是主體與客體的忻然遇合、圓融一體的關系,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無我之境”,即王國維說的“優美之感情”,在此境界,我與外物化而為一,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物我相忘,心物相化,完全處于一種無利害沖突的超脫寧靜的狀態,所以這里的“無我”就是不執著于一己的窮通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我相忘,無私無欲的靜穆恬淡的心境,達到古典的和諧之美。所以說是“人惟于靜中得之”,“靜”就是指創作者心境的靜穆、和諧。
“有我之境”發自“壯美之感情”。這是在物我矛盾沖突的狀態下,“我”在痛苦、震驚、彷徨、抑郁之際,產生出悲劇情緒。在激烈的心靈的沖突(“動”)之后,達到情緒的“凈化”,產生順其自然的達觀心境(“靜”)。這種“由動之靜”的審美過程,反映出中國古代壯美、崇高審美范疇的特點,即有情感、情緒的激動、沖突、對立,而終歸于靜穆飄逸的和諧之美。同時又得力于歐洲文藝心理學的分析,指出動和靜的相對性是心理現象。“動”是情感極動,產生強烈的動力、張力的表征;“靜”則是在情感的強烈的沖擊之后,漸趨平緩,而潛入心靈深處,呈現出靜默和諧的心境。
“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以我觀物”與“以物觀物”,“壯美”與“優美”之說,都只是相對而言,在實際的文藝創作中很難截然劃分,其意義不在于為意境分類,而是它確實總結了中國詩歌創作中主客體結合的兩種基本方式:借景抒情與緣情寫景的分野。這對我們理解中國古代詩歌創作規律有極大的啟發意義。
我們結合王國維的藝術思想傾向來看,他更偏愛“無我之境”。“無我之境”是運用叔本華的“唯意志論”來觀察萬物,他認為“我從兩個方面認識自己,即為意志和肉體”,“意志是我真實的自我,肉體的表現”。王國維把“我”分為兩個:精神的自我和肉體的自我。他追求的是精神的自我,是“求生的愿望”。所以王國維在一種審美靜觀的狀態下,把人格物化了,變成了物我一體,以此求得意志的自由,精神的解脫。
王國維更向往禪境的解脫,這與司空圖、嚴羽、王士禎一脈相承。他們都推崇“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認為理想的詩境是“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在文學欣賞方面他們所推崇的大多是具有禪境的詩人、詩作,如王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劉若虛“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都是詩境與禪境相合之作,同屬“以物觀物”的“無我之境”。
四、結語
中國傳統意境論者,從皎然的“境象”說,王昌齡的“三境”說,司空圖的“韻味”說,嚴羽的“興趣”、“妙悟”說,王士禎的“神韻”說,直至王國維的“境界”說,一脈相承,都是崇尚禪境,推崇超脫空靈,靜穆悠遠的詩風,這是晚唐宋元以來的詩歌傾向,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意境說才興旺發達起來。這是意境論的特色,也是它的一個歷史偏向。
王國維作為中國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學思想家,他第一個試圖把西方美學、文學理論融于中國傳統美學和文學理論中,構成新的美學和文學理論體系,他的《人間詞話》是對中國傳統意境論的深化,可以說他既是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理論的集大成者,又開中國現代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先河,在中國美學和文學思想史上,他架起了從古代向現代過渡的橋梁,起到了繼往開來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施義對.人間詞話譯注[M].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
[2]施義對.人間詞話譯注[M].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
[3]周錫山.王國維文學美學論著集[M].北岳文藝出版社,1987.
[4]姚柯夫.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M].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5]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M].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
[6]繆鉞.王靜安與叔本華[M].上海古跡出版社,1982.
[7]周策縱.論王國維人間詞[M].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6.
(作者系中國石油大學古代文論專業在職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