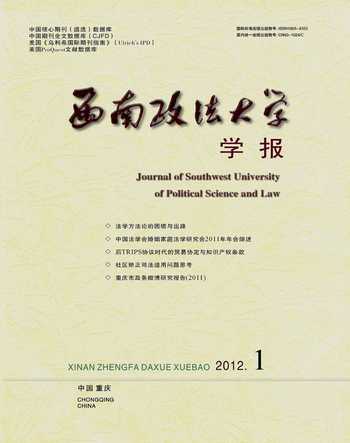論美國檢察官的起訴不當
劉國慶
摘 要:美國檢察官在司法實踐中存在一些起訴不當的做法,危害極大。美國檢察官起訴不當行為的出現原因多元化,其中最為突出的因素有三。目前,美國正積極地推動從三個方面入手來遏止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我國也存在一些類似的問題,認真地審視美國的問題可以為中國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思路。
關鍵詞:起訴不當;正當程序;豁免權;報復性起訴;裁量權
中圖分類號:DF73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1.12
前言
所謂起訴不當是指“檢察官的不適當或違法行為,比如檢察官試圖回避一方當事人證據展示的要求或試圖去說服陪審團對被告人作出錯誤的定罪。假如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導致誤判,根據禁止雙重危險條款之后的起訴行為是禁止的。”[1]美國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的外在表征具有多樣性,歸納起來主要有七種。檢察官的起訴不當危害極大,既有違檢察官原本應恪守的客觀性義務,有悖程序正義,也容易導致冤假錯案。美國理論界認為檢察官起訴不當的產生主要因素在于現有的規范檢察官的倫理道德規范存在缺陷,難以發揮實質性的指導作用,檢察官所享有的裁量權過大趨于極端化,難以有效制約,以及現有歸責機制存在不足,運轉不靈,難以對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真正發揮威懾懲罰作用。為此,美國正積極地有針對性地從上述三個方面著手進行制度改革以遏制與減少檢察官起訴不當行為的發生。反觀我國,檢察官也存在若干起訴不當問題,危害不小,應引起足夠的重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通過對美國問題的探討能為中國相關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資借鑒之處。當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望學界同仁予以批評指正。
一、美國檢察官起訴不當行為類型及危害
截至目前,在司法實踐中,美國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具有多樣性,本文難以一一列舉,筆者認為以下幾點表現得尤為突出,需要予以格外的關注:
(一)使用偽證
在美國檢察官所有的起訴不當行為中最主要的,也是首先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確定的要數檢察官明知是偽證而故意使用以獲取對被告人的定罪目的。法院認為檢察官故意使用偽證以實現對被告人定罪之目的剝奪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賦予被告人的獲得正當程序保障的權利。關于檢察官蓄意使用偽證而指控被告人的諸多案例中,最為著名與經典的要數1935年的穆尼訴霍羅汗(Mooney v.Holohan)一案。Mooney v.Holohan,294U.S.103,112(1935).在該案中,托瑪斯?穆尼因為1916年的謀殺案而被判處死刑。在庭審中,檢察官提交了涉嫌偽證的證言。被告人因此提出案件重審的動議,加州法院拒絕了被告人的請求。之后,穆尼試圖尋求獲取加州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加州最高法院最后維持原判。穆尼轉而向聯邦法院尋求救濟,在聯邦法院獲得救濟的意愿受阻后,被告人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聽取了被告人的訴求。在伊始階段,代表國家利益的美國首席檢察官承認在庭審中檢察官提交并用于對被告人穆尼定罪的證人證言是偽證。然而,既然代表的是國家利益,該首席檢察官指出明知而故意使用偽證并沒有侵犯正當程序,并對其主張進行解釋,他指出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本身并不能自動獨自地剝奪被告人所享有正當程序的權利,除非被告人被剝奪了被告知以及獲得聽審的權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并不贊同該首席檢察官對正當程序性權利的理解與詮釋,聯邦最高法院主張獲得法庭審判的權利本身就內含該審判免受明知偽證而故意使用不當影響的權利,對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指出“我們不能認同該首席檢察官對正當程序作出如此狹義的理解。在維護民眾自由而反對政府對公民合法權利剝奪方面,正當程序體現了基本的正義理念。正當程序要求的并非僅僅對公民進行告知以及獲得聽審的權利,假如政府試圖以所謂的審判為名,實際上是通過蓄意地提交使用偽證以欺騙法庭與陪審團以達到對公民進行定罪,剝奪被告人人身自由之目的。那么政府以此等方式對被告人定罪將其監禁就與司法正義的基本要求完全相悖,格格不入,此舉無異于恫嚇與威脅。檢察官乃政府利益的代表,其起訴行為如行政官員執法一樣構成政府行為,理所當然地應歸入美國聯邦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范圍,受其規制。該修正案適用于政府的任何行為,無論是立法行為,司法行為,亦或行政行為。”由穆尼一案可以看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于檢察官在案件起訴中使用提交偽證的做法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此舉違反了正當程序條款的要求,剝奪了被告人有權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
(二)布蘭迪義務之違反
此種起訴不當行為是指檢察官將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在證據展示時故意藏而不露,旨在實現對被告定罪之目的。在1963年的布蘭迪訴馬里蘭州(Brady v.Maryland)一案中Brady v.Maryland,373U.S.83(1963). ,馬里蘭州檢察機關起訴布蘭迪及其同伙涉嫌謀殺罪。庭審之前,檢察官應布蘭迪辯護律師的請求向其展示了布蘭迪同伙的部分法庭外陳述。但檢察官對布蘭迪同伙的殺人供述在庭審中隱而不發,布蘭迪對此毫不知情直至初審被判決死刑后方如夢初醒。布蘭迪于是就檢察官隱藏證據行為提出上訴,馬里蘭州上訴法院維持初審判決,僅就量刑問題發回重審。聯邦最高法院在其判決中指出“檢察官起訴無論是出于善意亦或惡意,對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隱而不發有違正當程序,即使被告人沒有提出證據開示的請求,檢察官仍應責無旁貸地向其展示任何可能為其開脫罪行的證據資料。如果一項證據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減輕他的處罰,在被告人的請求下,而檢察官拒不出示的話,這將使檢察官扮演一個不遵循公正標準的角色……。”在1972年的基格里奧訴美國(Giglio v.United Sates) 一案中Giglio v.United Sates.405U.S.150(1972).,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將檢察官所負有的上述布蘭迪證據開示義務(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拓展延伸至可以用作彈劾檢控方證人之可靠性的證據,盡管該證據不會導致被告人的無罪釋放。更為重要的是,在1976年的美國訴阿格斯(United States v.Agurs)一案中United States v.Agurs,427U.S.97,110-111(1976).,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裁決中指出,檢控方有義務將其手中所持有的有利于被告人的“重要性”(materiality)的證據主動向辯護方展示而非消極地應后者的要求被動展示。當然,檢控方所負有的布蘭迪證據展示義務并非毫無邊界,也有一些限制,比如,檢控方沒有義務去找尋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即使之后發現了此類證據也并不違反布蘭迪義務。此外,檢察官也沒有義務向被告人展示那些已為其知悉或持有的有利于自身的證據。當然,對于布蘭迪證據展示義務最為重要的限制是檢控方的證據開示義務僅限于那些“重要性”(materiality)的證據,所謂的重要性并非僅指那些具有關聯性的證據,而且還指那些人們合理地認為將對本案的結果產生舉足輕重作用的證據。時隔30多年后,上述布蘭迪案判決精神在1995年的凱爾斯訴懷特里(Kyles v.Whitley)一案中Kyles v.Whitley, 514 U.S.419(1995).繼續得以弘揚,并將有利于被告人的直接證據與質證證據也納入了證據開示的范圍。聯邦最高法院更是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被告人是否因證據而獲得不同判決,而在于其是否理解缺少這些證據能否產生值得信賴的判決。
(三)陪審團之選拔
在陪審團成員的選拔問題上,美國檢察官也經常存在不當行為。盡管自從1879年美國便制定法律明確規定所有美國公民只要符合條件均具有擔任陪審員的資格,而不分種族及其它。但在司法實踐中,美國檢察官仍有一些途徑基于種族的因素而將部分人排除在外以實現對被告人定罪之目的。具體來講,在陪審員的挑選過程中,控訴方與被告方均有權基于某種事由去挑戰陪審員的選擇,有時還可以運用無因回避的權利(Peremptory challenges),尤其是后者。雙方均可以運用此項權利基于種族的考量而將有關陪審員剔除在外。實踐中,檢控方經常使用此種策略將部分人排除在陪審團之外。為了對抗檢控方此等不當做法,在1965年的巴特森訴肯塔基(Batson v.Kentucky)一案中Batson v.Kentucky,476U.S.79,96-98(1986). ,被告是一名非洲裔美國人,被指控犯有夜盜與接受贓物罪。在遴選陪審員的過程中,檢察官用其無因回避權而排除了候選人名單上的全部四位非洲裔美國人。被告人對此提出異議,法官在裁決中指出每一方當事人均可以使用無因回避權而排除他們想要排除的任何人。最后,被告人由一個全部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審判定罪。案件最后被提交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對被告的定罪并首次允許被告人挑戰檢控方運用無因回避而挑選的陪審團。根據巴特森一案的裁決,當被告人基于種族或性別歧視為由而挑戰檢察官對于陪審員之排除要求時,被告人必須首先確立一個表面成立的證明,表明足以引起檢察官根據種族而行使其無因回避權的推論。一旦被告人確立了表面上成立的證明,責任就轉移到檢控方,檢察官就必須為他行使無因回避權提出一個中立的解釋。一旦檢察官提供了中立的理由,那么初審法官就必須確定被告是否就所有的相關事項履行了證明有意歧視的責任。如果初審法庭認定檢察官違法,通常給予被告人以適當的救濟,比如將被檢察官不當排除的陪審員恢復到候選人名單上,或用一個新的候選人名單重新開始。當然,盡管在巴特森一案中給予被告人此項程序性權利,但無因回避的存在仍為那些肆無忌憚不講道德的檢控方基于種族或性別因素考量而將有關陪審員剔除在外大開方便之門。
(四)選擇性起訴或報復性起訴
在美國1986年的美國訴阿姆斯壯(United States v.Armstrong)一案中United States v.Armstrong,517 U.S.456,464(1996). 確立了禁止不合理的選擇性起訴,法院在其裁決中指出“檢察官是否起訴的決定不能基于種族、信仰或其他專斷的分類這樣不合理的標準。”在1985年的Wayte v.United States一案中Wayte v. United States,470 U.S.598,608(1985).,法院在裁決中指出也不能因為一方當事人行使了成文法或憲法所保護的權利而作出起訴或加重起訴指控的決定。美國最高法院之所以作出如此禁止性的起訴規定是出于維護與捍衛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的需要;在涉及聯邦政府的情形下,這種禁止性的規定出于維護第五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的內在需要。但遺憾的是,選擇性起訴的主張難以證明,法定證明標準太高,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Reno v.American-Arab Anti-Discrimination Comn一案中Reno v.American-Arab Anti-Discrimination Comn, 525U.S.471,489(1999). 指出“選擇性起訴的主張是非常少見的……我們已經強調,要求刑事被告人出示‘清楚的證據取代檢察官合法行事的推定,證明這個主張的標準非常難以達到。”檢察官提出報復性起訴有違正當程序的內在要求應被禁止。相對于選擇性起訴的處理,美國最高法院在特定情形下給予了主張報復性起訴的被告人“報復推定”的利益,據此,有效地將證明負擔轉移到了檢控方,檢察官必須證明自身缺乏報復性動機。美國關于檢察官報復性起訴問題的經典案例是1974年的布萊克治訴伯里(Blackledge v.Perry)一案Blackledge v.Perry,417U.S.21(1974).。在該案中,被告因攜帶致命武器襲擊而被定罪,這是輕罪。被告人根據州法律要求在更高級別的法庭申請重新審判的權利。在第二次審理之前,檢察官調查并取得一項新的公訴書,指控該被告人以殺人為目的而攜帶致命武器進行襲擊,這是一項重罪。被告人主張檢察官的重罪指控是對他行使合法權利的懲罰,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美國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人的裁決,盡管被告人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檢察官提出更為嚴重的指控是因為他行使重新審判的權利而對他進行懲罰。最高法院裁決的根據是,綜合案件各種情況,認定檢察官具有報復的“現實可能”。最高法院指出其如此裁決的理由并非“報復性動機必須不可避免地存在”,而是擔心這樣的動機“可能會違憲地阻嚇被告人行使他的成文法權利。”
(五)不允許的評論或在庭審中試圖導入不適當的證據
美國檢察官起訴不當行為外在表征具有多樣性,其中最具有可視性的要數檢察官在正式庭審中所發表的不當言論,此舉嚴重地損害了正當程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檢察官的不當言論也是最為寬泛,最難界定,最難一一列舉以及最難評價的。美國法庭也曾努力地試圖去裁決檢察官的言論是否有違正當程序。在一些其它案件中,美國法院還發現檢察官還存在另外一種起訴不當行為,即檢察官在庭審中提交一些不具有可采性的證據信息,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證據信息,比如,檢察官故意將那些已在庭前審前動議階段予以排除的證據在正式庭審中提交出來。美國檢察官的上述不當做法均有可能對陪審團的自由心證造成負面的影響,從而對案件事實作出錯誤的認定。
比如在審前動議階段已被排除的非法證據,假如在正式庭審階段檢察官再次提交出來就是有力的明證,法官將接觸此類非法證據信息,從而對法官自由心證帶來消極負面的干預影響,英美法系國家二員法庭模式阻擋不良污染信息的有效渠道將嚴重受損。美國證據法學者達瑪斯卡教授曾就此問題指出英美法系國家通常采取二元法庭,法官可以通過審前動議階段將那些不具有可采性的證據信息阻擋在事實認定者的門外,使那些不具有可采性的證據不在事實認定者的頭腦中留下任何的印記。相反,在大陸法系國家的一元法庭模式下,無法避免被禁止但有說服力的信息的污染,那些被禁止的證據仍對裁判者的思想產生負面的影響,干預自由心證的正確形成,從而誤導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參見:米爾吉安?R?達瑪斯卡.比較法視野中的證據制度[M].吳宏耀,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221;米爾吉安?R?達瑪斯卡.漂移的證據法[M].李學軍,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65-66.)再比如檢察官對于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及被告人罪行的成立與否純粹發表個人的主觀看法與觀點而缺乏一定證據資料的支撐。
(六)違反迅速審判原則的起訴
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賦予被告人獲得迅速審判的權利,一則可以及時有效地發揮刑罰手段對罪犯的威懾效應,二則可以使被告人盡早擺脫訴訟之累,“一方面可以及時將罪犯繩之以法,而產生刑罰威懾功能,另一方面則使無辜之被告,得以早日洗刷罪嫌,還其清白。”[2]美國檢察官也有可能因為不必要的延遲起訴而構成起訴不當行為,由此也就侵犯或剝奪了被告人所享有的獲得迅速審判的憲法性權利。被告人的該項權利是在1967年的科勞佛訴北卡萊羅納州(Klopfer v.North Carolina)一案中確立的。
Klopfer v.North Carolina,386U.S.213,223(1967). 在衡量被告人的此項憲法性權利是否遭受檢察官的侵犯時,法官通常要考慮四個方面的因素,這是在1972年的巴科訴溫果(Barker v.Wingo)一案中確立下來的Barker v.Wingo,407U.S.514,531(1972).,它們分別是延遲的時間長度,哪部分的延遲是由檢察官的過錯所導致的,因為上述延遲給被告人造成的損害如何,以及被告人在何種程度上主張自己迅速審判的權利。當然,盡管如此,由于上述對于檢察官延遲是否屬于必要合理的亦或不當的由于法官采取的是一種衡量測試之方式,因此本身充滿了變數與不確定性,這就為檢察官故意延遲起訴而不被發覺或僥幸逃脫懲罰制裁提供了一定的活動空間。
此外,檢察官在最后陳述(closing statement)或開場白(opening statement)之時也有可能訴諸于情感希望引起陪審團的共鳴以博取陪審團的同情,有時檢察官的陳述已遠離該制度設置的初衷,比如有的檢察官要求陪審團應設身處地地為被害人著想或大談特談社區的犯罪控制問題等比較寬泛的話題均是不允許的,屬于起訴不當行為。
美國檢察官的上述起訴不當行為所帶來的危害是巨大的,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有損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林鈺雄教授曾就何謂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作過比較全面與形象的闡述:“檢察官對于利于與不利于被告之事情要一律注意……,在刑事訴訟法上,有法官同為客觀法律準則及實現真實正義的忠實公仆,毋縱之外還要毋冤,除暴之外還要安良,并非也不該是片面追求攻擊被告的狂熱分子。”[3]美國早在1816年田納西州的一份法院的裁決中就指出,“檢察官在人民與政府之間進行裁決,是權利的保護者,他不應使無罪者受到折磨或滋擾,也不應讓應被起訴的人得以逃脫;他追究犯罪;他保護無罪者;他判斷情勢,并根據個案中的實際情況保護公共福祉與公民的安全,使其免受傷害;當并非為了公共利益時,應避免利用個人的熱情與惡意;他在需要時會使用合理的裁量權實現社會正義。”
Fout v.State,4Tenn.98(1816). 在1935年的伯格訴美國(Berger v.U.S)一案中Berger v.U.S,295U.S.78,88(1935). 對何謂美國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作出了最為經典的詮釋與論述:“美國檢察官代表的不是訴訟中的普通一方,而是國家政權,他應該公平地履行其職責;檢察官在刑事起訴中所尋求的利益并非勝訴,而是實現正義。因此,在一種特殊與有限的意義上講,檢察官是法律的仆人,既不能放縱犯罪,亦不能冤枉無辜是其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雙重目標。檢察官可以而且應該堅定積極地進行控訴。盡管他可以重拳出擊,但卻不能隨意地犯規出拳,避免使用可能產生錯誤定罪的不當方法追訴犯罪,用盡所有合法手段實現司法的正義乃屬于檢察官職責之所在。”司法實踐中,美國檢察官之所以采取起訴不當行為的直接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將被告人定罪,對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通常閉而不談,百般掩飾,對于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不擇手段,有時在證據展示階段深藏不露以達出奇制勝之效果,對于被告人的合理訴求打擊報復以及威脅偽證等都呈現出美國檢察官濃厚的追訴傾向,置案件的真相與被告人的人權保障于不顧,完全將自己等同于民事訴訟的一方當事人,與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要求完全背道而馳。
其次,有損政府的誠信及法治的權威。檢察官的起訴不當問題也損害了社會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代表政府的公訴機關為了取勝可以不擇手段,就個案來講,公訴機關可能是贏家,但從長遠來講,則是最大的輸家,因為它失去了民眾對于司法制度的信任,失去了人們對于政府的信任。此外,政府扮演著教育國民的角色,公訴機關為了取勝而無所不用其極會錯誤地引導人們競相模仿,對一個國家的法治造成嚴重的傷害,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劉易斯?布蘭迪(Justice Louis Brandeis)曾指出:“我們的政府是一名有影響力且無所不在的老師。無論是好是壞,他都是全民的榜樣。犯罪是具有傳感性的,如果政府本身以身試法,那就會滋生公眾對法律的蔑視,就等于鼓勵每一個人均無需守法,鼓吹無法無天。這等于宣布在執行刑事法律時,目的可以使手段合理正當化,就等于昭示人們,為了將一個事實有罪之人繩之以法,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甚至犯罪,這將帶來極其危險可怕的后果。”
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277U.S.438,468(1928).值得一提的是布蘭迪大法官的此番言論是針對執法人員,尤其是警察非法取證而言的,但筆者認為政府的教育角色對于檢察官的公訴行為也同樣適用。 “沒有什么比政府自身無視法律的存在而故意以身試法能更快地摧毀政府的存在了。”
Mapp v.Ohio,367U.S.659.再次,導致冤假錯案的出現。早在13世紀英國著名的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就曾指出:“讓十名有罪者逃脫也勝于讓一名無罪者受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的溫希普一案中曾指出:“我國體制的基本價值觀認為錯誤地判定一名無辜者有罪要比錯誤地釋放一名有罪者要糟糕得多。”盡管如此,美國在刑事訴訟中因為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而導致的冤假錯案仍不在少數。自從1935年的美國伯格(Berger)一案以來,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被視為導致冤假錯案發生的最為常見的主導性因素之一。根據美國2000年的一項研究,有62人得益于DNA技術的使用而無罪釋放,其中有26個案件
中存在一定程度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在隨后對由于DNA技術的使用而無罪開釋的70起案件
中,其中34起案件存在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4]403。
最后,有損于程序正義。美國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對正當程序造成嚴重的損傷,比如檢察官以威脅的方式獲取不利于被告人的證言以達到對被告定罪之目的對程序的正當性造成了傷害,檢察官違反證據開示義務打算在法庭之上進行突然襲擊損害了公訴機關與辯護方公平競爭與理性對抗之精神,檢察官為了取勝在陪審團的人選上大做文章對被告人有權獲得公正的審判造成負面影響等。
二、 美國檢察官起訴不當行為的原因及矯治
從上文所述可見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外在表現形態具有多樣性,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國檢察官如此而為呢?筆者認為主要為規范檢察官職業行為的倫理道德規范存在缺陷,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以及對于檢察官起訴不當行為歸責機制的不足三個方面的因素
筆者認為美國檢察官起訴不當行為的產生還與當事人訴訟模式下庭審采取司法競技主義不無關聯。司法競技主義主張當事人之間平等對抗及理性交流,認為真理越辯越明,不可否認該制度存在諸多優勢,但此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在此制度下,當事人的主要目的在于贏得訴訟的勝利,而不是發現案件真相,即檢察官以贏得訴訟的最終勝利為最主要的目的。”由此導致許多負面效應,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就是容易導致檢察官角色的變更,在一造當事人與司法正義的捍衛者之間搖擺不定,最終通常會滑向前者,為了贏得訴訟的勝利而不擇手段,起訴不當便帶有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缺乏透明度及有效約束。美國學者瓊?雅各比曾就美國檢察官巨大的裁量權指出:“美國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在三個方面已經成為不可爭辯的了:他有權單獨決定是否提起刑事訴訟;他單獨決定在何種程度上指控某個人;在他認為應該或必須終止訴訟時,別人不能加以阻止。”[5]再比如美國學者博頓?阿特金斯在談及美國檢察官所享有的不起訴裁量權時曾指出:“然而,我想知道為什么一名美國檢察官——比如說一名縣檢察官有自由裁量權來決定不起訴,即使有明確的有罪證據。也許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政治的影響。而且,他也不必向任何人說明其已經查明的案情和已經收集的證據,也不必向任何人說明他為何對法律做出如此解釋,更不必向任何人說明為何在此困難的政策問題上采取此種立場。”[6]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猶如一劍兩刃,檢察官有了靈活處置權,有助于實現社會政策及提高訴訟效益,但也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比如引發了檢察官的選擇性起訴及報復性起訴等起訴不當行為。為此,美國采取一些措施以規范檢察官的裁量權,增加其透明度,主要有以下兩點:其一,建議檢察官辦公室使用檢察官手冊,該手冊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一般的社會政策以指導其裁量權;另外一方面,檢察官的工作流程。檢察官手冊旨在引導檢察官裁量權科學、公正地運用以實現司法正義。此外,美國律師協會還建議該手冊的內容應向公眾開放,除非相關事宜涉及機密問題。其二,美國司法部還發行了美國律師使用手冊(USAM)以指導檢察官裁量權的運用,使用手冊對公眾開放。該手冊指出檢察官起訴的總體原則是只要他相信被告人的行為構成了犯罪,且相關的具有可采性的證據將足以將被告人定罪,檢察官就應該起訴,除非檢察官認為:1.起訴不符合既定的社會政策;2.被告已在其它司法區受過有效的追訴;3.目前不存在適當的非刑事替代性措施。除了上述內容外,美國律師使用手冊還給美國聯邦檢察官提供以下七個參考因素以指導起訴工作:1.聯邦執法的優先問題何在。2.被告所犯罪行性質及嚴重程度如何。3.起訴的威懾效果如何。4.被告所犯罪行的可責性如何。5.被告有無犯罪前科。6.被告是否愿意與執法人員或檢察官合作。7.假如被告被定罪,可能的量刑或其它后果如何。8.被告個人的具體情況。除此之外,美國律師使用手冊還規定以下三種因素不得作為檢察官考量是否對被告人提起公訴的參考標準:1.個人種族、宗教、性別、民族、政治派別、個人活動及信仰。2.檢察官個人對于被告的情感,被告的社會關系及被害人的因素。3.對檢察官個人職業或個人情況潛在的可能影響。
其次,規范檢察官的倫理道德規范存在缺陷。從歷史上來看,美國規范檢察官職業行為的道德準則經過一個歷史演化過程。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ABA)于1908年頒布了第一部規范檢察官職業行為的倫理道德規范,該規范指出“美國檢察官的主要職責并非在于對被告人定罪,而在于實現司法正義。”此外,該規范還指出“檢察官故意隱瞞案件事實真相以及將對于那些有助于為被告人開脫罪責的證據藏而不露是應該受到譴責的。”遺憾的是,1908年的規范并沒有就檢察官應如何通過具體的舉措來實現司法正義作出明確的規定。此外,該規范過于簡單含糊難以為檢察官的職業行為,尤其是起訴行為提供有效的指導并進行有效的規制,有學者就此提出批評,“該道德規范如此的含糊不清,如此的模棱兩可以至于對于解決實際問題幾乎毫無任何作用”,以此作為對上述批評的回應,美國律師協會于1969年頒布了模范法典,之后又于1983年頒布了模范法典。1983年的模范法典就檢察官的一些道德規范作出比較明確的規定,內容較以前有所擴充,關于檢察官的道德義務方面有五點比較具體明晰的規定。其主要內容如下:其一,要求檢察官在對被告人提出公訴時應具有合理的根據,具有定罪的可能性。其二,要求檢察官應作出合理的努力以確保被告人已被告知各項權利以及給予合理的機會獲取律師的幫助。其三,不能試圖從那些沒有獲得律師幫助之被告人之處獲取其放棄一些審前重要的權利,比如獲得初步聽審的權利。其四,應及時地將那些可能導致被告人無罪開釋或減輕罪行所有證據或為檢察官所知悉的信息全部向被告人展示,將那些有助于被告人在量刑程序中獲得益處的而又不受到特權保護的為檢察官所知悉的信息向被告人展示,除非檢察官基于保護法庭審判的有序進行等法定事由而免除了上述義務。其五,采取必要適當的措施以防止案件調查者,執法人員以及其他協助檢察官的人員在庭審之外作出一些不適當的言論以消除對正式審判產生不當影響。在1990年,美國律師協會又對檢察官的倫理道德義務附加一條。
“檢察官不得傳喚被告人的委托律師提供關于其委托客戶過去或現在的證據,除非在有限的法定情形下。”美國于1994年又頒布了規范檢察官的模范法典,課以檢察官的倫理道德義務增加至七條。
在原有基礎之上又增加一條,即“檢察官不得在庭審之外發表不當言論以加深民眾對被告人的譴責與憎恨。”規范檢察官職業行為的倫理道德規范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演變,盡管取得一些進步,但總體上仍難以滿足司法實踐的客觀需要,難以對檢察官的起訴行為提供比較全面的指導以實現司法正義。為此,美國無論是理論界亦或實務界仍在不懈地探索完善。
最后,對檢察官起訴不當行為的歸責機制存在不足。在美國,由于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而受到處罰的少之又少,即使是造成冤假錯案,之所以出現上述局面,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檢察官通常享有民事訴訟豁免權,此舉就極大地限制了檢察官對其錯誤行為承擔責任的可能性。其二,美國上訴法院對于此類上訴案件采取了極其嚴格的審查標準,很少基于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而推翻原判決,通常將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歸同于無害錯誤(harmless error)。所謂“無害錯誤”按照美國權威詞典《布萊克法律詞典》就是指“錯誤并不影響一方當事人的實質性權利與案件結果,該錯誤并不構成案件重審的事由。”(參見:Bryan A.Garner.Blacks Law Dictionary[K.] 8th ed.West Group,2007:582.)根據《元照英美法詞典》之規定,所謂“無害錯誤”就是指“任何輕微的、形式上的或純理論上的、沒有侵犯當事人的實質權利和對判決沒有影響的或僅有極小影響的錯誤。它不構成準予對案件重新審理,或撤消陪審團裁斷,或撤消、變更法院判決或裁定的根據。”(參見:薛波.元照英美法詞典[K].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28.)我國臺灣地區學者王兆鵬教授認為“無害錯誤”的法理基礎有三:其一,證據法或訴訟法之設計并非完美無暇,不可能完美地不發生任何微錯誤;其二,上述審查程序不完美;其三,節省司法資源。認為假如不分錯誤對判決結果的實際影響如何而一律發回更審,會造成有限司法資源的浪費。(參見:王兆鵬.刑事訴訟講義[M].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740-741.)這也助長了檢察官的囂張氣焰,使其在起訴中有恃無恐,起訴不當行為頻發。為此,美國學界普遍主張對于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應采取一種更為前攝性的做法,而非滿足于現狀,或一味地回避。有學者建議一旦法院法官或上訴法院發現檢察官存在起訴不當行為就應對檢察官行為進行獨立的調查,倘若認定不當行為存在則對相關責任人實施必要的處罰[4]427。相反,假如對于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視而不見,坐視不管,聽之任之,不施加任何的處罰,那么檢察官的上述起訴不當行為將會有增無減而繼續延續下去。
三、 美國檢察官矯治起訴不當行為的啟示
美國檢察官在司法實踐中所出現的上述大部分起訴不當行為在我國實踐中也曾出現或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目前我國檢察官的起訴不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使用偽證。其二,報復性起訴的問題。其三,非法證據的不當導入問題。其四,庭審中的不當言論問題。筆者認為任何公權力機構都不得從自己的非法或不當行為中受益,負責起訴的檢察官更是如此,解決我國上述問題可借鑒美國的有些做法,主要可從以下幾點入手:
首先,制定并完善我國檢察官道德規范。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0年制定并頒布了《檢察官職業行為基本規范(試行)》以指導規范檢察官的行為。從縱的角度來看,這是歷史進步,它有助于規范檢察官的日常工作。但其本身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與美國的相比較,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幾點特色:其一,該檢察官職業行為規范沒有突出“職業行為規范”的特質,更多的是對檢察官提出政治素質方面的要求,政治氣味過濃,更像是對檢察官進行政治教育的教材或文件。其二,喧賓奪主,主題不突出。既然是指導規范檢察官職業行為的就應將側重點放在對檢察官的職業屬性定位及如何具體指導檢察官的具體工作上面,尤其是提起公訴的工作。而反觀我國頒布的基本規范有點本末倒置之嫌。其三,相關規定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過于空洞,不具有可操作性,對于指導實踐中檢察官具體的起訴工作意義不大。總之,我國2010年制定的檢察官職業行為基本規范在規范檢察官職業行為方面作用不大,需要進行重塑以規范我國目前實踐中出現的起訴不當行為,保障起訴工作的正常有序進行。為此,筆者建議在未來的《檢察官職業行為基本規范》中應將如何具體地指導檢察官的各項職業行為,尤其是如何具體地指導其提起公訴方面應有所為而又有所不為列為內容重點并作出比較明晰的規定,此舉可以達到“一箭雙雕”之療效,既可以約束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也可以有效防止上述各類不當起訴行為的發生。
其次,應完善目前的對于檢察官各類起訴不當行為的歸責機制。對于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可考慮內外并舉,對于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可由獨立的調查機構進行調查,在此基礎之上進行處罰,對于檢察官的起訴不當行為不可以“目的之善”為借口而一味地姑息縱容。
最后,可借鑒美國的做法,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指導檢察官進行公訴的指導手冊,并向公眾開放,該手冊應重點闡述檢察官在是否作出起訴決定時應重點考慮哪些具體的因素,而不得考量哪些具體的因素,從而使得檢察官在起訴時有所為而又有所不為。
參考文獻:
[1]Blacks Law Dictionary[K].8th Ed.West Group,2007:1258.
[2]林山田.刑事程序法[M]痹齠┪灝.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86.
[3]林鈺雄.檢察官論[M].臺北: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31.
[4]Peter Jo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ial Misconduct and Wrongful Convictions: Shaping Remedies for a Broken System[J]盬isc.L.Rev.2006,(399).
[5]瓊?雅各比.美國檢察官研究[M].周葉謙,等,譯.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0:37.
[6]楊誠,單民.中外刑事公訴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10.
On Prosecutorial Misconducts of the U.S.Prosecutors
LIU Guo瞦ing
(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China)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osecutorial misconducts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the U.S, which do great harm. The reason why prosecutorial misconducts come into being is diversification, and there are three leading factors. Currently, the U.S. is actively promoting to curb prosecutorial misconducts from the three瞤ronged approach. China also has some similar issues. Taking issues and solutions by the U.S seriously can provide some ideas.
Key Words:prosecutorial misconduct; due process; immunity; retaliatory prosecution; discretion
本文責任編輯:周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