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生產力現代化的本質特征與“未來景象”
董正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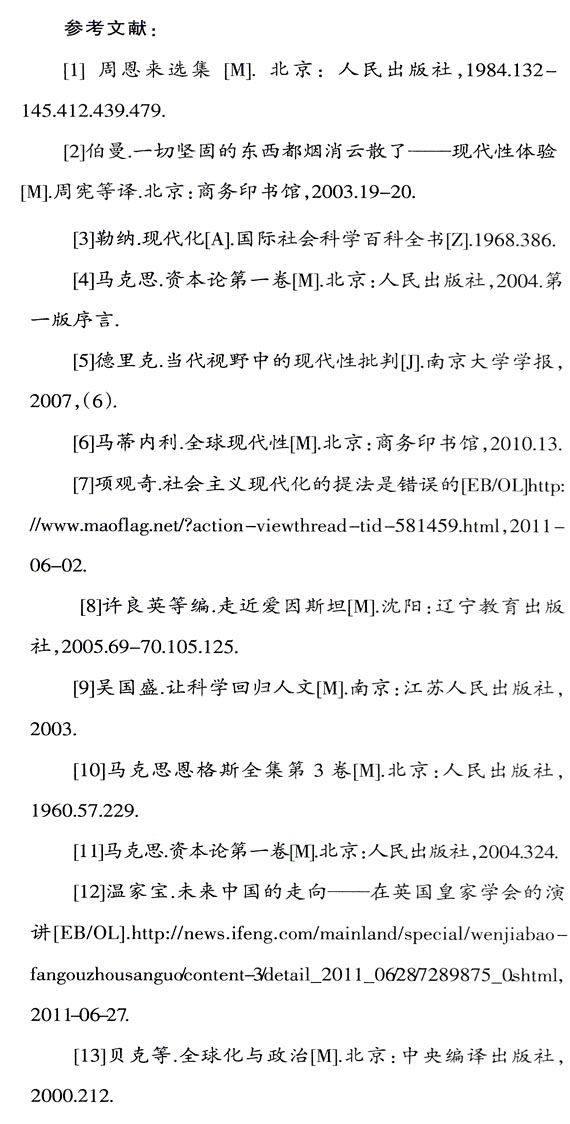
摘要:現代化不是一個從抽象思維中產生出來的理論概念,應當從歷史經驗的角度探尋其本質。現代化不僅僅是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不只是經濟增長,還需包括社會、政治、思想的現代化。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要在社會變革、思想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經濟和政治制度創新、科學技術創新等方面做新的探索。當今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未來前景,是“世界體系”的擴展或曰“全球化”。全球化的大趨勢對國家主權形成沖擊,但主權國家仍然是世界體系的基本結構、基本格局。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和全球化趨勢給中國人帶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然而,來自國外和內部的各種困難、挑戰也將與機遇相伴隨。
關鍵詞:科學技術;生產力;本質;未來景象
中圖分類號:D6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1502(2012)01-0005-07
“現代化”作為一個科學認識和研究的對象,無論其意指一個歷史進程,還是指一種目標、愿景,在中國知識界都經歷了從褒義到貶義、再到褒義的演變過程。在20世紀30年代《申報月刊》組織的討論中,不同政治思想傾向的學者異口同聲地鼓吹現代化,這已為世人所共知。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地將現代化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從1954年到1975年,從第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到第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每次《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出或重申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并且對具體的實施步驟做了越來越詳細的規劃。然而與此同時,“現代化”作為一種理論研究的對象卻一直被視為禁區。在“文革”極“左”思潮的控制下,報刊雜志大批“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宣揚“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甚至要揪出所謂“四個現代化背后”的“黑手”,嚇得人們聞“現代化”而色變,唯恐避之不及,更不要說去研究它了。這種形勢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變。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宣稱國人已經普遍對“現代化”持積極的、贊揚的態度,應當不是妄說。
然而,現代化的本質特征究竟是什么,現代化——或日當今世界發展——可以預見的未來前景如何,卻仍然是一個眾說紛紜、亟待深入探討的課題。把兩個問題作為一個課題,是因為它們相互關聯太密切。簡單地說,即前者決定后者,反過來,后者又能折射出前者。
現代化從來不是一個先驗的從抽象思維中產生出來的理論概念,我們應當從歷史經驗的角度,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層面來考察其內容,探尋其本質。
一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前人對西歐現代化歷史經驗的總結。
有些人至今仍然將現代化看作是虛幻的、未曾發生的歷史,或者只看到它陽光明媚的一面。事實上,正如伯曼所說:“假如我們向前推進100年左右,試圖確定19世紀現代性的主旋律和主音色,那么我們首先會注意到的便是那幅高度發達、明顯可辨、生機勃勃、并由此產生出現代體驗的新景象。在這幅景象中,出現了蒸汽機、自動化工廠、鐵路、巨大的新工業區;出現了雨后春筍般的大批城市,常常伴隨著可怕的非人待遇,……出現了日益強大的民族國家和資本的跨民族集聚;出現了各種大眾群眾運動,……出現了一個不斷擴展的包容一切的世界市場,既容許最為壯觀的成長,也容許駭人的浪費和破壞,除了不容許堅固不變,它容許任何事物。”伯曼所描繪的“19世紀現代性的主旋律”,反映了西方早期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一方面是工業化、城市化,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另一方面是可怕的非人待遇和駭人的浪費與破壞。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有人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德文版)里的一句話“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來說明現代化的涵義,其意在于告訴人們:遲發展國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就是“西化”,世界現代化的美好前景,就是達到工業發達國家已有的“景象”。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從下面的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在這里所“顯示”的,正是包括伯曼所說“可怕的非人待遇”在內的“現代災難”:
……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地對他說,這正是閣下的事情!
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
撇開這點不說,在資本主義已經在我們那里完全確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廠里。由于沒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廠法,情況比英國要壞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
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
很明顯,馬克思在這里表達了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即工業較發達國家顯示的景象或伯曼所說的“現代體驗的新景象”)的鮮明而尖銳的批判態度。
進一步我們還應看到:迄今已經全面展開的世界性現代化進程,在造就空前未有的歷史大變革的同時,也帶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矛盾和沖突。如同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所寫的:“……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獄。”光明與陰影同時存在,人們必須居安思危。
現代化與“現代性”緊密相連不可分離,二者之間不存在誰代替誰的問題。現代化可以被簡要地定義為“一種創造現代性狀況的過程”,翻而構成現代社會本質特征或日“現代化過程中所具有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的特定形態”的“現代性”,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統一體。二戰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后,現代化進一步向全世界擴展,形成全球化的大浪潮。冷戰結束之際,福山曾預言世界文明的終結——終結于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但更多的人看到的是新的比冷戰更嚴酷的“文明沖突”,而且很快就被一系列全球性的恐怖襲擊和戰爭所驗證。這也正像伯曼所說的:“現代的環境和經驗直接跨越了地理的和種族的、階級的和國籍的、宗教的和意識形態的界限: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現代性把全人類都統一到了一起。但這是含有悖論的統一,一個不統一的統一:它將我們所有的人都倒進了一個不斷崩潰與更新、斗爭與沖突、模棱兩可與痛苦的大漩渦。所謂現代性,也就是成為一個世界的一部分,在這個世界中,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
充滿矛盾和變動不居,可以說是迄今為止世界現代化的本質性特征。一方面是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另一方面,剛剛擺脫舊的折磨,馬上又要體驗新的痛苦。整個世界正在面臨規模空前的風險和危機,包括各種經濟、政治、社會風險與危機,能源危機,生態危機和生化災難,核戰爭恐怖和災難,全球化大趨勢下新的失落和認同危機,等等。
正因為現代性充滿矛盾,充滿變數,人們才會對它眾說紛紜,種種理論觀念如“單一的現代性”、“歐洲
現代性”(Euro-modemity)、“殖民現代性”(colonialmodernity)、“晚期現代性”(late modemity)、“第二次現代性”(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等等,讓人目不暇接。而“多元現代性”(mulfiple modernities)、“另類現代性”(ahemative modemity)等等,都指向那個把全人類都統一到了一起的“大旋渦”,說明今日已經將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口卷入的現代化進程,只能是一個構建全球“多元現代性”的“不統一的統一”過程。簡單地說,我們應該批判地看待“現代性”,認清現代化充滿矛盾的本質性特征,如同批判地看待當今的全球化浪潮一樣,既要看到其積極的正面的價值,又要認真對待、逐個解決它帶來的嚴重問題。
二
既然現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歐早期工業化,那么,非“西化”的現代化又有哪些能夠反映其本質特征的內容呢?要想說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厘清現代化與生產力發展的關系。
有人認為現代化就是發展生產力,說得比較完整一點也不過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眾福祉,也被理解為強國富民。下面的說法很有代表性:“現代化是指什么?是指生產力。……生產力不包含生產關系的含意,不包含社會形態的含意。”所以,“就像不能說資本主義現代化一樣,也不能說社會主義現代化。……說現代化物質文明,還馬馬虎虎,說現代化精神文明,就不太合適。……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文明,有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這些文明的內容和本質是不一樣的。籠統說現代化精神文明,不知道你是說哪一種精神文明。”現代化的這種認識,與將現代化等同于工業化一樣,是非常片面而且十分有害的。
現代化意味著從傳統的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大變革。在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中,現代大工業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技術革命和科學革命又起了領頭作用。從而,科學技術被稱為“第一生產力”。既有的三次世界現代化大浪潮,都是由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所帶動的生產力大飛躍所造成的。其中,科學技術進步又是工業革命的動力。
現代科學技術不僅具有“生產力”方面的功能,而且具有“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包括促進現代人文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代表了現代化進程中的兩種思維模式,前者從自然的角度出發,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后者則以人為中心,透過人的視角,從人的經驗出發了解自身、認識自然。但這并不是說科學與人文互為歧路。科學注重求真,其成果當屬“物質文明”;人文則重在求善、求美,當屬“精神文明”。兩個現代文明合在一起,才能說明現代化的本意。科學的第一個樣本是哲學,哲學是“愛智”之學,自由之學。所以說,科學一開始就是關乎自由的學問。現代人文主義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的影響。培根所確立的實驗觀察和歸納推理法、牛頓提出的運動三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不但奠定了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基礎和理論框架,而且引發了觀念形態的革命;宗教神秘主義的面紗被理性之手撩開,人類從對自然的恐懼的陰影下走出來,重新審視自身的價值和能力,奠定了批判理性的人文主義基調。西歐許多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如狄德羅、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其思想的人文主義光輝、對傳統的批判鋒芒,都直接來源于科技發展所帶來的信心和樂觀態度。
總之,對工業化、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大發展之于現代化的意義和重要性,無論怎么估計都不會過高。從19世紀后期迄于今日,中國人所看到的與西方國家的差距,首先是科學技術與生產力,實現“四個現代化”首先要著手的也是提高科學技術與生產力。在今天發達國家主導跨國資本流動和全球自由貿易的背景下,中國要實現可持續性經濟發展,只能訴諸不斷的科技創新和提高生產力,以科技和工業的現代化帶動社會和人的現代化,否則就會空有“高速增長”、“貿易順差”之名,而實際上是跨國公司的廉價加工基地。
但是,不能把現代化的本質屬性簡單地規定為發展生產力。正如火車離開火車頭無法前行,先進生產力猶如現代化的火車頭,但是它不能囊括現代化的道路、目標和現代化的列車所運載的內容。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雖然有著自身的內在邏輯,但離不開其承載者——人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制度體系。沒有一個良好的國內制度和國際社會秩序,生產力有可能停滯甚至倒退。這在前現代是如此,例如西歐古代的輝煌被中世紀的“黑暗”所取代,中國歷史上一次次改朝換代造成生產力的大破壞;現代依然如此,軍國主義的興起和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即使為了發展生產力,也必須變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使之互相適應,而這些都是現代化的內容。
對生產力發展在現代化中地位的認識,涉及對現代化意義的認識。就拿“第一生產力”——科學來說,歷史與現實中,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會遇到這樣一類尷尬:醫學科學可以延長垂死病人的生命,卻不能顧及病人的痛苦和愿望,不考慮該生命繼續存在的意義;藝術科學探討藝術品產生的條件,卻不追問它是否與人類的博愛精神對立。甚至還有更難堪的局面,例如物理學和化學的發展導致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出現;基因技術導致各種危害性轉基因食品,甚至出現克隆人怪物的危險;經濟發展理論在促進財富增長的同時,也導致巨大的貧富懸殊;人類運用先進科學技術征服自然,在帶來生產力巨大發展的同時,也造成對自身生存環境的嚴重破壞。英國宇宙學家馬丁?里在他即將出版的新書《最后的世紀》中預言,地球在未來200年內將面臨十大迫在眉睫的災難。這些災難多數都與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化有關。所以,很難證明科學所描述、改造或創造的世界是否值得存在。
科學具有“唯一的”、理性的尊嚴,但人的價值選擇卻可能是多元的、相對性的。從科學中找不到人“應當如何生活”的答案,科學不提供人生指南。當然,不是說科學家都是沒有人文關懷的科學主義者。相反,許多科學家都充滿了人文精神。這可以愛因斯坦為代表。這位20世紀世界最偉大的科學家,卻嚴厲批評“在戰爭時期應用科學給了人們相互毒害和相互殘殺的手段。在和平時期,科學使我們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沒有使我們從必須完成的單調的勞動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為機器的奴隸”。他告誡人們:“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他甚至明確提出,“關于目標和價值的獨立的基本定義,仍然是在科學所能及的范圍之外。”因此,如果將現代化定義為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就只是手段,它們必須很好地受到控制,才能“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
現代科學技術革命是在現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內強大的利潤驅動和巨大的競爭壓力下產生的。現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趨勢決定著科學技術的基
本進程。擴張性、掠奪性是現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基本特性,這一方面為現代科技的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源,但另一方面,也將其功用引向一個又一個死胡同。除了不斷制造新式武器用于毀滅性戰爭,環境、能源問題從資本主義早期就開始積累,到20世紀50年代,弊端逐漸顯示出來,成為人類所面臨的一大公害。從煤煙污染、工業“三廢”污染以及石油、化工、毒氣污染,到農藥污染、核污染和噪聲污染,都使人類的生存環境遭到極大破壞,人的生命健康受到嚴重威脅。正是在此背景下,新一代科學哲學家提出了“進化認識論”、“科學歷史主義”和“讓科學回歸人文”,關心科學產生的社會文化條件,強調科學研究是人的活動,指出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是知識體系分科化、專業化的結果,而知識的分科化、專業化又來自訴求效率與力量的技術理性。所謂“弘揚科學精神”,不應當是特別地張揚科學的優越性,而應當在科學與人文合一的層面上重新審視自由與理性。
因此,將科學與人文結合起來,將由科學技術引導的生產力發展與對人及其生存環境的關懷結合起來,將現代經濟發展與現代文化思想建設、制度建設結合起來,才能說明現代化的本質。中國政府反復申明的“三步走”戰略,以經濟建設即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以不斷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設為動力,以社會和諧、共同富裕為目標,囊括了現代化的核心內容,也體現了現代化的本質。
如上所述,現代化大變革絕不僅僅是發展生產力,它還必須包括人的自由、解放和社會的發展,這就要求在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對政治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進行全面的變革,由此而構成現代化的各個有機組成部分或“分進程”。這些分進程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因不同的性質、不同的順序排列而形成了現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所謂“西化”,也可以稱之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粗略地說,就是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或者以資本主義為目標的現代化。非西方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當年掠奪性、擴張性現代化的老路,而需要另辟蹊徑。這就要求在社會變革、思想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經濟和政治制度創新、科學技術創新等方面做新的探索。所謂“現代精神文明”是針對傳統文明而言的。但現代精神文明不等于資本主義精神文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應當是一種比資本主義精神文明更高級的現代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正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具體的而非抽象的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的帶有本質性的特征。
在中國,這種有自己特色的精神文明的結晶,就是人們正在探討的、建立在華夏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法治、民主與人權。法治是針對人治而言,民主是針對專制而言,人權是針對特權而言。這些看起來都是具有普遍性價值的觀念或制度,全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早發展”、“遲發展”各種現代化模式,概莫能外。然而仔細分辨,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別。就拿“人權”來說,人權是社會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一個現代化的社會當然不可能沒有人權,爭取實現法治化、民主化等現代化目標,不可能不實踐人權。現代西方各國的人權觀念源于早期啟蒙思想家關于人皆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權利假設,其人權實踐則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起碼需求。這種人權是狹隘的,其實踐具有欺騙性,所以馬克思批評它是“資產階級所有權”、“本身就是特權”,㈣“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人權”。中國人的人權觀念最早也是從西方舶來的自然權利概念。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猛烈抨擊君權、神權、族權、夫權等傳統特權,積極倡導個人自由、個性解放,倡導“天賦人權”,為人權在中國扎根也為現代化在中國的擴展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不等于說中國的人權理念和實踐就是照搬西方的。事實上,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許多跟現代人權接榫的因素,如人權所包含的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里都能找到而且相當豐富。缺少的主要是民主法治。現在,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其他有關的國際公約,不僅關注重在保障個人自由的第一代人權,更關注著重于為個人自由與基本生存權利提供社會經濟條件的第二代人權和包括發展權、環境權在內的第三代人權。中國學者也正在積極探討符合最廣大民眾利益的人權理論和民主與法制體系。有了這些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建構做保障,加上可持續經濟發展所造成的高度物質文明,假以時日,未來的中國將是一個國內社會和諧、人民安居樂業,國際上與所有平等待我之民族和諧共處的高度民主自由平等與法治化的繁榮富強的理想國度。所有這些目標實現之日,也就是中國現代化達成之時。“沿著這條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前進,中國必將會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
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為中國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然而,來自國外和內部的各種困難、挑戰也將繼續與機遇相伴隨。社會主義現代化將給中華民族帶來美好前景,中國實現現代化也將預示全世界的美好前景。但前進的道路不會平坦,曲折和反復在所難免,我們必須盡力少走彎路。
三
世界現代化或日當今世界的發展趨勢和未來前景,是“世界體系”的擴展或日“全球化”。這個“世界體系”由全球性的資本流動、生產與交換,具體體現于各種各樣的跨國金融往來、跨國貿易和跨國生產,以及維護這些活動的國際機構、國際組織所構成。套用沃勒斯坦的概念,這是一個“世界政治經濟體”,也是一個充滿矛盾斗爭的統一體。迄今為止,這個世界政治經濟體各個部分的規章制度,基本上是發達的“中心”國家制定的。幾百年來,處于體系“邊緣”的國家和地區針對“中心”國家的侵略壓迫進行了不懈的反抗,以爭得體系中平等的一席。他們的經驗證明,只有苦苦力爭,平等、和諧的世界秩序才有可能實現。居于體系“中心”的少數發達國家憑借其科學技術、工業和軍事實力,以不平等交換為手段,力求維護其在世界經濟、世界市場的霸主地位;與此同時,“中心”的“國家階級”(state class)也不惜放低身段,以各種“跨國”形式,居高臨下地與“邊緣”的資本擁有者聯合起來。相形之下,下層勞工的世界性流動與國際合作,以及“邊緣”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平等合作,則落在了后頭。
迄今為止的世界現代化進程,其基本載體不是各殖民帝國和霸權相繼支配下的“世界”,而是一個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早期資本主義現代化是如此,正如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遲發展現代化依然如此。在“中心”與“外圍”地位仍然懸殊而全球化日益擴展的今天,遲發展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尤其需要捍衛自己的獨立、主權。因此,迄今為止世界體系中最重要的層級、最重要單位,仍然應當是“國家”,包括多民族國家和單一民族國家。地區一國家和世界體系的關系,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我們既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不能無視不同民族、國家和地區歷史的個性、特殊性,不能忽視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多線性和多條道路。民族國家是現代世界體系中最活躍的因素,民族國家體系仍然是現代世界體系中最重要的次體系。如果不忽略500年來國家(以及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強國的霸權爭奪與更替、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與東方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掩飾“中心”對“邊緣”的侵略、控制,不抹殺殖民地的反抗斗爭和勝利成果,就不能不重視“國家”。尤其是從“非西方”的角度看,一百多年來,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是非歐洲、非西方各民族人民擺脫西方壓迫剝削的利器,無論從“亞國家”還是從超國家的角度削弱之,都是非歷史的。即使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主權國家仍然是世界體系的基本結構、基本格局。消解了現代民族國家,也就消解了現代世界體系本身。全球化的大趨勢對國家主權的確形成有力的沖擊,但正如全球化本身,這種沖擊既有正向的,也有逆向的。既有聯合國、歐盟這樣的超國家、跨國家、區域或全球性的新型組織結構對國家部分主權的取代或削弱,也有一兩個超級大國、霸權國家通過自身“外部主權”的擴張對周邊和世界其他國家主權的威脅與削弱,還有達倫道夫所稱的“強大的反向發展趨勢”即追求比現有民族國家更小的空間,“它的主角不是加拿大,而是魁北克;不是英國而是蘇格蘭;不是意大利而是帕達尼”。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科索沃戰爭、非洲一些國家的沖突與分離運動等一再說明,這類反向運動常常造成巨大社會災難。關注世界現代化的現狀與前景的研究者,應當充分關注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演變;對針對它的正向、逆向運動,都應當給以足夠的分析評價。同理,對現代世界體系里“中心”國家的現實和未來發展趨勢,也應給予足夠的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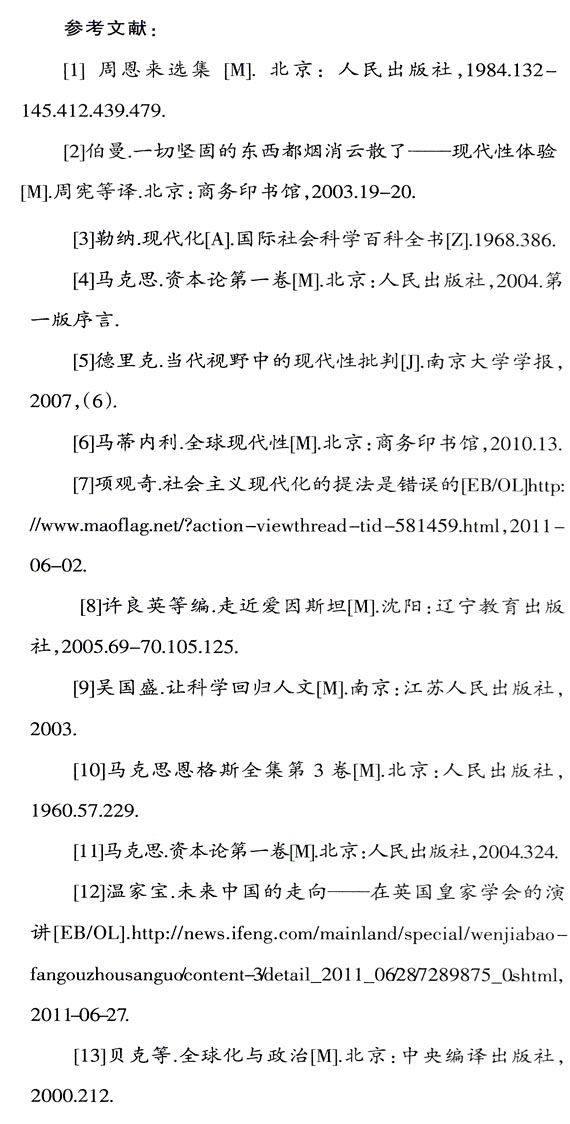
責任編輯:翟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