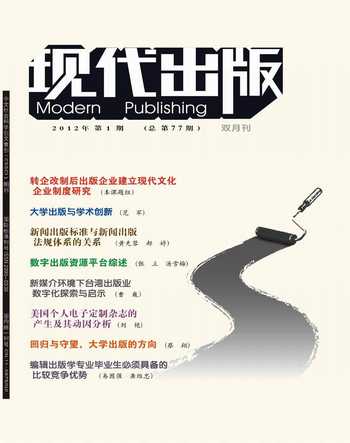大學出版與學術創新
摘要:出版,經濟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大學出版作為文化產業,其貢獻在產業之外。倘若我們今天的大學出版社背靠西南聯大這樣一所大師云集、英才輩出、思想活躍、成果迭出的大學,何愁沒有出版創新?我們講大學出版社為大學服務,恐怕主要也在于堅定地支持這種探索、思考和創新。認識大學的保守文化,小心呵護它,才會按規律辦事,才會對大學的變革發展持以正確合理的期待。
關鍵詞:大學出版;現代大學;學術創新;出版創新
對大學出版戰略以及“十二五”發展思路這類“宏大敘事”,我個人無甚新論和高見。這里,我想和大家探討一下“大學出版與學術創新”這個老話題。我始終認同的觀點是:出版,經濟是手段,文化是目的。大學出版作為文化產業,其貢獻在產業之外。我們是賺錢為主,順便做點文化;還是主要經營文化,順便賺點錢。順序顛倒,結果是很不一樣的。我談的問題,在經濟與文化中,側重文化;在傳統與現代中,側重傳統;在務虛與務實中,側重務虛;在大學與出版中,又側重大學。
一、從“諾貝爾獎情結”說起
“諾貝爾獎情結”不僅廣泛存在于我國的教育界、科技界,也存在于新聞出版界,國人談及此每每痛心疾首!中國奧運會辦了,世博會辦了,揚眉吐氣。看來辦世界杯足球賽實在太難,就特別渴望舉全國之力、不惜代價早點拿個諾貝爾獎。每年10月初是諾貝爾獎頒發之期,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結照例要發作一次。至于舉辦者把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先后授給達賴、劉曉波、高行健等人,實屬“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國人共憤。但對于諾貝爾獎的自然科學包括經濟學方面的獎項,似乎海內海外并無多大爭議。人們普遍相信,中國的國力已經大大地提高了,美中不足的是,迄今尚無一位大陸籍學者獲得自然科學類的諾貝爾獎。不錯,是已經有多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獎,2009年又有一位,這證明諾貝爾獎委員會并不歧視華人科學家。這一事實恰恰讓人疑惑:何以無一人(不包括抗戰時期艱難困苦的西南聯大培養的楊振寧、李政道)是在中國大陸接受教育又在大陸從事研究呢?
柳斌杰署長在為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蔡翔社長的《大學出版發展戰略研究》所寫的序言中有這么一段話:“幾十年來,我國的大學出版社為大學及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們出版了大量學術成果,成就顯赫。學術品位成為‘校園內出版社區別于‘校園外出版社的最大亮點。然而,在確立發展戰略的時候,大學出版社應當以更加深邃的戰略眼光,去追求更加高遠的宏偉目標。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國(大陸)的大學出版社,還沒有任何一家出版過我國(大陸)的大學及科研機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學術著作(學術論文)!我認為,由于我國(大陸)的諾貝爾獲獎者暫時還沒有誕生出來,不僅成為我國大學出版社‘心中永遠的痛,而且也可能成為我國大學出版社層次還不夠高、影響還不太大的潛在原因。”①我個人以為:我們的大學出版社將來若能推出自己國家科學家的優秀論著并獲得諾貝爾獎,無疑是非常光榮的。但中國科學家是否能獲得諾貝爾獎,與大學出版社層次如何、影響大小,與出版社有沒有推出能獲該獎的論著關系并不直接。20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層次之高、海內外影響之大(當時屬于亞洲第一、世界前三),出版史家都是熟悉的。至于牛津、劍橋大學獲得諾貝爾獎之多,眾所周知,但與他們各自的出版社似乎關系也不是太大,盡管這兩家大學出版社都很“牛”。出版,特別是圖書出版,從本質上看它可能更適合人文社科的東西,或者說,在人文社科方面更能體現出版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從“諾貝爾獎情結”,我們很自然想到“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時,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同樣的問題錢老后來又反復問過幾次,真是智慧老人!其實,“錢學森之問”提出的問題不僅體現在自然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同樣存在,或許更為嚴重。這個“之問”的答案別說是科學巨匠、兩院院士、學部委員,就是稍具歷史文化常識的人也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只是大家或啟而不發,或故意讓答案“跑偏題”,或有意“顧左右而言他”罷了。
回到出版上,人們總是懷想張元濟、陸費逵、王云五……這些出版大家漸漸遠去且日益模糊的背影。長江出版傳媒集團王建輝董事長在參觀張元濟紀念館時題詞:“張元濟不可追!”后來又有知名出版人寫過同題文章公開發表。如今的經濟水平、物質財富、科技能力都已大大增強了,各種“硬件”比起張元濟的那個時代,真有天壤之別。但一代出版大家今天有幾人能望其項背。現在,我們出版界可以涌現房地產大亨、資本運作高手、多種經營能人,甚至是制造股市神話的“故事家”,但就是難以產生真正杰出的出版家。盛世可以修典,但盛世未必能出大家,包括大出版家。
二、現代出版與現代大學共生共榮
提到現代大學,不得不說北京大學;討論現代出版,也繞不開商務印書館。二者可以比肩,也有某種深刻的內在聯系。回顧它們的歷史淵源,也對我們面向“十二五”的大學及大學出版有某些啟示。
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曾經這樣說:“在我的內心深處,優秀的出版社永遠是無形的大學和無聲的老師(不包括現今音像出版物)。而像商務印書館這樣歷史悠久的出版社,對文化的貢獻決不下于任何一所著名大學。”②因此之故,有歷史學者將商務印書館和北京大學比作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雙子星座”。從人際關系的“細部”來考察,二者的共生共榮,相互扶持,可說是現代出版史、教育史上的不朽佳話。
出版家張元濟和教育家蔡元培的私交公誼以及共同成就的事業,一直讓人感嘆和追懷。他們是浙江同鄉,又是光緒己丑(1889)鄉試同年,壬辰會試同年,又同入翰林院為庶吉士。若算舊歷,二人還是同庚,加上志向相同,可以算“六同”。因為張元濟,蔡元培一直是商務印書館的朋友,關心商務的事業,對其早期的奠基性成就有著重要貢獻。他雖然不是商務的股東,卻于1934年被選為董事,后來一直連任,參與制定“一·二八”的復興規劃。他雖不是商務花名冊上的人,卻自愿以商務人“自詡”:他給商務印書館的人寫信,歷來用“本館”而非“貴館”稱商務印書館。有研究者說,蔡元培是張元濟的精神支柱,胡適是王云五的精神支柱,而胡愈之是鄒韜奮的精神支柱。我則不完全贊同這種說法,說兩兩之間同聲相應、同氣相息可能更恰當。
過去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我想,沒有商務印書館,中國的現代大學也可能還要多摸索若干年。中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是要從蔡元培主政時期的北京大學算起的,而蔡元培出掌北大,主要是按照德國大學模式改造舊北大成新北大,這與他兩度留學歐洲(主要是德、法)大有關系。商務則是幫助蔡元培完成留學夢想的最有力支持者。1907年,獲得半工半讀機會的蔡元培留學德國,經費還差不少,商務印書館與蔡元培約定,通過為商務編書,給予一定報酬,實際是每月100個大洋,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后,蔡元培決定再次出國,商務給他預支稿費每月約200大洋,同時還幫助他留在國內的妻小,使其得以安心求學,數年后順利歸國。1919年“五四”運動后,北洋政府被迫請蔡元培重主北大,不知他的行蹤,催請電報無處可發,只能發到商務印書館,請商務轉交,由此可見交誼之一斑。蔡元培一生廉潔,無恒產、無積蓄。他去世時還是中央研究院院長,治喪事宜卻是由商務印書館料理的,可見其與商務關系之深。我想,商務成就了蔡元培,而蔡元培的思想,特別是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對商務印書館,也無疑是有某種影響的。
三、大學的學術創新是大學出版創新的基礎
在出版社編輯活動中,是選題策劃更重要,還是審稿加工更值得重視,歷來是有爭議的。我以為,對于大眾出版來說,特別是一些普及之作、文化快餐乃至跟風產品,策劃的作用舉足輕重。但在專業的學術出版領域,編輯的工作主要是“價值判斷”和“規范化”,對策劃的作用不可隨意拔高和過分倚重。周振甫對錢鍾書《談藝錄》《管錐編》的編輯貢獻固然值得稱頌,但這些著作的學術價值主要還是來自作者的創造。學者研究什么、怎樣研究,乃至能拿出什么樣的成果,與策劃者是沒有太大關系的。優秀的學術成果來自優秀的學人,特別是學術大師,而學者最重要的東西是學術的精神,是敢于質疑、勇于批判與創新的精神。
因此之故,出版學專家們格外青睞學術精神、大學精神。不可否認,我們曾經有過真正的學術精神、大學精神。1929年,陳寅恪先生為現代學術大師王國維撰寫紀念碑銘文,其中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三光,是日、月、星。這樣的評價當然完全適合于陳寅恪先生自己,而這段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明何以今天的大陸學者不能拿到諾貝爾獎之類的大獎。
香港著名教育專家金耀基曾說:“學術的獨立自由應該是大學的‘最高的原則,只有在這個原則的堅持與維護下,大學才能致力于真理的探索,才能在辨難析理的過程中將錯誤、獨斷的假知識減少至最低程度,而有可能一磚一石的建立起‘知識的金廟來。”③前面提及的蔡元培先生之所以深受尊崇,讓人景仰,就在于他奠定了北京大學乃至中國大學數十年兼容并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確立了大學之為大學的基本準則和文化精神,并且付諸實踐。抗日戰爭中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戰時中國的最高學府。其環境之惡劣與成績之顯著,形成極為鮮明的反差;它的“破破爛爛卻精神抖擻”也與我們今天日漸富裕、奢華,也日漸世俗化的大學形成巨大反差,以至讓今人覺得“不可思議”。那些名家大師幾乎是在饑寒交迫中創造出傳世之作、培養出棟梁之才,原因何在?當年執教西南聯大的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所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話,或許能給我們答案。他說:西南聯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正因此故,一個已經消逝了半個多世紀的大學,還能如此吸引那么多知識者的目光。它的魅力遠不止于“艱苦創業”和“人才輩出”。北大教授陳平原說:“在我看來,談論聯大的意義,對今日中國正熱火朝天地開展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有啟示。大學的使命,除了傳播知識,更為永恒的命題在于探索、思考,以及挑戰各種成見。”④試想,倘若我們今天的大學出版社背靠西南聯大這樣一所大師云集、英才輩出、思想活躍、成果迭出的大學,何愁沒有出版創新?我們講大學出版社為大學服務,恐怕主要也在于堅定地支持這種探索、思考和創新。
四、大學出版與學術的創新需要自由的空氣和寬松的環境
大學出版的創新、大學學術的創新看似大學及其出版社的事,其實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一個國家要想其科學家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家取得創造性成就,就得創造一種制度環境,讓科學家們能獨立地、自由地思考、研究。在學術文化創新上,可以說是“制度決定成敗”。眾多的基金,大量的投入,無窮無盡的各種“工程”,最終都解決不了學術創新、科技創新的難題。
2010年5月4日溫家寶總理在回答北京大學一位學生關于如何理解“錢學森之問”時說,錢學森之問對我們是個很大的刺激,也是很大的鞭策。溫家寶強調大學改革要為學生創造獨立思考、勇于創新的環境;大學還應該逐步改變行政化,按照教育規律辦學;大學應該以教學為中心,使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我個人認為,“錢學森之問”的解決有三個層面:專家學者個體,大學與專業研究院所,國家——黨和政府。套用老話講,黨和政府的政策與制度設計才是“綱”,其他兩個層級都只是“目”。能否有獨立思考、自主創新的環境,能否真正按教育規律辦學,按科學規律研究,主要取決于“綱”,而不是“目”——“綱舉則目張”。
有學者針對前蘇聯說過一段話,似乎就是針對當下中國說的:蘇聯向科研機構撥了大量資金,但唯有當這些資金“流入獨立的科學觀點控制的渠道”,即由自治的科學共同體掌握、使用,才能對科學研究產生積極作用。否則,這些補助的分配伴以建立政府指導的企圖,它們施加的影響便只能是破壞性的。當代中國投入到大學、研究機構包括出版社的經費越來越多,堪稱龐大,但它們大多數是由行政權力主導分配的,因而其作用也是相當不確定,至少是十分有限的。倘若思想的自由、學術的包容還是宏觀一點的困惑,而現行的學術GDP崇拜、有百害無一利的量化考核、按數字搞學術及教育上的“梁山水泊排座次”,更是從學術評價機制上徹底斷了學術與文化創新的“后路”。我們很欣喜地看到,最近出臺了《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強調重質,重創新,重同行評價。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對這一“意見”,學者反響積極,而一些科研管理者反應則比較冷淡。實際上,不合理、不科學的量化考核體系造就了一個利益集團,甚至形成了一個利益鏈。一種新的機制的建立,是對既有利益集團、利益鏈的一種沖擊。
如何辦大學、如何辦大學出版,現在是不是可以允許有略帶自由的思考、略顯個性化的選擇、稍微多樣化的模式?我們可不可以做一個秉持文化保守主義的出版人?我覺得出版社與大學在文化品格上有相近、相通之處。章開沅先生2007年從牛津大學訪問歸來后,發表了《泰晤士河源頭的思考——從“牛津現象”談起》一文。他說:“牛津的特點是政治上偏于保守,文化上善于守舊。”“牛津就是這樣悠然自得地經歷了幾百年的滄桑巨變,舊貌并未完全換新顏,卻又不緊不慢地跟上時代的步伐。無論是人文還是科技,許多學科仍然處在世界前沿,人才與成果之盛有目共睹,遑論諾貝爾獎獲得者之綿延。”⑤在章先生看來,現代與傳統并非截然兩分,創新與守舊本應相生共存,否則創新便必然會流于淺薄的時髦,甚至流于單純的形式創新乃至話語創新。出版的創新與守舊也當作如是觀。
無獨有偶,美國的耶魯大學也是以保守的文化品格著稱。王英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介紹了耶魯保守文化品格的形成,剖析了該校保守的管理、保守的教育理念,以及由此而引申的“大學保守文化品格的合理性”。作者在文末坦陳心曲,發人深思:“當我們沉下白日躁動之心,秉燭夜讀耶魯大學的發展史時,我們就會被耶魯清新的文化品格,深厚的文化積淀所打動:它幾百年來不為躁動的社會變遷所動,始終如一地堅持自己的社會職責,如同人類社會漫漫路上的一盞明燈,星光閃爍,為世人所矚目。它在靜謐中發展,在穩定中前進,以其保守的文化品格營造出一所循序漸進的世界一流大學,創新型人才和重大科研新發現如清泉從中汩汩流出,永不干涸,永不渾濁。”⑥
事實上,大學與社會經濟組織的區別,就突出體現在“保守”這一獨立的品質上,大學的魅力來自于保守基礎上的豐厚積淀和創新。“大學不是一個溫度計”,跟著社會同涼熱;大學必須經常給社會提供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并不一定都是社會所想要的,而往往是社會所需要的,這才叫“引領”。大學要服務社會,但需要保持某種距離,要有“張力”。大學與生俱來地具有保守性,也可以說保守性是大學的遺傳特征。英國著名高等教育學家阿什比曾經深刻地說過,任何大學都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大學的重要使命就是儲存、傳遞和創造人類文明。大學的這一使命賦予了大學保守的文化品格。大學要創造新的人類文明就要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大學的保守性,才會使得大學在穩定中發展。認識大學的保守文化,小心呵護它,才會按規律辦事,才會對大學的變革發展持以正確合理的期待。
大家熟知的周國平先生曾這樣寫道:“人們常常嘆息,中國為何產生不了大哲學家、大詩人、大作曲家、大科學家等等。據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們的文化傳統的實用品格,對純粹的精神性事業的不重視、不支持。一切偉大的精神創造的前提是把精神價值本身看得至高無上,在我們的氛圍中,這樣的創造者不易產生,即便產生了也是孤單的,很容易夭折。”⑦中國人民大學前任校長紀寶成大聲呼吁:“別讓實用主義遮蔽大學精神。”⑧其實,無論是在教育界還是出版界,這種工具理性、實用主義現在是絕對占上風的。對真理的追求,對理想的保護,對文化的創造與傳承,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如果說在極左時代對出版的沖擊主要來自政治,現在則還來自市場化、商業化、功利化。在出版界,老商務也成為出版人崇奉的一個似乎不可企及的夢想。其實,假如我們允許甚至鼓勵在淡定中堅守、在穩健中創新,出版業或許有更美好的未來。
記得柳斌杰署長在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道:“要大力培育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科研工作是探索規律、發現真理的工作,第一需要的是科學精神。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首先要大力倡導科學精神。歷史反復證明,沒有敢于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就沒有真正的科研,也就沒有推陳出新的創造能力,沒有繼往開來的時代進步。我曾給研究所的同志多次講過,科研要堅持科學性、獨立性原則,不要看著眼色、順著上級說話,要說真實的話,有根據的話,別人不愛聽而有真知灼見的話。這就要求我們要大力弘揚追求真理的精神,倡導批判的精神,尊重科學結論,崇尚理性質疑,不迷信,不盲從,獨立思考,敢于負責。”⑨
竊以為,以上所言算是不看眼色的一點實話、真話,或者像“白頭宮女說玄宗”的一點閑話。無論如何,大學不能沒有理想、失卻精神,大學出版也不能沒有精神的追求和文化的夢想。
(本文為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范軍2011年11月17日在寧波“大學出版論壇”上的演講,本刊發表時略有刪節)
注釋:
① 柳斌杰.大學出版發展戰略研究·序[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章開沅.文化的商務——王云五專題研究·序[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③ 金耀基.大學之理念[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14.
④ 陳平原.大學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07.
⑤ 章開沅.章開沅演講訪談錄[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9:108、109.
⑥ 王英杰.論大學的保守性——美國耶魯大學的文化品格[J].比較 教育研究.2003(3).
⑦ 周國平.人文精神的哲學思考[N].文匯報. 2002-12-01.
⑧ 紀寶成.別讓實用主義遮蔽大學精神[N].人民日報.2010-10- 27.
⑨ 柳斌杰署長在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成立大會上的講話[N]. 中國新聞出版報.2010-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