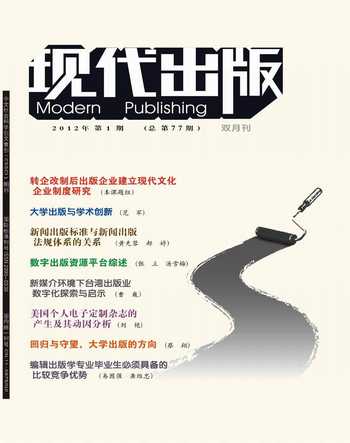回歸與守望,大學(xué)出版的方向
深秋的一個(gè)午后,我在自己的辦公室發(fā)呆。一縷斜陽(yáng)從窗外灑進(jìn),在滿墻的書柜上婆娑。我追隨著光影,用目光去觸摸那些書脊,去查閱那或明或暗的書名,追憶那或長(zhǎng)或短的故事。對(duì)于一個(gè)出版人來(lái)說(shuō),這應(yīng)是一份愜意,還帶著些許的自豪,因?yàn)樵谀且槐颈撅柡顺晒闹鞅澈螅那挠涗浿覀兊拿帧?/p>
可是這個(gè)午后與我的圖書兩兩相望,卻是一個(gè)失意的邂逅。這些寶貝圖書,從過(guò)往到今天,給我呈現(xiàn)的卻是一個(gè)文化價(jià)值日益單薄、印制冊(cè)數(shù)逐年下降的過(guò)程。滿目的樣書中,令人珍視、值得饋贈(zèng)的良品佳作已寥如晨星。可是這些年編輯的任務(wù)漲了又漲,出版補(bǔ)貼的門檻高了又高,要上繳的利潤(rùn)多了又多。于是我的耳邊驟然回蕩起編輯們的無(wú)奈、教授們的牢騷,還有領(lǐng)導(dǎo)們的不滿……
我們心中那寄托理想、視若生命的大學(xué)出版,究竟怎么了?
當(dāng)前中國(guó)的出版正處在一個(gè)歷史的變革時(shí)期,轉(zhuǎn)企改制給出版產(chǎn)業(yè)帶來(lái)了前所未有的生機(jī)和活力,但經(jīng)濟(jì)改革與制度創(chuàng)新并非萬(wàn)能,出版顯現(xiàn)的問(wèn)題終究要回到文化的母體中去尋求答案。
大學(xué)出版作為出版中的出版,面對(duì)的是文化中的文化。大學(xué)出版人應(yīng)當(dāng)以深刻的文化自覺(jué),去認(rèn)識(shí)大學(xué)出版的本質(zhì),擔(dān)當(dāng)大學(xué)出版的重任。大學(xué)出版人的這種文化自覺(jué)是對(duì)理性與思辨的回歸,對(duì)激情與創(chuàng)新的守望,是引領(lǐng)大眾在高尚與媚俗、進(jìn)步與倒退之間科學(xué)抉擇的一股內(nèi)在力量。
大學(xué)出版應(yīng)該是文化的
文化是民族之魂魄,國(guó)家之根基。文化一旦生成,它對(duì)個(gè)體的生存將具有決定性的制約作用,像血脈一樣構(gòu)成人存在的靈魂;同時(shí)它構(gòu)成了社會(huì)運(yùn)行的內(nèi)在機(jī)理,從深層制約著社會(huì)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其他領(lǐng)域的發(fā)展。文化看似柔弱,實(shí)則剛強(qiáng),因?yàn)樗偸且詿o(wú)形的精神意識(shí)和觀念,深刻影響著有形的存在與現(xiàn)實(shí),深刻作用于社會(huì)發(fā)展和百姓生活。
我們的出版自誕生以來(lái),歷經(jīng)千年演變、百年滄桑,其載體從甲骨的、簡(jiǎn)帛的、雕版的、印本的,到電子數(shù)字的,已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其受眾從王權(quán)專享到普世共有,已遭遇顛覆性的推動(dòng);其社會(huì)功能從政治的、教育的,到經(jīng)濟(jì)的,甚至娛樂(lè)的,也已得到全方位的開(kāi)發(fā)。無(wú)論載體、受眾、功能如何變遷,出版的本質(zhì)是文化,始終如初。沒(méi)有思想的圖書是一堆廢紙,沒(méi)有內(nèi)容的互聯(lián)網(wǎng)是一片死海。沒(méi)有文化的出版,言語(yǔ)蒼白、精神頹廢,它又如何教化育人,又怎樣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因此,是文化給出版以血肉、是文化給出版以骨骼、是文化給出版以魂魄。離開(kāi)文化,出版將煙消云散。
大學(xué)自其誕生以來(lái)就對(duì)社會(huì)文化產(chǎn)生巨大影響。大學(xué)是文化發(fā)展的區(qū)域中心。它包括眾多學(xué)科領(lǐng)域,集學(xué)術(shù)研究、科學(xué)發(fā)現(xiàn)、人才培養(yǎng)及精神建構(gòu)于一體,成為新文化的孵化器。它有科學(xué)、民主、創(chuàng)新的精神理念,有開(kāi)放、平等、自由的文化氛圍,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文化積淀。大學(xué)出版根植于大學(xué),更應(yīng)該回歸文化,守望文化,致力于構(gòu)筑大學(xué)的文化精神。所以柳署長(zhǎng)說(shuō),大學(xué)出版理應(yīng)努力營(yíng)造高雅的文化氛圍,堅(jiān)持引領(lǐng)社會(huì)文化的批評(píng)精神與超然態(tài)度,追求大學(xué)的社會(huì)責(zé)任之大,追求大學(xué)的學(xué)問(wèn)之新,以大氣魄、大氣派,引領(lǐng)社會(huì)的文化潮流。
大學(xué)出版應(yīng)該是服務(wù)大學(xué)與學(xué)術(shù)的
大學(xué)出版的特點(diǎn)在于,它是辦在大學(xué)里的出版社,即背后有大學(xué)母體作為依托。這一特點(diǎn)幾乎是天然地造就了大學(xué)出版服務(wù)大學(xué)、傳播學(xué)術(shù)的特殊使命。中國(guó)古代大學(xué)的雛形——國(guó)子監(jiān),既是封建時(shí)代最高的教育管理機(jī)構(gòu),也是重要文獻(xiàn)典籍的編纂刊印場(chǎng)所。真正以大學(xué)出版社命名的,是1929年成立的南開(kāi)大學(xué)出版社,后因日本侵略華北而停辦。之后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前,大學(xué)出版事業(yè)一直與中國(guó)無(wú)緣。新中國(guó)成立后,國(guó)家為適應(yīng)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發(fā)展的需要,適時(shí)成立了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和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到1959年,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因國(guó)家對(duì)出版事業(yè)的調(diào)整而暫停,之后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隨著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的解散也被迫停辦。以此為起點(diǎn),直至“文革”結(jié)束,我國(guó)大學(xué)出版事業(yè)一度陷入停滯。到1978年,隨著各行各業(yè)的撥亂反正,為適應(yīng)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以及科學(xué)發(fā)展的需要,大學(xué)出版在我國(guó)得以恢復(fù)和發(fā)展,大學(xué)出版體系一步步建立成形。
我國(guó)大學(xué)出版事業(yè)一波三折的發(fā)展歷程證明,政府對(duì)出版資源的行政配置決定了大學(xué)出版服務(wù)大學(xué)的生存目的;大學(xué)對(duì)大學(xué)出版的客觀需要決定了大學(xué)出版?zhèn)鞑W(xué)術(shù)的自身價(jià)值。大學(xué)出版的使命和高等教育的性質(zhì)及其基本職能由此緊密相連。高等教育旨在培養(yǎng)精英,研究學(xué)術(shù),以此發(fā)展科技文化,推動(dòng)社會(huì)進(jìn)步。大學(xué)出版作為大學(xué)的一個(gè)有機(jī)組成部分,以自己獨(dú)特的內(nèi)容和方式踐行服務(wù)大學(xué)、傳播大學(xué)學(xué)術(shù)的使命,與生俱來(lái),唯我獨(dú)尊。
大學(xué)教育與科研的發(fā)展催生并壯大了大學(xué)出版,大學(xué)管理體制的每一步變革也帶動(dòng)了大學(xué)出版的功能性轉(zhuǎn)型。大學(xué)因知識(shí)密集、科研豐厚,為大學(xué)出版提供了永續(xù)不絕的選題資源;因人才薈萃、大師輩出,為大學(xué)出版提供了成熟穩(wěn)定的作者隊(duì)伍;大學(xué)為社會(huì)所重視、受百姓之敬仰,更為大學(xué)出版提供了卓爾不群的品牌效應(yīng)。這些得天獨(dú)厚的出版資源優(yōu)勢(shì),是大學(xué)出版的安身立命之本,更是成長(zhǎng)壯大之本。因此,大學(xué)出版以大學(xué)為依托,受大學(xué)之恩澤,服務(wù)教育、服務(wù)學(xué)術(shù)理當(dāng)義不容辭。離開(kāi)大學(xué),大學(xué)出版將不復(fù)存在。
當(dāng)今數(shù)字時(shí)代,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的革新與傳播方式的演變既豐富了大學(xué)出版,也向其適應(yīng)能力提出了考驗(yàn)。但大學(xué)出版推動(dòng)學(xué)術(shù)發(fā)展這一使命仍會(huì)薪火相傳,彰顯更加獨(dú)特的專業(yè)價(jià)值。耕作于出版行業(yè)最精尖、最冷僻的領(lǐng)域,大學(xué)出版的長(zhǎng)處和深度均得自學(xué)術(shù)出版的專業(yè)性。大學(xué)出版在內(nèi)容過(guò)濾、開(kāi)創(chuàng)品牌方面始終維持質(zhì)量標(biāo)準(zhǔn),它通過(guò)市場(chǎng)推廣來(lái)提升學(xué)術(shù)科研成果的可見(jiàn)度,并資助供應(yīng)鏈、投資未來(lái)。這些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錘煉的真本事,是大學(xué)出版積累起來(lái)的無(wú)形資本,也是大學(xué)出版邁向發(fā)展升級(jí)之路的通行證。未來(lái)的行業(yè)格局多變,大學(xué)出版若能轉(zhuǎn)化自身優(yōu)勢(shì),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知識(shí)、文化與學(xué)術(shù)的自由傳播,不僅能夠轉(zhuǎn)型為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潛在市場(chǎng)的投資者與創(chuàng)新者,同時(shí)也能成長(zhǎng)為供應(yīng)鏈上最終可以依賴的債權(quán)人和風(fēng)險(xiǎn)承擔(dān)者。
大學(xué)出版即便為產(chǎn)業(yè),也應(yīng)該是現(xiàn)代的
我們今天的大學(xué)出版,已經(jīng)成為中國(guó)現(xiàn)代出版產(chǎn)業(yè)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轉(zhuǎn)企改制后的大學(xué)出版作為獨(dú)立的市場(chǎng)主體,應(yīng)當(dāng)彰顯現(xiàn)代企業(yè)的精神風(fēng)范。現(xiàn)代企業(yè)發(fā)展到今天,已由純粹的經(jīng)濟(jì)組織轉(zhuǎn)變?yōu)榧扔薪?jīng)濟(jì)責(zé)任,又有社會(huì)責(zé)任的二元組織。也就是說(shuō),對(duì)一己之利的追求已經(jīng)不是現(xiàn)代企業(yè)的唯一目標(biāo),大多數(shù)成功企業(yè)是在一種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對(duì)財(cái)富的渴望,同時(shí)兼顧其他利益主體的目標(biāo)激勵(lì)下,走向卓越的。
對(duì)現(xiàn)代企業(yè)而言,利潤(rùn)對(duì)公司猶如呼吸對(duì)生命一樣,呼吸對(duì)生存來(lái)說(shuō),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生活的目的;同樣,利潤(rùn)可以決定公司的生存,但它并不是公司存在的原因。盡管那些與更廣泛的社會(huì)道德目標(biāo)聯(lián)系起來(lái)的企業(yè)價(jià)值觀,有時(shí)可能會(huì)抑制企業(yè)對(duì)獲利能力的追求,但大多數(shù)研究結(jié)果和企業(yè)的發(fā)展實(shí)踐反復(fù)證明,這些價(jià)值觀實(shí)際上是可以長(zhǎng)期地促進(jìn)而不是阻礙利潤(rùn)和績(jī)效的。
現(xiàn)代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的擔(dān)當(dāng),直接影響企業(yè)的品牌和聲譽(yù),也逐漸成為社會(huì)對(duì)企業(yè)評(píng)估的重要指標(biāo)。可以預(yù)見(jiàn)在不久的未來(lái),企業(yè)的競(jìng)爭(zhēng),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的競(jìng)爭(zhēng)。作為現(xiàn)代企業(yè),大學(xué)出版社在追求經(jīng)濟(jì)利潤(rùn)的同時(shí),必須擔(dān)當(dāng)起兼顧其他利益主體的社會(huì)責(zé)任。作為現(xiàn)代文化企業(yè),大學(xué)出版社的社會(huì)責(zé)任必定是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助人的形式,來(lái)增進(jìn)民族的精神幸福,促進(jìn)社會(huì)的和諧發(fā)展。從這個(gè)意義上講,大學(xué)出版的企業(yè)身份,不僅沒(méi)有遠(yuǎn)離文化傳承與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的本質(zhì),反而是以更加清晰、更加具體的方式去追求經(jīng)濟(jì)利潤(rùn),從而實(shí)現(xiàn)自身的價(jià)值訴求。
更進(jìn)一步說(shuō),出版可以產(chǎn)業(yè)運(yùn)營(yíng),但絕對(duì)不能產(chǎn)業(yè)化。現(xiàn)代出版產(chǎn)業(yè)的本質(zhì)目標(biāo),依然是文化。或者用老一輩出版家劉杲的話來(lái)說(shuō),文化是目的,經(jīng)濟(jì)是手段。離開(kāi)文化的出版經(jīng)濟(jì)不過(guò)是空中樓閣,隨時(shí)都有可能坍塌。
大學(xué)出版,無(wú)論是從出版本質(zhì),還是從天賦使命的角度來(lái)追溯,無(wú)論是從傳統(tǒng)出版事業(yè),還是現(xiàn)代出版產(chǎn)業(yè)的眼光來(lái)看待,都具有鮮明的文化色彩、濃厚的學(xué)術(shù)氣息。作為現(xiàn)代大學(xué)出版人,一旦我們明了,是大學(xué)給了大學(xué)出版以生命,是利潤(rùn)給了大學(xué)出版以呼吸,而文化和學(xué)術(shù)則賦予大學(xué)出版以生命的意義,則大學(xué)出版,分花拂柳,撥云去霧。路,就在不遠(yuǎn)的前方。回歸大學(xué)文化,堅(jiān)守學(xué)術(shù)出版的使命,守望文化與學(xué)術(shù)的品位,拒絕庸俗。這,正是我們大學(xué)出版人奮進(jìn)的方向!
回歸大學(xué)出版的文化本質(zhì)和學(xué)術(shù)使命,離不開(kāi)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大學(xué)出版作為學(xué)術(shù)出版的排頭兵,對(duì)高尖學(xué)科、冷僻學(xué)科、瀕危學(xué)科學(xué)術(shù)成果的出版功在當(dāng)代、利在千秋,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需要合理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建構(gòu)起一套科學(xué)的評(píng)價(jià)體系或考核機(jī)制。即使在注重資本主義理性的英美國(guó)家,大學(xué)出版也是依靠政府扶持和社會(huì)資助,以非營(yíng)利的出版方式存在、發(fā)展并壯大的。用大學(xué)出版的盈利所得來(lái)彌補(bǔ)教育投入的不足,只是權(quán)宜之計(jì);大學(xué)出版過(guò)度的商業(yè)化,終將摧毀大學(xué)的靈魂和精神,傷害民族和國(guó)家的利益。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huì)將文化命題定為全會(huì)議題,之后的《決定》指出,要完善文化產(chǎn)品的評(píng)價(jià)體系和激勵(lì)機(jī)制。在這一利好形勢(shì)下,相信我們的大學(xué)出版也將迎來(lái)機(jī)遇。
堅(jiān)守大學(xué)出版的文化本質(zhì)和學(xué)術(shù)使命,更需要我們大學(xué)出版人的勇氣和激情。
任何一項(xiàng)偉大事業(yè)的背后,總是涌動(dòng)著一股不朽的精神力量。大學(xué)出版作為文化與學(xué)術(shù)的守望者,在低俗文化泛濫、拜金主義橫行的今天,對(duì)科學(xué)理性、審美價(jià)值和社會(huì)批評(píng)的堅(jiān)守,那是一種可貴的文化擔(dān)當(dāng)。這種擔(dān)當(dāng)飽含人文主義情懷,飽含自由與獨(dú)立、引領(lǐng)與創(chuàng)新的精神,堪稱一種文化英雄主義,即所謂以文化兼濟(jì)天下,以文化普渡眾生,舍我其誰(shuí)?!
正如我們知道廣西師大更知道廣西師大出版社,相信有那么一天,我們所有的大學(xué)出版社,不僅是大學(xué)的附屬和延伸,更是大學(xué)的一段佳話,一個(gè)品牌,一份榮勛!
(本文為中國(guó)傳媒大學(xué)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蔡翔2011年11月17日在寧波“大學(xué)出版論壇”上的演講,本刊發(fā)表時(shí)略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