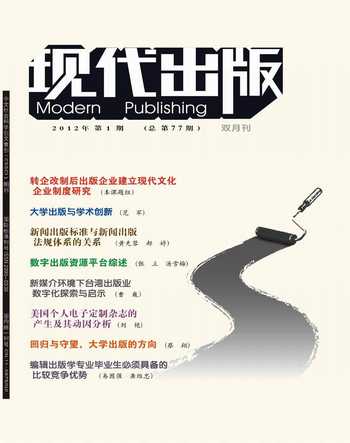勿讓編輯繼續(xù)教育課程成“雞肋”
董拯民
在各行各業(yè)都要求從業(yè)人員持證上崗的大背景下,職業(yè)資格考試已成為我國除高考、考研之外又一大考試陣地。不過,當(dāng)考試者千辛萬苦獲得資格證書后,卻并非萬事大吉,考證只是繼續(xù)教育的開始,于是職場中誕生了“養(yǎng)證”一詞。“養(yǎng)”就意味著要為證書不懈地付出時間、金錢和精力,此中還有一種必須接受的無奈。
出版行業(yè)自然也不能例外。2008年2月21日,新聞出版總署頒布了《出版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職業(yè)資格管理規(guī)定》(以下簡稱《規(guī)定》),其中第七條指出:“出版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應(yīng)按照規(guī)定參加繼續(xù)教育”,“繼續(xù)教育的具體內(nèi)容,由新聞出版總署另行規(guī)定。” 2010年頒布的《出版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繼續(xù)教育暫行規(guī)定》第七條指出:“出版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每年參加繼續(xù)教育的時間累計不少于72小時。其中,接受新聞出版總署當(dāng)年規(guī)定內(nèi)容的面授形式繼續(xù)教育不少于24小時。其余48小時可自愿選擇參加省級以上新聞出版行政部門認(rèn)可的繼續(xù)教育形式……”在執(zhí)行該規(guī)定的過程中,每位編輯可謂是“冷暖自知”。不可否認(rèn),該規(guī)定的出發(fā)點是好的,目的是持續(xù)提高編輯的業(yè)務(wù)能力。我國出版業(yè)肩負(fù)著傳承優(yōu)秀文化、傳播先進(jìn)科學(xué)技術(shù)以及堅持正確輿論導(dǎo)向的重大歷史使命,這就對出版從業(yè)人員特別是要對出版內(nèi)容負(fù)責(zé)的編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科學(xué)落實該政策并非易事,這正是筆者認(rèn)為當(dāng)前繼續(xù)教育課程的效果值得商榷的原因。
其一,《規(guī)定》中關(guān)于證書登記、續(xù)展登記以及資格取消等作了明確要求,體現(xiàn)的是對持證編輯的“管”字,但對于尚未取得資格證書的編輯的繼續(xù)教育卻缺乏監(jiān)管力度。
其二,《出版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繼續(xù)教育暫行規(guī)定》雖然明確規(guī)定“出版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享有參加繼續(xù)教育的權(quán)利和接受繼續(xù)教育的義務(wù)”,但在實際工作中,出版單位除了自己為新編輯組織一些必要的培訓(xùn)外,幾乎很少會用職工教育經(jīng)費讓新編輯參加各項繼續(xù)教育課程的培訓(xùn)班。
其三,如何設(shè)置編輯繼續(xù)教育的課程是一個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難題。盡管《出版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繼續(xù)教育暫行規(guī)定》要求繼續(xù)教育課程的設(shè)置要本著“以人為本,按需施教”的原則,但是學(xué)員還是很難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選擇課程。我們知道,參加學(xué)習(xí)的編輯,既有圖書編輯,還有期刊編輯,圖書編輯和期刊編輯又分社科類編輯、科技類編輯,等等。面對這些有著截然不同需求的編輯,當(dāng)前的繼續(xù)教育課程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如果講課老師無法將所講課程與編輯實際工作結(jié)合起來,繼續(xù)教育也就失去了意義。
其四,“收費高,授課時間不靈活”也讓編輯們頗感無奈。在很多行業(yè)都走上產(chǎn)業(yè)化道路的今天,編輯繼續(xù)教育似乎也未能幸免,培訓(xùn)費用一年年“水漲船高”。由于政策制定機構(gòu)同時也是培訓(xùn)主辦機構(gòu),在成本不透明的情況下收取過高費用難免有壟斷的嫌疑。另外,由于工作原因,很多編輯無法做到脫產(chǎn)學(xué)習(xí),于是就出現(xiàn)了學(xué)員簽完到便離開的情況,同樣背離了參加繼續(xù)教育的初衷。
我們知道,學(xué)習(xí)的最大動力在于興趣,興趣源于對知識的渴求。目前,參加繼續(xù)教育對編輯們來說是一個“痛并快樂著”的過程,既有學(xué)習(xí)到新知識的快樂,同時也承受著課程選擇余地小和時間耗費大之痛。如果我們回到舉辦繼續(xù)教育的出發(fā)點來考慮,或許會讓當(dāng)前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迎刃而解。
首先,行政主管部門要放下“管理”的架子,將繼續(xù)教育的重點放在對新編輯的培養(yǎng)上。另外,可將政策的執(zhí)行手段更加人性化,如可以要求編輯在取得“出版專業(yè)資格證書”后的一定時限內(nèi),每年必須接受72個學(xué)時的繼續(xù)教育課程,但滿足課程考核要求后則不再強制要求其參加繼續(xù)教育。
其次,把舉辦繼續(xù)教育的權(quán)力下放到出版單位。打破目前繼續(xù)教育培訓(xùn)班只能由新聞出版總署或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屬機構(gòu)舉辦的格局。出版管理部門可予以認(rèn)可或支持單個出版單位或者幾個同類的出版單位聯(lián)合起來,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對編輯進(jìn)行繼續(xù)教育。如此一來,繼續(xù)教育的內(nèi)容能夠與編輯的實際工作緊密聯(lián)系起來,所取得的實際效果或許會更好。
最后,如果繼續(xù)教育的舉辦權(quán)暫時不能下放,那么培訓(xùn)機構(gòu)需加強師資力量配置,讓參加培訓(xùn)的編輯能有足夠的選擇空間。如果現(xiàn)有課程能夠滿足各出版單位的需要,相信出版單位也十分愿意將新編輯的業(yè)務(wù)培訓(xùn)一并交由培訓(xùn)機構(gòu)去做。
在信息時代,知識的更新速度很快,編輯業(yè)務(wù)能力的提高更在于平時在工作中的學(xué)習(xí)與積累,每年72個學(xué)時的繼續(xù)教育課程遠(yuǎn)遠(yuǎn)不能滿足需要。接受繼續(xù)教育是編輯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卻不能把這一過程“行政化”后又“產(chǎn)業(yè)化”,讓原本有著積極意義的編輯繼續(xù)教育變成了“嚼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作者系中國致公出版社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