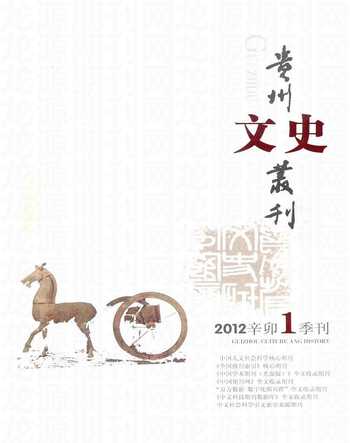從幕府到書院看乾嘉漢學大吏阮元的尷尬與無奈
刁美林 邵巖


內容提要:阮元是乾嘉漢學的領袖人物。他組織起清代最大的學術幕府,創辦詁經精舍和學海堂,開展聲勢浩大的學術活動,成績卓著。然而在與幕賓相處、主持學術研究、領導學術流向、創辦書院進行教育改革及實踐的過程當中,阮元也有著鮮為人知的尷尬與無奈。這是整個清代學術及士人的真實寫照。
關鍵詞:阮元幕府詁經精舍學海堂漢學宋學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8705(2012)01-65-70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蕓臺,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曾任山東、浙江學政、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嘉慶四年會試的主考官,浙江、江西、河南三省巡撫,漕運、湖廣、兩廣、云貴總督,晚年拜體仁閣大學士,晉太傅銜,是清乾、嘉、道“三朝閣老”、“九省疆臣”。他不僅在仕途上為自己贏得了顯赫的地位,而且在和揚州學派的汪中、焦循及皖派戴震的嫡傳弟子王念孫、任大椿等人的交往中,逐漸成為一位經學大師。他延攬名儒,建立起清代最大的學術幕府,研討學術,編纂典籍,成就斐然。他還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名望,通過創辦研習漢學的專門機構——詁經精舍和學海堂,以期通過“專勉實學”達到“以勵品學”和尊經崇漢的宗旨,成為中國書院史上的轉折點和里程碑。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術領袖和仕途一帆風順的封疆大吏,也有其鮮為人注意的學術尷尬與無奈的一面。這些尷尬與無奈,不止阮元本人所獨有。作為乾嘉漢學的殿軍,阮元的學術困境正是那個時期絕大多數學人狀態的流露和表白,也是乾嘉學術逶迤前進的真實寫照。
一、禮賢下士然難免有隙
阮元是有清一代贊助獎掖學者而享譽后世的學者型官員中影響最大的一位。這既表現在阮元幕府規模空前,又表現在阮元及其幕賓的學術活動帶有極宏大的氣象,是清代其他以贊助學術而聞名的學者型官員所無法比擬的。阮元學術幕府中學人幕賓達到120多位。這些學人幕賓有從事編書、校書一類工作的漢學家;有詩人類的幕賓,他們主要與阮元及其他幕賓進行詩歌唱和,調劑幕府生活;有協助阮元處理政事的幕賓,使幕府的學術活動能夠正常進行。這三類幕賓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然而,阮元雖然身為幕主,在整個幕府的學術活動當中處于中心位置,卻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最能反映阮元身處尷尬境地的例子當屬《十三經注疏》的校勘了。顧廣圻于嘉慶六年應阮元之邀至杭州“十三經局”,不久便與主定《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段玉裁發生爭執,釀成軒然大波。段玉裁認為注疏合刻于北宋之季,顧廣圻則認為始于南宋。兩人辯駁,“自此二氏交惡,終身不解。”作為發起人的阮元很為難,“從顧則茂堂實為前輩,袒段則義有未安。是以遲至二十年段氏歿后,始行肇工。”嘉慶二十二年南昌學堂重刊《宋本十三經》始成。晚了整整十四年。本屬學術范圍的爭論,結果導致二人關系破裂。這一結果反過來影響到《十三經注疏》的重刊。需要強調的是,阮元早已于嘉慶十九年來到江西巡撫任上,若非當時江西鹽運道胡稷、貢生盧宣旬及前給事中黃中杰等人支持以及南昌知府張敦仁和九江、廣信二府知府,南昌、新建、都陽、浮梁、廣豐、會昌等縣知縣及一些紳士出資相助,重刊《宋本十三經》今天能否見到都是問題。
不僅是幕賓之間的分歧,主賓之間的矛盾也讓阮元感到很為難。段玉裁是雍正十三年乙卯生人,年長阮元二十九歲,阮元對其非常尊重。《十三經注疏》實行分任纂輯,是一項多人合作而成的學術成果。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之《阮刻十三經校勘記》中記載:“《易》、《榖梁》、《孟子》屬元和李銳,《書》、《儀禮》屬德清徐養原,《詩》屬元和顧廣圻,《周禮》、《公羊》、《爾雅》屬武進臧庸,《禮記》屬臨海洪震煊,《春秋左傳》、《孝經》屬錢唐嚴杰,《論語》屬仁和孫同元。”李銳,精通歷算學,阮元說他“深于天文算數,江以南第一人也”,與焦循、凌廷堪號稱“談天三友”。徐養原,自幼從師于名流學者,探究學術源流,對經學、小學、歷算、輿地、氏族、音律均有研究。顧廣圻,《清史稿》說他“天資過人,經、史、訓詁、天算、輿地靡不貫通,至于目錄之學,尤為專門”,他是乾嘉年間惟一能與盧文弨相提并論的校讎名家,他的好友戈襄云其“性剛果,故出語恒忤觸人”。臧庸“沉默樸厚,學術精審”。洪震煊被阮元稱之日:“齊侍郎后,不圖復見洪生也!”這么多學富五車之士,阮元唯獨任命段玉裁“主其事”,也就是相當于現在說的“執行主編”,足見阮元對他的倚重和信任。
可段玉裁對阮元還是有意見。嘉慶九年,段氏致函王念孫云:“弟七十余耳,乃昏如八九十者,不能讀書。惟恨前此之年,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時拙著不能成矣。所謂一個錯也。”書信中所謂“為人作嫁衣”之事,當指他在編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過程中,承擔了實際負責人的工作,為主纂阮元“作嫁衣”,而“拙著”是指《說文解字注》。他曾提到:“弟衰邁之至。《說文》(即《說文解字注》)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書請王伯申踵完。伯申杳無回書。今年一年,《說文》僅成三頁。故雖阮公盛意而辭不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證》,自顧精力萬萬不能。近日亦薦顧千里、徐心田養原兩君而辭之。”由此可見,段氏之所以對阮元流露出不滿之意,應當是因為主持《十三經校勘記》而耽誤了《說文解字注》的撰寫。這確實也是事實。
問題不僅止于此。段氏自身的品行和秉性也是兩人產生矛盾的重要原因。段氏在音韻、訓詁、經學、小學等多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自視甚高。他曾言:“玉裁昔年深究古文辭之旨,為端臨知我耳。”還在《與劉端臨第十七書》中狂言:“弟于學問深有所見……吾輩數人死后,將來雖有刻《十三經》者,恐不能精矣。”自負之情,溢于言表。他認為,阮元的水平不如自己,重刊《十三經》的“總纂”一職理應由自己來擔當,僅為一“主其事”,實在是委屈自己。
段氏還非常頑固。最著名的例子是《直隸河渠書》的作者署名問題,這是歷史上的一段學術公案。段的恩師戴震曾客于直隸總督方觀承幕,繼趙一清、余蕭客之后參與撰寫《直隸河渠書》。稿未成而方歿。后為“無賴子”,即吳江捐納通判王履泰所得,刪改之后易名,也就是今天我們能看到的《畿輔安瀾志》。關于此書的真實作者,后來發生了爭論。由于趙一清先于戴震人幕,且在幕時間比戴長,成稿是戴的一倍還多,所以有戴竊趙之議。段玉裁為文辯之,在《經韻樓集》中定此書系“趙為草創而戴為刪定”。其意在夸大其師編撰之功,難以服人。為尊者諱且不惜為之曲的學術詬病暴露無遺。
由是觀之,段玉裁是一個恃才傲物且秉性頑固之人。阮元雖對段玉裁這位長輩是很尊敬和信任,對他的學問也給予高度的評價,但他們之間還是免不了有罅隙存在。這讓阮元很為難。因為,在清代幕府中,賓主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所謂“合則留,不合則去”,是主賓之間相處的原則。如果幕賓一旦因不合而拂袖離去,對幕主來說是相當難堪的事,往往會影響其在士林中的地位和形象。上面所提戴震曾客方觀承幕,方歿后,楊廷璋繼任直隸總督,戴由于楊不禮賢下士,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楊在士林中的威望受到不小影響。因此,對于段氏對自己的怨憤,阮元只能隱忍之。上述《宋本十三經注疏》“遲至(嘉慶)二十年段氏歿后,始
行肇工”便是有力證明。
需要說明的是,阮元和段玉裁之間也并不是積怨甚深。兩人交往的過程中,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的。段與阮的關系總體上還是不錯的,否則,段也沒有必要非得留在阮幕那么多年。我們應該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編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時實際擔任主編的重要功績,但也不能因而否認阮元在其中“總纂”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組織之功。
二、從揚漢抑宋到調和漢宋
所謂“漢學”、“宋學”,是清代學者習用的兩種迥然不同的概念和學術取向。前者在理論上崇尚東漢的古文經學,治學方式提倡“實事求是”取證,特重漢儒經注。作為學術流派,它萌于明清之際,盛于乾、嘉,衰于道、成。后者奉程朱為宗,尤其是朱熹個人的學說,其最大特點是以主觀意愿詮釋儒家經典,使經學理學化,專主空談心性,輕考證。
阮元從一開始是主張揚漢抑宋的,他是繼惠棟、戴震之后出現的揚州學派的重要學者、乾嘉學派的殿軍。作為清代漢學的代表人物,阮元大力推闡漢學治學宗旨:“圣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圣賢為尤近。……有志于圣賢之經,惟漢人之詁多得其實,去古近也。漢許(許慎)、鄭(鄭玄)集漢詁之成者也。……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為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況圣賢之道乎?”并特別強調:“圣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圣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圣賢之道亦誤矣”,所謂“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為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況圣賢之道乎”?是說要尋求圣賢之道和經書義理,就必須通過文字、音韻、訓詁,舍此別無他徑。他走的是戴震一派以古訓求義理的路子。
阮元的漢學立場時有表露。比如《問字堂集》序中,阮元即尊崇漢儒而貶低宋人,“以元鄙見,兄所作駢儷文,并當刊入,勿使后人謂賈、許無文章,庾、徐無實學也……《原性篇》言性本天道陰陽五行,此實周、漢以來之確論,而非太極圖之陰陽五行也。引證一切,精確之極,足持韓、孟之平。宋人最鄙氣質之性,若無氣質血氣,則是鬼非人矣,此性何所附麗?漢人言性與五常,皆分合五藏,極確,似宜加闡明之”,“惟是求仙采藥,致壞封禪二字名目爾,光武尚可,唐玄宗、宋真宗等,仍是漢武故智,以致宋、元以來,目光如豆之儒,啟口即詈封禪,是豈知司馬子長、司馬相如之學者哉”。阮元不僅自己堅持漢學立場,而且積極推廣這種學術:“以經注經,此為漢學之先河,六藝指歸”。曾入阮府作為幕僚的方東樹就批評阮元“徒以門戶之私與宋儒為難”。
然而,自嘉、道時起,漢學由鼎盛走向衰落。這是因為,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考據學家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國家景運昌明,通儒輩出。自群經諸史外,天文、歷算、輿地、小學,靡不該綜,載籍鉤索微沉,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到嘉、道之際,漢學研究已無多大的發展余地,“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的漢學一統局面,已難以再現。正如梁啟超云:“考證學之研究方法雖甚精善,其研究范圍卻甚拘迂。就中成績最高者,惟訓詁一科;然經數大師發明略盡,所余者不過糟粕。”換句話說,嘉、道時期已經到了對百余年來的漢學研究進行全面清理、總結的時期。而當時能夠擔當此項重任的非阮元莫屬。最能體現阮元此時學術觀點有所變化的是他在幕賓江藩與方東樹之爭中所持的態度。
江藩與方東樹,歷來被視為嘉、道之際漢、宋之爭的代表人物。江所著《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系統地總結了清代漢學發展的歷史及研究成果,對宋學的貶抑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方所著《漢學商兌》則“為宋學辯護處,固多迂舊,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漢易者之矯誣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為知言。”耐人尋味的是,江、方都久客漢學家的領袖阮元幕下,而且他們之間的爭論,就發生在他們客阮元幕府期間,這就使爭論更加引人矚目。
作為幕主,阮元在這場爭論中的態度很值得注意。方東樹上書于他,他并沒有給予答復。方東樹的弟子鄭福照說:“阮文達公初與先生論學不合,晚年乃致書稱先生經術文章信今傳后。”其實,阮元在結交方東樹之前,其學術思想中已有折中漢、宋的趨勢,主張“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所謂阮元初與方東樹“論學不合”并不是絕對的,因為方東樹對漢學的攻擊既然有合理的因素,這就不能不引起論學主張實事求是的阮元的注意。但是,由于方東樹對漢學的攻擊過于猛烈,以至于《漢學商兌》“意氣排軋之處固甚多,而切中當時流弊者抑亦不少;然正統派諸賢莫之能受”。而漢、宋兼采在當時還“只是一種強有力的潛流”,并未形成風氣,這就使作為漢學家領袖的阮元很難對方東樹的觀點公開表示贊同,因為“在本派中有異軍突起,而本派之命運,遂根本搖動。”事實上,阮元雖沒有對《漢學商兌》公開表示看法,但他將江藩與方東樹二人長期留居幕下,直至道光六年他調任云貴總督,二人方才辭別,這實際上已經表明了他的態度,說明嘉、道之際漢、宋合流的趨勢已開始出現。
阮元晚年,漢、宋兼采形成風氣,阮元不必再有所顧忌,所以他著《性命古訓》,“謂漢儒亦言理學,其《東塾讀書記》中有朱子一卷,謂朱子亦言考證。”并“致書稱先生(方東樹)經術文章信今傳后。”當然,阮元畢竟來自漢學家陣營,即使主張漢、宋折中,也免不了對漢學有所偏袒:“稍欲調和兩家說,然其意護前總不能自克,凡載諸文字者略可考見”。他還資助江藩刻印了《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三種著作。阮元的這種態度與來自宋學家陣營的方東樹主張漢、宋兼采,卻又免不了對宋學有所袒護,是同樣的道理。
以科舉正途入仕的阮元不滿于漢學家的門戶之見,主張調和漢、宋之爭。一方面,是因為清廷奉程朱理學為官方正統哲學;另一方面,漢學末流日益脫離現實而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最重要的是,終身致力于學術研究的阮元發現,門戶之見對學術的交流與發展極為不利。強調門戶,拘守一隅,自設藩籬,甚至黨同伐異,這嚴重影響了學術的交流與發展。而阮元則主張“力持學術之平,不主門戶之見”。正是漢、宋學兼宗的治學態度,以及與前輩師長及同輩友朋之間的砥礪與切磋,使得阮元的學問具有兼收并蓄、恢弘博大的氣象。
實際上,漢學與宋學兩者不可偏廢,并非阮元首創,早在乾隆初年就已有此提法。乾隆五年上諭說“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箋疏之說,夫典章制度漢唐諸儒有所傳述,考據因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以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而圣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就個人的學術傾向而言,阮元無疑是揚漢抑宋的。其調和漢、宋的學術主張將自己推到了清代兩個最大學術流派之間的爭端當中。我們在同情其學術境遇的同時,也不得不慨嘆,阮元作為一位講求實事求是治學態度的乾嘉學術大師的確當之無愧。后來的事實證明,阮元的這一做法對后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主張兼采漢、宋學的思想,對晚清學術界特別是以林伯桐、陳澧等為代表的嶺南學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雖“不弋科舉”卻“漸染俗學不能變”
清代的書院,經歷了由禁止到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朝廷大興文字獄的影響,迫使書院改變了學術追
求,一種與現實政治較遠而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考究經典的學風終于形成,即乾嘉考據之學。而當時清代的書院仍以理學為尊,以朱子為宗,以科舉為業,講求心性之學,不研究或傳授漢學。因此,創辦新式書院,給腐朽的教育注入新鮮活力,成為乾嘉學者的共同愿望。以阮元為代表的乾嘉漢學中堅創辦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專課經史訓詁之學,崇揚乾嘉漢學,成為乾嘉漢學研究、人才培養和傳播的基地。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創建的目的是以經史實學去挽救書院墜落為科舉附庸的流弊,意在返回傳統,推古求新,重振書院事業。它們不僅使江浙及嶺南地區形成了重漢學的學風,而且成為各地書院改革過程中仿效的楷模。
阮元于嘉慶二年任浙江學政時,在杭州孤山南麓構筑了五十間房舍,組織文人學子輯成了《經籍纂詁》這一規模宏大的古漢語訓詁資料匯編。嘉慶六年,阮元奉調撫浙,遂將昔年纂籍之屋辟為書院,選拔兩浙諸生好古嗜學者讀書其中,顏其額日“詁經精舍”。同時又在西偏修建了第一樓,作為生徒游息之所。精舍地處風景秀美的西湖孤山之麓,它聘孫星衍、王昶等主講,授“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于是漢學大行。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說:
蕭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書,初時鮮過問者。自阮文達來督浙學,為作序推重之,坊間遂多流傳。時蘇州書賈語人:“許氏《說文》販脫,皆向浙江去矣。”文達聞之,謂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
天文、算學、地理等長期居于傳統學術視野邊緣的科技內容,在這里得到了少有的重視,其中甚至還有一些西學內容,這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罕見的,在當時大多數書院熱衷于八股時藝的環境下顯得尤為難得。它開啟了清代書院培養真才實學之士、講求經世致用之學的良好風氣。
實際上,在辦書院之前,阮元一直就重視西學。前述他的幕府當中的李銳,精通歷算之學。阮元說他“深于天文算數,江以南第一人也”,與焦循、凌廷堪號稱”談天三友”。他做了一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就是為《地球圖說》補畫地圖和天文圖。《地球圖說》是錢大昕根據法國傳教士蔣友仁獻給乾隆皇帝的《坤輿全圖》上的說明文字潤色而成。首次在中國正確地介紹了哥白尼的日心說,以及開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天文學發現。
阮元任浙江學政、巡撫十余年,提倡漢學、獎掖人才。阮元幕府和詁經精舍培養了大批漢學家,洪震煊、洪頤煊、徐養源、嚴杰、周中孚、朱為弼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道光以后,漢學開始向廣東等邊遠地區傳播。阮元及其幕府對嶺南學風的影響又是最大。學海堂的創立,成為阮元督粵時推廣漢學的前沿陣地。
嘉慶末道光初,阮元總督兩廣,目睹“邊省少所師承,制舉之外,求其淹通諸經注疏及諸史傳者,屈指可數”。于是仿詁經精舍之例,在廣州城北粵秀山麓建立學海堂,“欲粵士無忘初志,學于古訓而有獲”。
詁經精舍和學海堂為突出“專勉實學”、崇尚漢學的宗旨,將科舉之學完全排除在教學內容之外,“月率一課,只課經解史策、古今體詩,不八比文、八韻詩。”阮元之弟阮亨稱詁經精舍“以勵品學,非以弋科名”。孫星衍也稱詁經精舍“不課舉業,許各搜討書傳條對,不用扃試糊名法”。所謂“非以弋科名”、“不課舉業”,并不是反對求取功名,而是認為學問和功名并不沖突,在治學中求取功名,順理成章。不僅如此,詁經精舍還在某種程度上反對程朱理學,孫星衍說:“(阮元)使學者知為學之要,在乎研求經義,而不在乎明心見性之空談,月露風云之浮藻,期精舍之舊章,文達之雅意也。”學海堂的教學內容也是以經史考據為主。阮元要求生徒“或習經傳,尋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教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
阮元的書院改革獲得了一些學者和官員的認同。之后的兩廣總督盧坤沿襲了他以經史考據課士的傳統,將《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文選》、《杜詩》、《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等書作為書院授課的主要教材。
然而,宋代以來書院與程朱理學、陽明心學的一體化的歷史慣性使崇尚漢學的書院很難完全與理學絕緣。更何況在當時科舉制度幾乎是士人出仕的唯一途徑,大多數士人已經從潛意識就信仰通過科舉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他們亦不可能不潛心科舉之學,更不可能從根本上反對科舉制度。況且,乾嘉漢學大師一般也是通過科舉之學獲得功名以后才專漢學的。因此,從書院發展的傳統、科舉取士制度所形成的社會背景都注定了反對科舉制度、專門研習漢學書院的數量會相當少,并不能成為清代書院的主流。有些宣揚研習經史考據之學為主的書院亦不得不采取變通措施,以獲得存在的合法性。盧文招在主講鐘山書院時,愿意跟隨他研習漢學的學生是寥寥無幾,“在鐘山幾五載,幸有一二同志信而從焉”,這足能透露出跟隨者少的窘境,他也不得不承認“漸染俗學已深者,始終不能變也”。出于教授這些“染俗學”者科舉之學的需要,有時也“不得已而看時文,講時文”。如湘水校經堂創辦以后就對教學內容實行變通,即漢、宋并舉,與詁經精舍、學海堂創辦時反對程朱理學,要“奧衍總期探許鄭,精微應并守朱張”已經有相當的距離了。其實阮元對書院生徒從事舉業也是有清醒認識和心理準備的,即在科舉是士人仕進的主要途徑的社會氛圍下,根本無法讓大多數士人拋棄八股文而完全沉醉于漢學之中去,他說:“上等之人,無論為何藝,皆歸于正,下等之人,無論為何藝,亦歸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習,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甚多,勝于詩賦遠矣。”這可能是阮元對書院講求宋明理學、開展科舉教育的清醒的認識,也是無可奈何的心理表白。


責任編輯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