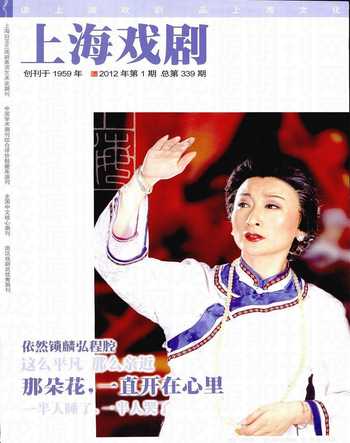守住舞臺
木葉
訪《京戲啟示錄》編導李國修
1974年,18歲的他,就讀世新大學廣播專業,于話劇社第一次接觸表演。
1980年。加入臺灣蘭陵劇坊,開啟戲劇之門。
1985年,告別電祝臺喜劇諧星的身份。游學日本研修戲劇。
1986年。創立“屏風表演班”,身兼劇團藝求總監、編劇、導演、演員。那一年,他31歲。如今屏風表演班走過了25車。創作出近40部原創作品。
回想這一路的戲劇旅程,李國修歷歷在目。說到興致處。還起身比劃幾下,眼眸中依舊透著18歲初次接觸戲劇的赤忱。在筆者采訪經歷中,李國修可算是唯一如此清晰記得自己生平的戲劇人吧,可見他的戲劇之路真是一步一個腳印踏實走來的。如今,他攜帶著醞釀多年的半自傳舞臺劇《京戲啟示錄》來到上海,筆春相約與這位臺灣戲劇家聊聊創作、談談情感。
問:是怎樣的契機讓您想要創立自己的劇團?因何取名“屏風”?
答:取名“屏風”,是因為我認為戲和人生并無距離,擺上屏風,就能演戲,幕前戲子伶人的扮演,不過是屏風后真實人生的演繹,創立劇團,緣于日本游學的經歷,那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當時日本有四百多個劇團,我這才了解到原來可以無處不劇場、天天有戲看。有次我在日本看一出傳統戲劇,聽不懂唱什么,只見將軍坐著一個小凳子,一黑衣人蹲在旁約莫一刻鐘,紋絲不動。因為這個,我哭了。這種對戲劇的尊重,從現代中尋找傳統的精神,讓我下定決心要守住劇場,守住自己的舞臺。那個黑衣人其實是檢場人,日本傳統戲劇中保留了在京劇中早已刪除的一個角色,我運用到《京戲啟示錄》中,那種間離效果是很美的。
問:《京戲啟示錄》創作緣起?該劇為您半自傳作品,如何作解?
答:1996年屏風成立十周年,當時承蒙所有關心我們成長的朋友厚愛,累積了小小的成績,我更強烈地感受當時自己的創作與做劇場的態度深受先父一生重情講義、執著無悔的影響。于是,在《京戲啟示錄》里,我只想回頭看看我親愛的父親——關于先父以及他和梨園行的過往。當時年歲未過半百,人生歷練不足寫下自傳,呈現于眼前的《京戲啟示錄》,姑且容我戲稱——李國修半自傳作品。
先父李慎恩,從十六歲起在山東青島拜無名藝師學做戲鞋。大時代的變遷,終老干臺北。憑著他的一雙手,養活了我們一大家子,生前他“貴”為“臺灣唯一制作純手工戲靴的藝師”;現則由我大哥李玉修繼承衣缽。多年來,從先父到我大哥一直依賴著臺灣京劇彼此共生共存著,耳聞或目睹兩岸京劇近年正逐漸凋零式微中,我只能在一旁擔憂且無力給予任何協助。大哥找不到徒弟傳承,角兒還唱不唱?將來又有多少戲鞋可做?在京戲的環境中,我是不是過于憂慮?
無論從任何一個立場,我于京劇,一向是個門外漢,我毫無資格對京劇的現在與未來妄下任何評語與斷言。我只能寫下一些感觸——從我對先父的回憶中。
問:創作過程中是否遇到過困難與瓶頸?
答:《京戲啟示錄》1996年首演,今年是第4度搬演。我常常對看完《京戲啟示錄》后的觀眾問一句話:“你掉眼淚了嗎?”因為自己在創作《京戲啟示錄》時身心飽受煎熬,身體曾發生嚴重的暈眩,整整三個禮拜思緒毫無焦點,劇本進度完全停滯。我是一個害怕面對自己的人,一邊創作,一邊哭掉10盒面紙,在文字與想象里,在心里和父親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對話,過程中幾乎崩潰,但終于熬過來,并且完成比以往都要令人滿意的劇本。
問:您似乎很鐘情于戲中戲,之前創作的《莎姆雷特》、《征婚啟事》都是如此,尤其是到了《京戲啟示錄》這結構更運用得爐火純青,在該劇中“戲中戲中戲”是如何鋪陳的呢?
答:因為父親的緣故,我打小就在后臺長大,看著戲臺上的忠孝節義,戲臺后的柴米油鹽。這就種下了我喜歡寫戲中戲的前因。此外,我認為戲中戲的文本結構最能恣意游蕩與勾勒出那真假之間的各種輪廓,借著戲與戲之間的時空進出,戲里戲外的扮演都是真實,卻也都是虛構,在這真假虛實的流竄間,更會看見故事里最真的情感與價值。
“戲中戲中戲”的敘事結構在《京戲啟示錄》第一次發生,風屏劇團彩排演出《梁家班》,梁家班演出《打漁殺家》,除了主要的三層結構外,還演繹了風屏劇團團長李修國回憶父親的“戲外戲”,以及梁家班班主的次子梁連英演出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戲后戲”。五個不同的時空,藉由一群不屬于特定時空的檢場人將場景與道具搬動來轉換情境,將時空與時空之間的轉變自然地連結。有時候,空間還在過去,角色卻已經來到現在;就像是人的記憶一樣,曾經的童年往事或青春時的一段美好回憶,得花多久的時間從腦海里將那畫面翻閱出來?!三秒鐘?一秒鐘?或是更短?!眼前所見的真實,有時會讓你躍入曾經的記憶,而曾經的假象或許會隨著越拉越遠的時間軌道,慢慢刻劃成為你相信的真實;每到下一秒,現在就會成為歷史!隨著舞臺上流暢的時空進出,你將會忘了去探究孰真孰假,全然地讓它引你進入時空與時空交迭的情境。
問:您說過您這輩子只想做好一件事,就是“開門、上臺、演戲”。那么,戲劇中是什么吸引了你不離不棄跟隨一輩子?
答:帶領屏風走過25年,回首草創的年代,的的確確經歷了一段坎坷之路。沒有人知道如何經營一個劇團,但屏風無懼無悔,屏風以“面對劇場的態度就是面對生活的態度”,堅持在要求別人的肯定前,先要求自己的付出。誠如我太太王月所言:“京戲走過中國人的戲臺兩百年,京戲讓多少角兒日夜叩求祖師爺能賞這口飯吃,好捐獻出自己的青春血汗,博取臺下觀眾的一聲叫好。輝煌的京戲班到梁家班,梁家班經風屏劇團到屏風表演班,歲歲月月的流逝,不變的是這班戲子伶人,其為掌聲而付出的忠貞心志!”我之所以執著于舞臺劇的表演與生活,在《京戲啟示錄*里已經表達了我的信念。感恩我的父親給我的人生啟示“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圓滿了!”父親做了一輩子的戲鞋,沒改過行。我選擇這輩子做戲,永不后悔。對于這出戲的感情,絕不止于它是半自傳色彩的作品,更代表他的人生信念與做戲的最高指導原則,而若是哪天屏風表演班要解散了,我也會選擇這出戲作為解散公演。
采訪的最后,他說“觀眾不曾棄我而去”。他亦不會棄舞臺而去。李國修表示,這么多豐做劇場,自己活在臺灣只求三件事情。一求溫飽、二求安定、三求傳承。一般大企業會被問到接班人,劇團也是,我父親做戲鞋的技能傳給我大哥,而我選擇劇場,要完成的使命也是傳承。2011年的12月《京戲啟示錄》傳承版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演出。作為屏風表演班25周年的禮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