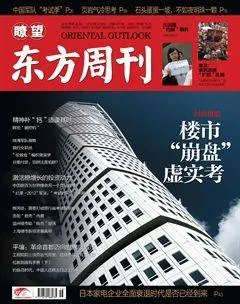“紅星— 2012”軍演:“考試時間”誰來裁決

初冬的華北平原,收獲后的田野靜默著,干枯的玉米秸稈連片挺立,隱匿在土黃色偽裝網下的異形帳篷與大地渾然一體。
這些帳篷內,安置著數組紅藍軍師旅級指揮所。從外面看去一片寧靜,走進帳篷卻是火藥味撲面。佩戴著不同軍種臂章的高級軍官們,面對密密麻麻坐滿一地的紅藍雙方指揮官,毫不客氣地指出他們所犯的錯誤。“這是一個不足”,成為高頻率出現的評價。
一次例行年度軍事演習——“紅星- 2012”于11月上旬在河北石家莊西部山區舉行。300多名中級軍事指揮員,演練了渡海登島、邊境地區反擊作戰等課題。
作為軍演考核模式的一種嶄新嘗試,演習組織方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邀請了北方三大戰區、野戰部隊、跨軍種院校等單位的指揮官、專家,對演習進行聯合考核與裁決。而在一體化指揮平臺上率部“廝殺”的雙方,紅軍是正在接受任職教育的學員,藍軍是學院的教員。
考評結果將記入這些年輕軍官的成績單,對即將回到部隊指揮崗位的他們來說,這個成績至關重要。
沙場秋點兵,解放軍在這個季節進入“考試時間”。過去大約10年間,中國陸軍對骨干部隊建立了以演習為主的考核機制,來自總部的考官們每年秋天都奔赴各大戰區,進行年度訓練考核和等級評定。
以想定作業演習的綜合動態方式取代單項靜態考評,以隨機抽取考官的總部考核取代自我評價,以條分縷析、層層量化的軟件系統取代人工打分……種種努力都是為了客觀反映部隊的戰斗力,發現漏洞與不足。只有連年通過檢驗者,才能被稱為中國軍隊精銳中的精銳。
事實上,由總部“空降”的考核還不能大面積覆蓋所有部隊,對于相當多的部隊單位來說,常態的訓練、演習中,內部評價仍是主要形式。就軍事院校而言,學員的培養成效多由自己的教員來評定。
在“紅星- 2012”軍演中,教員不再是“裁判員”,卻化身學員的“敵人”,師生對陣,共同接受外來考官多角度的挑剔審視——這些新鮮嘗試,看似演習考核模式的微調,卻將匯入軍隊打磨戰斗力的革新潮流,促動軍隊建設的大步推進。
受邀參與聯合考評的空軍指揮學院教授申曉青大校告訴本刊記者:“在形成機制后,這種考核模式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不能自己給自己發合格證
聯合考評組的辦公室里,紅藍軍提交的作戰文書堆成小山。幾位鬢角發白的高級軍官,像批改作業那樣細致地標注、勾畫。除了像申曉青這樣的各軍兵種專業權威,考官們還有來自應急機動作戰部隊、特戰旅以及扮演藍軍部隊的指揮官。
對于演習中指揮員們運用空軍的情況,申曉青毫不客氣:“很難稱為合格。”
他舉例說,聯合戰術兵團指揮部的指揮員不太了解敵我雙方的空軍兵器,“紅方配置的是‘殲轟7’,一些指揮員認為它只能執行轟炸任務,其實它掛上空空導彈就可以進行空戰。”
再比如,派出陸航部隊時,高空要由空軍航空兵建立保護地帶,因為武裝直升機很難應對戰斗機的突襲。
申曉青講評完剛走出軍用帳篷,就被幾名陸軍中校圍住,詢問有關空軍出動周期的問題。
“不少問題連專門的空軍參謀也未必能講得清,但軍種聯合是大勢所趨,通過這樣的演習提升指揮員的聯合作戰意識很有必要。”他告訴本刊記者,目前指揮員們已經會在演習中“本能”地使用空軍,對于空軍在火力打擊中的角色很清楚。
面對考官們不留情面的批評,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院長石忠武少將毫不意外,相反,他認為這正是此次探索的目的所在,“這樣才能真正檢驗學員的能力。”
他說,在最后的考核結果中,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自己人”的意見只占30%,“外部評價”是主導性的。
這種考核模式用專業術語講叫做“訓考分離”。軍事演習兼具訓練和考核雙重性質,以往常見的模式是“自訓自考”—— 演習導演組、考評組都是本單位的領導和業務權威,最后為自己組織的演習打出分數、評定成效。
在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陸軍中級指揮員對于空軍、海軍的了解,一般來自專門軍兵種教研室的授課。雖然學院也有空軍教員,但學養和經驗很難與專門軍種學院的高級教授匹敵。
“自己學校的教員考評自己的學員問題很多。”石忠武分析說,一方面,學員成績與教學業績相關,教員們很難完全做到對學員毫不留情;另一方面,考核結果也經常會產生爭議,為此甚至一度由學員參與考評,但反復調整仍無法達到理想狀態。
“戰斗力怎么樣,不能自己給自己發合格證。”石忠武說。
“達爾文的進化論說明,近親繁殖會導致衰退,這是無需置疑的。”申曉青說。這位專家在空軍內部就以權威和直率而知名,他對于這次演習的觀察不僅限于對指揮員們的考評,甚至包括演習本身。
比如在演習設定中,將一個空軍航空兵團編入一個旅級聯合戰術兵團,在申曉青看來,這更像傳統的合同作戰模式——用其他軍種支援陸軍作戰。而“紅星—2012”的目標更應強調聯合作戰。
濟南戰區扮演藍軍部隊、某機械化步兵旅副旅長劉俊學對本刊說,作為演習前的一項準備工作,聯合考評組曾對演習的模式、規則等進行了認真的“辯論”。
“一次演習能夠檢驗一個單位的全部面貌。”石忠武說,演習不僅檢驗學員,也應考驗教員,而這在“自訓自考”的模式中無法實現。
從“排隊打槍”到綜合演練
“紅星- 2012”在華北平原的田野上排兵布陣的這個季節,也是中國各地部隊外訓、演習、演練的高峰時段。這些軍事行動不僅具有訓練的性質,也成為部隊考核的主要方式。
像參加奧運會一樣進行射擊競賽,曾經是中國軍隊考核的主要手段之一,另外一些重要的訓練考核方式還包括像《士兵突擊》中的許三多那樣做“腹部繞杠”。
“現在部隊中也有崗位練兵,比如評定神槍手、技術能手,不過,各種考核方式都豐富了起來。”劉俊學說。
一類是根據不同訓練階段、訓練目的進行的成績考核,比如新兵入伍訓練,考核大多由“大單位”—— 即戰區及相當等級的上級機關組織。
最受關注的則是專業戰術、合同戰術以及年度演習。承擔不同任務的部隊每年組織不同數量、種類的實兵軍演,此外還有指揮員晉級考評等。
根據2008年頒布的新一代《軍事訓練與考核大綱》規定,部隊每年野外駐訓時間不少于4個月,加上外出演習和進行特別課目的施訓,“大多數部隊每年外訓時間在半年以上,長的超過8個月,比過去增加了一倍多。”劉俊學說。
除了戰斗部隊,科研院所、軍事院校等都按照大綱執行。這個已經常態化的外訓時段成為提升中國軍隊戰斗力的關鍵一環,而一般作為外訓收尾的演習、演練也具有了檢驗性質。
新一代《軍事訓練與考核大綱》是新世紀以來軍事訓練改革的成果,加大信息化含量,突出了野外訓練和演習的比重。正如這一大綱頒布時,某集團軍裝備部部長接受《解放軍報》采訪時所言:野外駐訓以及演習、演練期間,走出營地的部隊由相對集中到高度分散,環境由整齊劃一到相對混雜,條件由相對舒適到比較艱苦,加上裝備動用頻繁,裝備管理和技術保障面臨的矛盾和困難增多。
軍事演習特別是實兵實裝軍演本身就極具風險。除了裝備損失,部隊整建制機動,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就可能使演習成為指揮員的“災難”。
過去主要的應對辦法是:演習以計劃性導調為主,按照既有計劃步步執行。導調是軍事演習中的關鍵詞,可簡單理解為導演調度。而實兵檢驗性演習為了避免“演習像演戲”,強調隨機導調。
另一種降低風險的辦法是減少科目,比如減少實兵實裝部分的時間,縮短遠程機動的距離,乃至放慢車速。總之,用最小的“動作”應對外訓、演習和演練。
誰來考,決定著演習的“難度系數”。“大家歸根結底還是希望通過演習更好地檢驗和提升部隊戰斗力。”總部“部隊演習改革”研究課題負責人、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教授楊寶有大校告訴本刊,一旦涉及具體問題,牽扯成績、利益等復雜關系,自己考自己就很難做到客觀超脫。
他說,在對抗性、檢驗性演習已經取代年終考核,成為衡量部隊的主要標尺之后,如何考評演習成為一個關鍵問題。
上百個考評點讓部隊“過篩子”
目前中國軍隊最權威的考評方式之一,是自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軍事訓練等級評定制度:由各戰區和大單位推薦,總部考核組抽簽確定若干直接考核對象。
“軍事訓練一級師旅級單位”評定的“保質期”為3年,表彰名單會在軍隊媒體發布。2011年,全軍及武警部隊有49個單位被授予這一稱號。
“一級師旅”的考核由靜態展示與動態演示、多媒體演示與實兵實裝考核等幾部分組成,隨著全軍統一的等級評定覆蓋面擴大,統一訓練考核標準也提上議事日程。
此前,各大軍區都是自己考核,骨干部隊的數據和指標水漲船高。“有時候說部隊能不能打,還會提起他的歷史傳統和作風。”曾任總參謀部軍訓和兵種部合同戰術訓練局局長的石忠武回憶說。
為了解決部隊演習的考核問題,陸軍演習評估系統在2003年正式建立。它以整體作戰能力為著眼點,當時確定了五大類、26個分能力。
楊寶有解釋說,五大類能力是指揮控制、遠程機動、火力打擊、整體防護、保障能力,后來又分解為32個分能力、100多個考評點。目前,為應對信息化條件作戰,增加了第六個大類即信息偵察能力。
“在五大能力中,指揮控制和火力打擊一直是各級首長和部隊關注的重點。”楊寶有說,這從側面體現了當前軍隊建設的方向。
演習評估系統希望通過信息導調員和自動器材,將演習數據進行量化演算、分析,最后自動形成考評報告,從而細致、客觀地反映演習情況。也就是考試工具的客觀化。
“比如部隊在機動任務中,什么戰場環境、什么裝備、什么路況、什么天氣條件,用多長時間能夠抵達,多長時間是合格、多長時間是優良。”石忠武說。
2005年,總部首次運用“部隊演習評估系統”對陸軍部隊實施考核。根據通報,3個“一級師旅級單位”在以實兵檢驗性演習為主要方式的考核中,被降為二級單位。
裁判員的變化使軍事演習的面貌大為改觀。在被視作經典案例的“確山- 2006”軍演中,總部考核組歸納出部隊存在的八大類500多個問題,并向公眾輿論公開,反響強烈。
第二年,這支受考核部隊所屬的濟南戰區主動對其再次考核。當時擔任演習總導演的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登上一輛坦克,命令其用高射機槍完成對低空目標的射擊,這一科目并未預設。
期待頂層設計
總部對骨干部隊的演習考核體系逐漸完善,但因條件約束,目前“一級師旅”抽檢考核覆蓋面有限,且并不涉及院校、科研機構等單位,面對更多部隊的外部考核機制尚未形成。
聯考聯評也曾在作戰部隊進行過嘗試,一般由戰區組織,而跨軍種、面向聯合作戰的外部評價,更是需要高級指揮機關的協調部署。
在歷經10年建設之后,如何將“訓考分離”下沉,使其貫徹于各級軍事單位并成為常態,已成當務之急。
申曉青更關注聯合作戰,他上次到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這座中國最著名的陸軍軍校還是在1998年。
在演習場地,申曉青認真地了解了陸軍的裝備情況,還坐進坦克駕駛艙體驗一番,“遇到搞炮兵的,就抓緊問問火炮的發展情況。”
他坦承,即使是自己這樣的空軍高級軍官和技術權威,對其他軍種也會缺乏一些基礎性的常識。在“紅星- 2012”演習過程中,他幫助陸軍專家修改了涉及空軍的演習文件,令后者獲益匪淺。
“這種聯合多軍種、來自第三方的常態考核機制,將是解放軍檢驗部隊聯合作戰能力的重要一環。”申曉青說。
引入外部評價,風險明擺著:可能造成業績指標下滑,肯定會帶來壓力。“這就得看首長的決心” 。
石忠武則強調,這種機制對于教員知識能力的轉型和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紅星—2012”演習中,由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的教員編成藍軍與紅軍對抗,藍軍最終被裁決獲勝。老師和學生一樣,在野外指揮所60小時連軸轉,在演習結束后的講評中,并肩坐在小板凳上,聆聽考官們對于自己作業的嚴苛批評。
從軍事院校的角度,石忠武更注重來自作戰部隊的評價,“到底學員能否達到部隊的要求,最有發言權的還是部隊”。申曉青強調,建立這一機制很有挑戰性,“必須下決心,有了開頭,才能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一個新模式的嘗試,哪怕只是微調,也會碰觸很多實際問題:是否有決心承受“自曝短處”的壓力?是否有無縫對接的技術平臺?能否建立科學實用的考核體系?跨軍種、跨戰區邀請考官,能否調動最權威的力量?
這些具體問題,無一不指向“頂層設計”。用申曉青的話說,這些都需要更高層次機構的決心和謀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