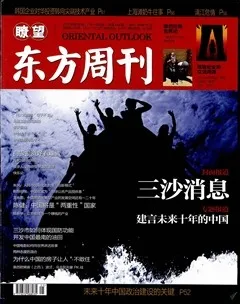陳健:中國將是“兩重性”國家
所謂“負責任的大國”是西方國家定義的,是要我們不要挑戰美國,不要挑戰現有國際體制。應對這一點,我們需要發展政治上的感召力,或者說中國要成為一個有感召力、親和力的國家。但是目前中國在這兩方面都做得還不夠
《瞭望東方周刊》:作為資深外交家,你如何評價觀在中國“大國”形象的塑造?
陳健:其實不存在“大國形象的塑造”這個問題——中國強大了,大國形象自然而然就產生了。
現在的問題是,西方希望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有時候也借用這句話,但是我并不太喜歡這句話。所謂“負責任的大國”是西方國家定義的,是要我們不要挑戰美國,不要挑戰現有國際體制。應對這一點,我們需要發展政治上的感召力,或者說中國要成為—個有感召力、親和力的國家。而目前在這兩方面做得都還不夠。
號召力體現在我們自己的成功上,包括經濟建設的成果帶來的號召力,以及中國的體制和價值觀所具有的號召力。我們的價值觀體系既要為全體中國人所接受,同時也要被國際社會認為是先進的價值觀體系,這樣就有了政治上的號召力。
同時還要有親和力,主要體現在外交上。我們需要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能夠促進各國謀取最大的共同利益。
《瞭望東方周刊》:你覺得在未來10年,中國應如何定位自己的國際地位?
陳健:應該說對中國的定位是最困難的,因為我們從國民生產總值來說是全球第二,按照現在各方面的估計,未來十年內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從總量來說已經是—個“大塊頭”了,但是人均還很低,而科技水平等軟實力、硬實力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
所以說中國有“兩重性”:既有發達國家的屬性,如東南沿海地區,上海北京等城市完全可以媲美發達國家;但內地有些地區還相當貧困。這個“兩重性’會繼續保持相當長一段時間,今后10余年還是兩重性繼續并存。
對于我們的發展目標,政府已經提出來了,包括可持續發展、消除貧困、消除差距等等,如果發展目標能夠實現,在今后十余年間我們就能成為—個中等發達國家,就可以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目前我們的難處在于,人家看我們是一個大國,要我們承擔大國責任,而我們知道自己還是—個弱國,大而不強,這當中的矛盾始終存在。
《瞭望東方周刊》:你如何評價中國在黃巖島事件中的外交表現?
陳健:黃巖島事件,我們的外交處理得很好。根據歷史經驗,我們既要占理,又要占義。中國始終要站在國際化視野之上,尋求自身利益的制高點;同時又要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這兩者缺一不可,也是當前外交上的—個難點。
《瞭望東方周刊》:在未來碳排放和環保責任的國際談判中,你認為中國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立場?
陳健:我主張,中國要承擔高于一般發展中國家、低于發達國家的義務。我們再強調自己只是發展中國家,已經不太夠了,因為我們已經是最大的污染國之一、第二大經濟體。不過從歷史責任和人均來說,我們的確不應該承擔發達國家的責任。所以我們所應該承擔的義務應該如此定位,這樣更容易被國際接受。
《瞭望東方周刊》:聯合國是另一個重要的大國角力舞臺。有觀點認為,聯合國容易受到大國的利益驅使,你曾在聯合國工作多年,如何評價這種觀點?中國應該怎么做?
陳健:聯合國容易受大國利益的驅使,這種觀點完全沒錯。聯合國是建立在大國一致的基礎上的,如果沒有大國一致,取消否決權,聯合國就將不復存在。所以聯合國必然受大國利益驅使,這是正常現象,我們要接受。
對于中國來說,關鍵是怎么利用自己的大國利益,尋求中國這個大國的利益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一致,這樣我們就不是像美國那樣的霸權主義超級大國,試圖主導世界,我們就站在一個更高的道義制高點上。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各國都很重視民間和公眾外交,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是否也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陳健:民間外交最好的例子就是奧運圣火傳遞在巴黎遭遇的風波。對于中國外交部發表的講話,西方媒體基本沒有評論,有的甚至以反對的態度來報道。但是中國留學生在巴黎奧運圣火傳遞中,既舉法國的國旗,又舉中國的國旗,獲得了很高的關注度。民間外交的好處在于,其發表的觀點影響力更大,而有的時候政府表態則往往被認為有固定的思維模式,不會引起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