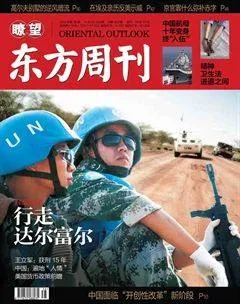京官靠什么彌補赤字
道光二十一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一共花掉了六百二十兩銀子。而他每年法定收入129.95兩。這樣算來,赤字為490.88兩。
做官一年,入不敷出如此。那么,京官如何彌補赤字呢·
一個重要的途徑是外官的饋贈。
談起晚清的官場腐敗,人們最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 “冰敬”(孝敬夏天買冰消暑的錢)、“炭敬”(冬天燒炭的取暖費)、“別敬”(離別京城時的“分手禮”)之類饋贈,少則數(shù)兩數(shù)十兩,多則數(shù)百兩。因為數(shù)目不多,面積太廣,人們習以為常,已經(jīng)很少有人認為這是一種腐敗。
對大部分京官來說,外官饋贈都是沙漠般枯竭的財政生活中不多的清泉,幾乎所有的京官對此如饑似渴,因為它們積少成多,已經(jīng)成為和俸祿一樣穩(wěn)定和重要的收入來源。馮桂芬說:“大小京官,莫不仰給于外官之別敬、炭敬、冰敬。”
許多京官生活的重心就在營謀饋贈,他們花大量時間酒食征逐,部分原因也是因為只有廣泛交游,才有可能輾轉(zhuǎn)認識許多外官。外官入都之際,京官都爭相延請。李慈銘說,京官窮得沒辦法,每逢一個地方官進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沒有同學、老鄉(xiāng)什么的關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話,就要想方設法拉上關系,先是去拜見,然后是請吃飯,希望從中獲得一點好處。
和大部分京官一樣,曾國藩對外間饋贈也十分渴望。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曾國藩在家書中說:“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
不過曾國藩在京官中屬持身清竣注重名聲的一類,故接受的官員贈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記舊存銀數(shù)》中,曾國藩記載正月這類收入有以下幾筆:
程玉樵送別敬十二兩。羅蘇溪送炭資十兩。李石梧送炭資十六兩。
在《辛丑年入數(shù)》中記載從二月到年底的此類收入:
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銀四兩。
三月初六喬見齋送別敬十六兩。勞辛階送別敬十兩。
十四日黃世銘送別敬十二兩。
六月十五日座師吳甄甫送別敬五兩。
十月初八李石梧送別敬十二兩。
通計全年炭敬、別敬等項共計九十七兩。
另一個度日的辦法就是借錢了。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帶來的銀錢花光,外官饋贈又如此之少,曾國藩開始面臨借錢問題。在京為官,聲譽如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決定了你能不能順利地借到錢。
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關將近,手頭銀兩終于全部花光,曾國藩找人現(xiàn)借了五十兩銀子,才勉強過了個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銀已達二百兩。到這年年底,累計更高達四百兩。在這一階段家書中多次出現(xiàn)“借”、“欠”、“窘”的字樣,艱難形狀,躍然紙上。在此之后,借錢更成為曾國藩彌補財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
從曾國藩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俸祿收入只能滿足清代京官開支的五分之一左右,外官饋贈和借款是京官重要的資金來源渠道。困窘的生活確實使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為利心所擾,并導致不斷的自我批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記十分典型:
座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后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謂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
兩日應酬,分資較周到。蓋余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
立志成為圣人的曾國藩,卻心心念念想著借祖父的生日多收點份子錢,并為即將到來的祖父生日宴會,未雨綢繆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這不能說明他本性如何貪婪,只能說明清代財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個遵紀守法的官員要面臨何等巨大的經(jīng)濟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