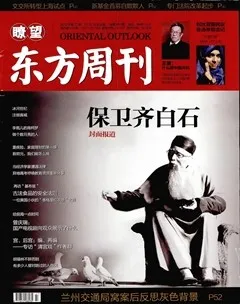救歐元,我們能怎么做
德國很可能也采取一種拖延戰略,它可以等待,將危機的時間盡可能拖長,使得本國銀行業積累足夠的資本以避免卷入外債貶值帶來的銀行業危機之中。
近日閉幕的歐元區峰會并沒有緩解外界的擔憂。歐洲三大經濟研究機構下調了對歐元區的預期,認為受政府縮減開支、勞動力市場形勢惡化和信貸條件收緊影響,第二和第三季度歐元區經濟將出現萎縮。
歐元區越來越濃的陰霾下,誰將從中獲益,誰會出手相助,又是誰在一旁作壁上觀?救助歐元,我們能怎么做?
邊緣國家可能從退出中獲益
一年以前,相當多的學者認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非常嚴重,但歐元區最終一定能夠克服困難,崩潰只是小概率事件,因為“歐元區解體的代價實在太高”。
一年之后,希臘的社會動蕩和經濟衰退顛覆了“退出成本不可承受”的想法。美國財政部、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顧問JohnH.Makin認為,“退出歐元區,希臘比目前的情形也不會再糟糕到哪里去。下一個問題是西班牙是否會效仿希臘”。
曾經在《大預測》中為世人描繪“2021年美國因為經濟危機而向中國籍IMF總裁申請援助”的經濟學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ArvindSubramanian甚至認為,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做法將引起其他未退出的成員國的嫉妒。在退出歐元區之后,通過巨幅貶值,希臘將很快重新走上穩健增長之路,“如果希臘能推行適宜的政策以快速地重建和穩定宏觀經濟,它或許將增長得更快更久”。到2013年,希臘已經重新走上恢復之路,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被緊縮政策折磨的國家還在危機中掙扎,它們國內的選民一定會向政府施壓,要求退出歐元區。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MichaelPettis對希臘、西班牙等國留在歐元區的前景進行了分析,結論也是這些邊緣國家將不得不退出歐元區。
其理由有二。一是外圍國家處于國際收支逆差國的地位,要解決危機,就必須徹底克服財政赤字問題,這意味著對外競爭力的提高和經濟的持續增長,而在現行歐元區框架下,這一目標難以實現。
另一個理由是,對陷入危機國家的救助,往往會與歐元區核心國的訴求相沖突。除非“德國和其他核心國家改變它們的經濟政策,刺激本國消費,減少本國儲蓄,以使得外圍國家的貿易逆差得以調整”,或者“外圍國家通過持續緊縮和維持高失業率,使得工資和價格下降至合理水平,并通過各項舉措鼓勵企業發展”。但是顯然,前一個訴求德國人不會同意,而后一個選項將被邊緣國家的選民極力抵制。最后的選擇只可能是希臘等邊緣國家退出歐元區。
從歷史經驗來看,債務貨幣化是債務國“解決”或走出危機的一種有效辦法,而退出歐元區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希臘等國進行債務貨幣化的前提。那些上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中的違約國家,無一不是通過貶值走向了復興。債務貨幣化伊始,它們都經歷了急劇的緊縮。而衰退只持續了一到兩年,經濟便觸底反彈。韓國以6%左右的平均速度增長了9年。盡管違約浪潮席卷了系統內幾乎所有的銀行,印尼也以5%以上的平均速度增長了9年。此外,阿根廷的增速接近8%,而俄羅斯高于7%。
德國會不遺余力地挽救歐元區嗎
歐元區內部最具影響能力的是德國。但德國會不遺佘力地挽救歐元區嗎?
從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開始,對德國的指責之聲就不絕于耳。批評者認為,正是因為德國等核心國家持續存在經常賬戶盈余,并且將這些盈余不斷通過本國銀行業對外圍國家提供貸款,才最終使得這些國家債臺高筑、難以為繼。
從德國的立場來看,上述指責完全不能接受。美國人認為,德國根本不是歐元區的受益者。歐元區成立之后,德國資本更多流向外圍國家,降低了國內投資,拖累了經濟增長。
德國現在在歐元區的情況,與當年美國面對拉美國家債務危機時的情況非常相似。拉美國家債務危機爆發在上世紀80年代初,但是直到1989年,美國才出臺布雷迪計劃,實現對官方資產的減記。而在此之前,美聯儲通過干預利率,使得美國的銀行能夠獲得充足的利潤,以實現資產的重組,而絲毫不顧拉美國家失去的十年。
德國會不會也采取一種拖延戰略呢?它可以等待,將危機的時間盡可能拖長,使得本國銀行業積累足夠的資本以避免卷入因外債貶值帶來的銀行業危機之中。問題在于,希臘等邊緣國家愿意留在歐元區內接受失去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命運嗎?誰會樂觀其“潰”
作為歐元區外部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美國會樂見歐元區的完整與強大嗎?
貨幣統一之后的歐洲,正是繼日元之后,最可能取美國地位而代之的經濟體。歐元的出臺讓歐洲一體化成為區域合作的典范,歐元自創設伊始(甚至之前)就作為美元霸權的挑戰者不斷被諸多學者討論至今。
從經濟規模看,歐盟也的確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這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將缺乏財政聯合的貨幣一體化所具有的脆弱性暴露無遺,這樣的局勢,不正是在向著對美國更有利的方向發展嗎?
不可否認,歐元區無序的主權債務違約會對美國的經濟造成沖擊。然而更關鍵的是,歐洲一體化的失敗帶給美國的是局部的、一時的、可承受的沖擊,同時帶來的卻是重大的戰略性的長期收益。在美國歷史學者赫爾曼看來,“歐洲的死亡,將證明美國自由市場制度的優越性”。他說,“歐洲正在崩潰,中國步履蹣跚,印度和巴西正在開全面自由市場改革的倒車,我們成了最后的穩定增長的經濟體。新的美國世紀正在到來——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最好能為此做好準備”。
新興經濟體援歐面臨內部約束
拯救歐洲的希望,也曾被放在新興經濟體身上。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出手救援,至少面臨兩重約束。第一,各國內部存在不滿于“窮國救助富國”的民間輿論壓力,這對于援助歐洲將帶來較大的阻力。第二,更重要的是,對于新興經濟體未來的增長可持續性存在重大爭議,決策者很難做出決斷。
如果新興經濟體的領導人決定出手援助歐洲,他們應該怎么做?
首先,他們之間應該達成某種協調,通過一種共同行動的方式來開展援救。說服國內民眾支持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集體行動,比說服他們支持本國單獨行動要容易一些。
其次,他們應當選擇一種兼具安全性和收益性的救助方式,例如通過購買IMF的債券來提供援歐資金。鑒于通過這種方式可以爭取到不低于美國國債利率的收益率,這樣就可以把援助歐洲解釋為全球范圍內優化資產配置的一種方式,從而規避“窮國救助富國”的指責。
第三,應當小心翼翼地采取措施維持本國的經濟增長和市場穩定。無論歐元區是否崩潰,歐洲實體經濟放緩幾成定局,通過貿易和投資渠道,負面影響將會傳導到新興市場。對此如果缺乏預案(比如降息刺激增長),是難以有底氣作出救助歐洲的決策的。
歐元區陷入危局,這顯然與歐元區的創建者們的愿望相悖,他們甚至沒有在條約中設立退出條款。
危機之下,要么是人的行為的調整。例如,更認同來之不易的歐洲聯合,更加勤奮,更注重有效率的投資和生產等等。要么是制度的退化,退回到各自為政的威斯特伐利亞歐洲。時至今日,無論歐元區的內部還是外部,放任歐元區或歐洲一體化進程崩潰情況出現且因此受益者的勢力似乎占據了上風。
人類歷史上又一次偉大的社會試驗結果就要見分曉。歐洲能順利通過嗎?筆者推測,它極可能面臨未來補考的命運。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